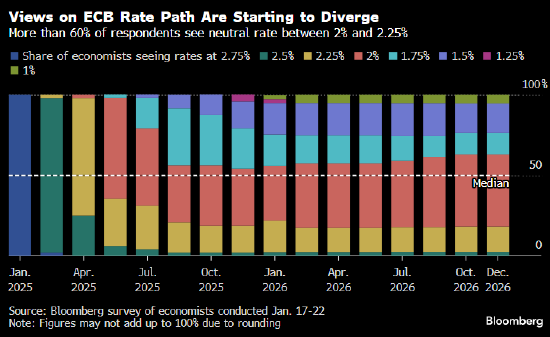原标题:被拆掉“葛宇路”的葛宇路:我想应聘保安或送外卖,挺艺术的
艺术青年葛宇路已经窝在老家武汉的家中小半个月了,工作毫无头绪。
生于1990年的他,最近作息黑白颠倒,每天坐在房间的桌前刷网页、看电影,有时他的父亲在凌晨起夜,看到他还没睡,会问他饿不饿。
 ▲曾经被收录进百度地图的“葛宇路” 图据东方IC 罗恒
▲曾经被收录进百度地图的“葛宇路” 图据东方IC 罗恒因为几年前用自己的名字“葛宇路”在北京命名了一条道路,却于今年夏天在网上引发了巨大争议,也改变着他的人生轨迹:“葛宇路”事件曝光之前,他是央美硕士研究生,毕业前的大半年时间耗在北京某高校的教师招聘上。如果不是因为毕业作品“葛宇路”的传播,他根本不会闯入公众视线,他在央美受的处分或许不会被报道并被大量关注,夏天过后,他本应会站在讲台谈“艺术”,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丢了工作,躲回武汉。
近日在武汉,他向红星新闻回忆起北京,包括用自己的名字给北京道路起名一事,常自我反思,但他说“很多时候很难想得那么明白”,又在天亮前昏昏睡去。
 ▲曾经出现在北京街头的“葛宇路”路牌 图据东方IC 罗恒
▲曾经出现在北京街头的“葛宇路”路牌 图据东方IC 罗恒新闻背景
葛宇路,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因为葛宇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了北京的一条无名道路(注:在2005年该路已被命名为“百子湾南一路”,2005(朝)地名命字0034号),结果该名称先后被高德地图、民政区划地名公共服务系统、百度地图等收录。
 ▲“葛宇路”早已被命名为“百子湾南一路” 图据东方IC
▲“葛宇路”早已被命名为“百子湾南一路” 图据东方IC此事后来在网上发酵引发关注和争议,今年7月12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官方微博通报了此事(见下图),市规划委工作人员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市民不可以私自命名道路,应由专门的地名办公室负责道路取名。朝阳区市政市容委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个人不能随意制作并悬挂路牌。

随即,葛宇路私设的“葛宇路”路牌被拆除。
 ▲正在被拆除的“葛宇路”路牌 图据北京青年报
▲正在被拆除的“葛宇路”路牌 图据北京青年报A
葛宇路命名“葛宇路”
被拆了路牌,还丢了北京工作
他心想,两个“葛宇路”没了
跟葛宇路见面是在晚饭时分武汉的一家书店。他坐在板凳上,戴个眼镜,穿着紫灰相间的条纹棉外套,眼睛小小的,手里的《白鹿原》已经看了一多半。他看起来更像程序员或者公务员,不太像“青年艺术家”。
他背一个黑色书包,最普通的一种。里面装了潜水衣和泳镜、摄影机和GoPro,这天他刚考完潜水证。之前他的一件作品掉落东湖,近来无事他又想起这个作品,学习潜水准备去湖中打捞。10月下旬的武汉阴雨连绵,气温陡降,教练告诉他水温太冷,贸然潜水会很危险,建议气温回升再说,打捞计划便搁置了。
 ▲接受红星新闻采访的葛宇路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接受红星新闻采访的葛宇路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他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外套袖口磨破的边,里面穿的是参加暑期 “禅学夏令营”时的白色禅服。“这都无所谓啦,能穿就行。”他的作品“葛宇路”已经卖给别人,挣的钱几乎都用在做展览上,“有钱先紧着做艺术展览花”。
他和记者在附近来回找吃饭的地方,他推荐不出来餐馆。虽说武汉是他的故乡,他说因读书离家几年,店换了一茬又一茬,选择令他为难。他说:“最近没有工作,实在没钱,不然该请你吃饭的。”
7月时他还有工作,是北京某高校的老师。为了能应聘上,他耗了大半年时间,有一关是做200多道心理测试,他还在网上找题目预演一番,结果是“阳光积极”。最后一轮面试,校领导在他对面坐了一排,向他许诺北京户口和免费单身公寓,一瞬间,他有了归属感。
但这种感觉并没有存在太久。
今年夏天,他的毕业作品“葛宇路”开始在网上刷屏。起因是2014年,葛宇路在北京百子湾发现一条无名路,他按照附近路牌的规格竖起了一块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葛宇路”路牌,3年内没人发觉异常,路名被百度地图、高德地图采用,为周围居民订外卖、打车提供便利。后来,葛宇路便将其作为了毕业作品。

 ▲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都曾收录显示“葛宇路” 图据网络
▲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都曾收录显示“葛宇路” 图据网络葛宇路和“葛宇路”火了,但他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一边对媒体讲述“葛宇路”创作过程,一边疲于应对私事。
 ▲葛宇路发微博澄清路牌事件 微博截图
▲葛宇路发微博澄清路牌事件 微博截图 ▲葛宇路因为路牌事件接受央视采访 央视报道截图
▲葛宇路因为路牌事件接受央视采访 央视报道截图7月13日下午,双井办事处牵头,街道城建科、双井城管执法队拆除了“葛宇路”路牌,后又在这条路上立起4块“百子湾南一路”的路牌。随后,葛宇路之前受到央美处分的事被报道,很快,北京那所高校客气地辞退了他。
他心想,完了,两个“葛宇路”都没了。
 ▲被拆下的“葛宇路”路牌 图据北京青年报
▲被拆下的“葛宇路”路牌 图据北京青年报而与此同时,葛宇路又成为了一个符号,商人的工作室想挂他的名挣钱,各种真人秀想让他上镜串场。
但他不愿意,“我当时要做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在北京,正常作息和饮食能让一个人不被落差击垮。他的老师安慰说,“你呀,这么不安稳,就算当老师也会觉得无聊。”
B
最初并不喜欢“葛宇路”
用自己的名字创作始于一次意外
他曾往湖里投糖果,希望喝的水能变甜
葛宇路讨厌追本溯源,作品火了,非得强调小时候有什么艺术天赋。他说自己小时候只是不想读书,才被父母送进一家艺术学校学绘画,三年后考进湖北美术学院。因为喜欢打游戏想报动画专业,却阴差阳选了“影像媒体艺术”。
大二时第一节影像媒体艺术课上,老师用影像让他看到全世界的当代艺术。有一对德国艺术家夫妇包裹了德国国会大厦,葛宇路感到很震撼,他觉得好又说不清怎么好,自此开始关注艺术。
葛宇路从不给艺术分类,也无法给艺术一个清晰的定义。他的大学朋友邓乾维还记得葛宇路所做的艺术尝试。湖美在一个岛上,临汤逊湖,岛上居民的饮用水来自此湖。上学的时候,葛宇路就朝湖里扔一颗糖,“挺美好的寓意,他希望岛上人喝的水可以变甜。”他还记得葛宇路当时在上课的路上每次都捡一块砖摆在教室楼前,日复一日,越积越多,“是一种时间的可视性。”
其实,葛宇路最初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小时候罚抄写名字,自己名字的笔画太多,他不喜欢。而且他觉得“宇路”听起来像女生,他也不喜欢。但现在,他开始审视这个上户口时被妈妈随口起的名字。
 ▲葛宇路
▲葛宇路在湖美读书后期,班上统计订教材人数,葛宇路自告奋勇先在黑板上写了“葛宇路”,后来者就接着他的名字写“×2”“×3”,名字没改,但数字增加。他的老师李巨川提议可以将这个创意用在公共空间里。湖美外墙上很多涂鸦,葛宇路把名字当涂鸦涂满外墙。一夜之间整条街,每块墙上都是黑色大字“葛宇路”,绵延一公里。
 ▲湖北美术学院外墙的“葛宇路”涂鸦至今仍依稀可见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湖北美术学院外墙的“葛宇路”涂鸦至今仍依稀可见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学校令其尽快涂抹干净。颜料洗不掉也刮不掉,葛宇路辗转买了和墙壁相同规格的水泥,他叫上几个哥们儿一起在深夜提着一桶桶水泥往墙上的“葛宇路”抹,一直弄到凌晨3、4点。他说抹掉涂鸦这件事很多人都不知道是谁干的,现在还有人在网上骂他:“葛宇路,你知道你让保洁阿姨多辛苦么?”
2012年,快要本科毕业的葛宇路决定考研。他想读中央美院实验艺术专业,选了宋冬做导师。第一年没考上,葛宇路北上,找了一份剪辑纪录片的工作,准备2013年的考研。
C
做了很多“葛宇路”路牌
这只是他多次“艺术实践”中的一种
留手机号陪聊,和摄像头对视
在北京,葛宇路喜欢胡同里丰富的烟火气。
下班后大家都会一拥而入,摊贩站在糖炒栗子刚出锅时的热气后,什么人都有,他们拐进胡同里,打开门钻进去不见了,不一会儿就传来电视剧的声音,再次出门又打扮得精神或者鲜亮一些。虽然北京艺术家聚集地有很多,但他都逐一避开。
提到葛宇路,他说,当时自己用KT板做了很多写有“葛宇路”的路牌,出门背着,看到哪条路没有名字就贴在墙上,最后只有百子湾的那块路牌保留了下来。他进一步将路牌做得符合规格,并当做了毕业作品。而如果没有人将这件事传到网上,这条路应该还在,他的朋友碰到后得知是葛宇路的作品,先是惊喜,随后说一句“意料之中”。
 ▲“葛宇路”路牌火了之后,还进入了美术馆展出 图据网络
▲“葛宇路”路牌火了之后,还进入了美术馆展出 图据网络北京的一些布告栏上贴着小广告。葛宇路想想自己能为这座城市做什么,于是他办了新的电话卡,贴了陪聊的小广告,上面留着新的手机号。他前前后后接了10多个电话,有时候上班正在剪片子也不得不跟打电话的人聊一个多小时。有人失恋,有人想跟他聊莫扎特、贝多芬。但那个手机号码欠费后,他没有再充话费,那次艺术“陪聊”的尝试就此作罢。
2014年,他考上中央美院的硕士研究生。葛宇路想,他不如将“艺术”扩大到在这个城市做点什么。
彼时,他正在为央美的一个老师整理摄像头拍下的素材。“如果我专门盯着摄像头,我的目光通过电波传到摄像头的那头,然后让那边的人知道有人想认识他,把他从摄像头后面盯出来,我们对话一下,还是蛮浪漫的。”
 ▲葛宇路和摄像头“对视” 受访者供图
▲葛宇路和摄像头“对视” 受访者供图之后的一个月,闲暇的下午他都让朋友帮忙搭脚手架,他坐在上面3个多小时,对着一个摄像头,直直地盯着。如果半天没有效果和反应,他就换另一个摄像头盯着。
最后,在央美旁边的一个小区,他终于得到了回应——有人喊他下来,“喂,小伙子,你在干嘛?”
葛宇路说:“我在用艺术的方式检测和修复监控机制。”
葛宇路还不死心,他问:“我可以去见见在摄像头里看到我的那个人吗?”但那位在摄像头里看到葛宇路的人赶走了他,说:“你这大脸吓死我了,跟蒙一块布有什么区别?”葛宇路的回答很艺术:“当然有区别,我们对视过啊!”
研究生毕业那段时间,葛宇路借宿在同学家的客厅一角,夏天,他把被子铺在地上,当时,他正等着搬进自己应聘上的北京某高校提供的单身公寓,去当一名老师。“葛宇路”事件发酵后,他的工作丢了,但他对不停搬家感到厌恶,犹豫之后还是想留在北京,便选择住在燕郊。
D
远离喧嚣,反思自我,又担心生计
想过应聘保安或者送外卖,“挺艺术的”
醉倒前他对朋友说,“先解决经济问题”
10月,他回到老家武汉,试图远离喧嚣,试图去想清楚一些事情,甚至试图还原当时为何做出那样的决定。他想总结一些经验,避免以后的问题。
在家里,他总是下午2点起床,跑去书店看书,晚上9点被店员催促离开,回家后回复一些邮件,然后在桌前刷网页、看电影。一部电影他能看很久,不停玩味,看电影时也掺杂着自己的现实困惑,“还是自己的原因,我总是在一些问题上判断失误。”
最近,葛宇路担心生计,想着去应聘保安或者去送外卖。他想,如果作为中央美院的研究生去做个保安挺艺术的,闲暇时间多,还可以思考怎么创作。
 ▲在湖北美术学院校外,葛宇路对K歌设备感到新奇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
▲在湖北美术学院校外,葛宇路对K歌设备感到新奇 图片来源:红星新闻这次回武汉,葛宇路的大学朋友邀他回学校叙旧,他答应了。毕业之后,葛宇路再没有回到学校,他也不知道这帮人现在在干什么。
组局人叫陈鹏欢,现在华中师范大学读研。他一边打电话一边向葛宇路介绍老友现状,他们中间的“灵魂人物”已经结婚生子,于鑫在学校附近开了工作室做家具生意,大部分人在考研或者准备读博,有一位还读了生物工程。
他们去华中科技大学接人,门口等人的时候陈鹏欢点了一支烟。他指着对面正在开发的楼盘跟葛宇路说:“宇哥,你搞艺术不如大一大二在这里买个房,当年1万现在3万,你卖作品才多少钱?”葛宇路笑笑没说话。陈鹏欢的朋友出来,他指着葛宇路向那女生介绍:“超级火,你可以上网搜搜。”女生将信将疑,用手机上网搜索完后惊喜地让陈鹏欢给他们合影。葛宇路全程呵呵笑道“不敢不敢”,乖巧地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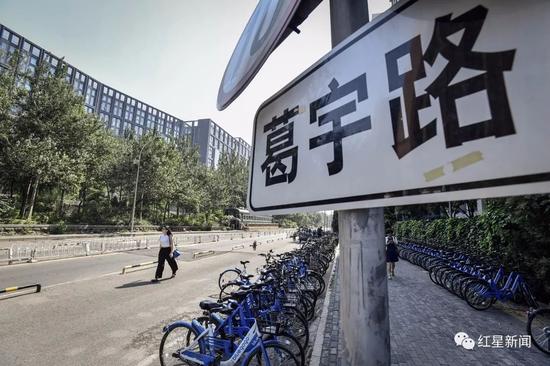 ▲曾经的“葛宇路”路牌 图据东方IC 罗恒
▲曾经的“葛宇路”路牌 图据东方IC 罗恒 ▲央视曾关注讨论“葛宇路事件” 央视报道截图
▲央视曾关注讨论“葛宇路事件” 央视报道截图湖美和这帮朋友给了葛宇路松弛的大学时光。当年,他们夜夜聚在一起喝酒,一个人提议晚上睡马路,一群人浩浩荡荡跟上。当年,也是这帮哥们帮葛宇路用水泥涂掉墙上的名字,那时,旁人围上来,抓着葛宇路的衣领嚣张地喊:“你就是葛宇路?”于鑫二话不说,上前推倒了那人,“我们不理解他做的东西,但是他是我哥们儿,我们都支持他。”酒桌上,于鑫主动聊起这件事。
葛宇路觉得这帮人如果搞艺术肯定更有想法,但最后只剩下自己还在做艺术。
那天葛宇路喝多了,被陈鹏欢和于鑫架着。陈鹏欢有点兴奋,对葛宇路说:“我要做你经纪人啊,我认真的。”有人想借葛宇路的名字挂牌工作室,但他都回绝了。葛宇路说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不能别人吹一下自己就飘起来了,这种挣钱方式只能是消耗自己,无益于做艺术。所以,他在醉倒之前回了一句:“你让我先解决经济问题再说。”
葛宇路说自己酒量很差。这次他喝了两口白酒之后,神情有点儿恍惚,他向一桌朋友提起白天陈鹏欢说买房的事情,随后他哈哈大笑,扔下一句,“当时我听完之后太心酸了。”
 ▲葛宇路的微信头像,图片上残留着“葛宇路”路牌的一角
▲葛宇路的微信头像,图片上残留着“葛宇路”路牌的一角来源:红星新闻
责任编辑: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