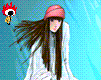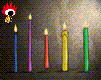| 驻足巴黎圣夏芒死亡火车站追忆死亡传说(组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5月15日13:59 新民周刊 | |||||||||
 本地最值得一看、历经数世纪未变的破屋顶  多尔多涅河平静的河水和两岸颇具特色的民居  在圣夏芒村,马尔罗曾经居住过的小城堡 撰稿/边 芹本刊驻巴黎特约记者 我决定跑到500多公里以外的中央高原,去看一个火车站。 巴黎以南要开出300公里,才走出单调的大平原,进入山区。经过奥尔良、夏托卢,到了利摩日,就已经算进了中央高原的大门,再往南走便是著名的奥弗涅山脉。越往南,山
在从蒂尔城沿120号国道向圣夏芒行驶的路上,景色很美,我竟然搜刮不出什么再好的形容词来,倒是这四个字比较平淡耐读。公路穿行在河谷间,曲曲弯弯,只见两边山体上新披的嫩绿,一波一波向后荡去。收音机里播着老歌,一首首似听非听地滑过去,就像这一切最深处的背景。忽然费里那略带沙哑的声音在唱:“爱,就是失去理智……”这样的布景里,听到这样一首歌,有一种包围着你的所有东西一时间都在融化的感觉。 为什么要去圣夏芒?在所有涉及安德烈·马尔罗的传记或回忆录里,这是个很少被提及的名字,他的很多简历上这一段经常是不存在的。他1942年至1944年在此逗留,当年租住的小城堡居然一无改变地伫立在公路边的山坡上,以至于在村边下车,一仰头就能看见。 我却并不是来看这座城堡的。我要看的是当年那个小火车站。 “心爱的的女人的死,就像晴天霹雳。” 120号国道到了圣夏芒便由于修路而中断了,我在傍晚走进村子,朝山上的城堡略看了几眼,便开始寻找那个小火车站。村子很小,要不了多久结果就出来了,令人失望:小火车站连同铁轨早在30年前便已全部扒掉。 我还是坚持找到了当年小火车站所在的地方。月台已是一片草地,铁道线已成河谷里的田野,一座现代化的多功能厅取代了当年的候车室,寂寞无主地立在村外田野边。1944年11月12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悲剧,已被时间涂抹得毫无缝隙了。 在《反回忆录》里,马尔罗写过这样一句话:“心爱的女人的死,就像晴天霹雳。”这个女人就是若塞特·克洛蒂斯,他的情人。 那一天,她送母亲上火车,就在这个小火车站,当车启动时,她在跳上月台的一刹那,失脚滑倒,被火车轧过,车轮将她的双腿压断。她没能熬到第二天便死了,从抵抗运动中匆匆抽身返回的马尔罗,未来得及见她最后一面。 她的临终遗言有不同版本,马尔罗在随笔《拉扎尔》中叙述的是这样一句话:“我从没有想过,死,是这样的。”她那位目睹车祸的女友提供了另一个版本,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喜欢你的香水味,不过现在……现在我很疼。” 我倾向于第二个版本,较符合真实;第一个版本更哲学,较符合马尔罗想象历史的风格。没有人想得到自己的死是什么样的。 这一年她34岁,就穿着被火车压碎的裙子入土了,连嵌进她那对美丽乳房的道碴也没有取出来。她留下两个儿子,一个不到两岁,一个四岁,马尔罗的非婚生子。 “死亡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它使所有在它之前发生的事都变得无可挽回。” 我对被突然中断的生命有一种特别的情感,我从未谋面的爷爷、我那在一个街口被车撞死的父亲都是这种命运。生命中遭遇过这种事情的人,不再相信永恒,他只知道一切都可能被停下来,被拿走,好像从来就没有属于过你,再说属于这个词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生命好像是被什么东西安排好的,说走就走了,在突然割裂的那个断层上,永远留着新鲜的、神秘的伤口。那道割缝像一个只能是天意的完美的杰作。以至于过去的和未来的都已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那一刹那。 马尔罗在小说《希望》中写过:“死亡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它使所有在它之前发生的事都变得无可挽回。”实际上何须死亡! 暴死有一种残酷的美感,我也是过了好久才明白的。 在她留下的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现在读起来,仿佛巫师的咒语,好像她早已预言了自己的死亡:“寒冷从脚底升起,仿佛沉入比寒冷更糟的彻骨的冰冷中。你感到你终将被它淹没……这寒冷裹挟着,压迫着,你知道吗,像沉重的东西压在你身上;好像永远永远都卸不去。五秒钟内,也许更长一些,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不再呼吸了。一切到此结束,那扇门开了,我走了。” 我是在一个极偶然的情况下听到她的名字的,马尔罗并没有为她写过什么纪念文字,在他的作品中只有绝少的几处提到她,而且只有片言只语。整个一部谈死亡的《拉扎尔》,也只有一句给了她。她未完成的手稿和遗照就像被收进魔术盒一样被集在一只小皮箱里,这只箱子并不在马尔罗手里,或者说他并没有试图拥有这只箱子。1945年后,他成了政府要员,他的生活已远远走出这只箱子的范围了。 我却在这个像影子一样一晃而逝的人物身上,看到了让文学都显得苍白的东西。命运最绝妙的一笔是意想不到的死亡。我承认是这种死亡深深抓住了我,这是一种具有致命吸引力的东西,因为它非人类的智慧能够解释。我也是在面对这样的死亡之后才明白,人类所有形而上学的东西都是面对死亡得来的。 “什么样的世界可以不付代价地去发现?” 有人靠文字和思想留下一部书,有人其生命本身就是一部书。若塞特就属于这后一种。我想起她二十岁出头时说过的一句话:“存在要趁早,年轻并不是本钱。”人在多大程度上无意识地预定了自己的命运! 见过她的人说她像30年代的电影明星,我看过她的一张照片,是那种古罗马雕塑似的美,古典而保守,今人的审美观未必喜欢。也就是这种美最初吸引了马尔罗。马尔罗的眼睛是专为美而生成的,这是一种天生的敏感。 那是1932年。她作为年轻的外省才女刚刚走入文坛,来到巴黎;他却早已成名,是巴黎左翼文人中的一员干将。她的处女作《绿色时光》刚刚由加利马出版社出版,不过一本书在巴黎知识分子圈里不过如石入海,倒是她的年轻和金发碧眼更引起异性同行的注意。 位于巴黎七区塞巴斯蒂安·博旦街(今天的巴克街)7号的《新法兰西杂志》社是文人们的聚会点,有纪德、圣-埃克絮佩里和妻子贡苏萝,有马丁·杜加尔、德里厄·拉罗歇尔、路易·阿拉贡……当然还有马尔罗。有一天,在杂志社的走廊里,她与他擦肩而过,他披在肩上的浅色大衣的衣角轻轻拂过她的身体,令她一阵颤栗。就这么一下,几秒钟的四目相对。很快她听到身后办公室里有人在向他道贺,他刚刚得了个女儿,克拉拉(马尔罗的妻子)生的。 他们经常有机会在出版商加利马家每星期天的午餐会上碰面,地点:卢森堡公园南面的梅杉街。不过那主要是这群目空一切的精神世界的王子们的聚会,她是插不上嘴的。两人第一次“交锋”是在1932年11月的一次招待会上,众人在议论某人坠入了情网。她脱口而出: “可他是结过婚的人。” 马尔罗正好在她身边,他带着“极大的惊讶”表情问道: “两者有什么关系吗?” 作为一切的开始,这段对话妙不可言,人生的某些场景就像有人导演过一样,你不得不惊叹生活有时比小说更精彩,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 1933年春,马尔罗发表了小说《人的境遇》,这本书彻底奠定了他在30年代文坛的地位。这时她已注意到他有时投向她的目光带着一点别样的关注和热情。但那是不说明问题的,眼睛不过是人体最大胆的器官。 又一次聚餐,人不多。她喝多了一点,胆子变大,说她赞成肉体自由。有人反对,说女人有先天的限制。她听马尔罗在说: “什么也没有尝试过的人,其悔恨不是不沉重,只是不那么显而易见。” 一群人又在七嘴八舌,马尔罗的声音再次传进她已微微晕醉的心田: “什么样的世界可以不付代价地去发现?” 她想起小时候父亲给她买过一只玩具猫,她非常喜欢,从不离手。但有一天,一只真猫走过她身边,她情不自禁一把就扔掉了玩具猫。“在这群男人中,马尔罗就像那只玩具猫中的真猫。” 第二天,她收到他的一张便条,约她单独午餐。就像她在几年以后意识到的,她选择了“灯蛾扑火”。这倒颇符合她20岁时的人生哲学“存在要趁早”,瞬间的闪光要胜过一个世纪在黑暗中的飞行。 这一年12月7日晚上,她与从外省来的父母共进晚餐。她在父亲放在饭店长椅上的报纸上,看见马尔罗获得了“龚古尔奖”。她奔去打电话,他在家里,约她在圣日尔曼大街的利普咖啡馆见面。她去了,人山人海,她走不过去。 我感叹那个一去不复返的年代文学的力量,那种磁石般的对周围世界的吸引力到哪里去了?我们这一代将为我们的迟到付出多大的代价? 第二天,电话响了,是马尔罗,约她在旺多姆广场的丽兹饭店午餐。这时,克拉拉在哪儿?她去巴勒斯坦了,一个偶然。不过走的人永远都有错的,不是吗? 吃完饭,就在侍者去拿他们放在寄存处的大衣时,他忽然目光望着别处快速地说了一句: “如果一个男人建议你和他共度一个月而没有明确的未来,你能做到这一点而不要求更多的东西吗?说实话,我认识的女人中,没有人会这么做。” 她说:“重要的是这个月有31天。不管怎么样,头一天,人都自以为能做到。” 载着他们的出租车穿过协和广场,忽然她感觉到马尔罗的头凑近她的衣领,接着是那两片喜欢美食的嘴唇。那座她好像望了一百年的石头雕塑,突然之间在她眼前活了起来。不多不少,就是这种感觉。 “一无所用的措施” 几年以后的一天,在他们幽会的旅馆里,他朦朦胧胧地搂着她睡着了,她大睁着眼睛望着沉浸在淡淡的温热中的房间。“他们之间除了这闪电般的爱的瞬间还有什么?” 永远是到问这句话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复杂了。她写道:“我知道不应该将目光投出鼻子尖底下那一块。” 1938年马尔罗带她去西班牙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希望》,这时小说《希望》已经出版,还有此前的《蔑视的时代》。她也写了第二本小说《一无所用的措施》,不过仅此而已,她的生活本身似乎已大大超过她的写作。而这种生活就是:等待、约会、分离。每一次回到巴黎或从一家旅馆出来,就像灰姑娘的午夜十二点,他匆匆与她告别,回到他与克拉拉位于巴克街的寓所。巴克街44号如今原封未动地依然立在圣日尔曼大街与巴克街交汇的那个街口,黑色的高大楼门上方有一块小牌子,写着马尔罗在此完成《人的境遇》。这是唯一留下纪念牌的地方。 说实话,写到这里,我有点不忍再写下去。要是他们都遵守那一个月的约定?可惜我不是电影剪辑师,我没有魔术师的本领,让生活定格在最灿烂的一章。只有那神奇的死亡之手可以结束生命这一小小的故事。这五月的傍晚,一切都并非在显示生命该在何时结束或在何时开始。天已变得一日长似一日,日落未落这段时间被拉得很长,太阳拖着橘黄色的斜长的影子,让目光所及的一切都超出了它们寻常的价值。我从旧火车站遗址,穿过静无一人的村庄,再拐上一条两边长满野草的山路,上到城堡门口。朝山下望去,是一片本地最值得一看、历经数世纪未变的石片屋顶,那大小、形状不齐的石片,一块挂着一块,鱼鳞般地勾勒出略带弧形的线条,让你充分感觉到地域与人的智慧结合出的那种非此莫有的美。 我知道她在这里生下第二个孩子樊尚,长子戈捷是在战火中的巴黎出生的。戈捷的孕育多少出自她的算计,二战打响了,马尔罗被征招入伍,如果他一去不回,她手中除了记忆之处,没有任何他们过往生活的凭据。于是她耍了个心眼。 他驻防普罗万(注:巴黎东南部的一个小城)的时候,她怀着两个月的身孕去看他。因为这个他不想要的孩子,他们在争吵中分手。她回到战乱中的巴黎,无头苍蝇似地找一家地下诊室堕胎(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堕胎在法国是违法的)。但是那个西班牙女人和当手术室用的肮脏的厨房,让她望了却步了。她有没有想起马尔罗点起她心中之火的那个晚上说过的话?没有一种自由不让人付出代价。 何况她已经明白,一旦超出“那31天”的约定,背景就已经转换了。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还能拴住他多久,让他被迫生活在一个已经疲惫而不幸的女人身边?克拉拉已经这样做过了,做了十四五年。”那是1940年,她30岁。好像生活已经进行到这样,任何转弯都缺少必要的力量。她只能抓住他,仿佛抓住青春的尾巴。不过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任何算计都是徒劳的,一如她的小说的名字:“一无所用的措施”,运气就像风向一样让人难以捉摸。 “除了死亡这一绝对的现实,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城堡的花园里长了没膝高的青草,但并不荒凉,因为满是新绿,山区的春天来得晚。我看到那眼水井,周边的铁器完全锈了,据说当年马尔罗把香槟酒和鹅肝酱冰在这井里,他这么个喜欢热闹的人跑到这偏僻的山里,就是因为这里是当时法国唯一还找得到丰盛食品的地方。所有和他亲近的人都没有他的运气,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洛朗和克洛德没有他的名气,却是在抵抗运动最没有希望的时候,参与了地下活动。洛朗1944年3月被捕,在胜利前死于德国集中营,据说是盟军飞机炸的。同年4月,若塞特抱着戈捷到巴黎去会马尔罗,在里昂火车站的月台上,她和被盖世太保押解的克洛德迎面而过,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她惊得喘不过气来,把孩子的小脸扭到一边,生怕他叫一声“小叔”。克洛德被德国人枪毙了。从这时起马尔罗才走入抵抗运动,并且恰逢其时。战后,他娶了洛朗的遗孀玛德兰。 那个我在旧照片上看过的石台阶还在,长满青苔,嵌在荒草中。曾经在这个石阶上被摄入镜头的人,除了马尔罗自己,没有寿终正寝的。仿佛他们都没有时间停留,只是他身边匆匆的过客。他一生的最后一本书就取名《过客》。 就在她最后去巴黎的那次,马尔罗买了个订婚戒指送给她,并且保证战后就跟克拉拉离婚。她几年前在里昂火车站站前广场那家旅店里的小小“计谋”,终让她尝到了正果。如果不是命运之手做了另外的安排…… 出事那天,她被从车轮下拉出,送到蒂尔城医院。恰好有一辆汽车翻了,医院里全是伤员,没人顾得上她。一切都是那样的巧合。你可以说这是偶然,偶然可以解释一切。据说她很平静,没有叫一声,也没有提到两个孩子。她大概绝想不到,跟她有关的东西都将消失,而且很快。包括那个火车站。 1960年5月23日,两个男孩,二十岁的戈捷和尚不满十八岁的樊尚,从地中海边驾车返回巴黎,途经巴黎与里昂之间的小城博纳时,撞上了一棵树。这是一条笔直的公路,让人无法解释。两人当场死亡,时间是晚上8点20分……博纳,他们生母在南方的家乡恰好也叫这个名字。 冥冥中好像有一只大手,把涉及这个女人的所有物质的东西都一一去除了,除了巴黎二十区那个小到市区图上几乎看不到的夏罗纳公墓。母子三人合葬在这里,墓上没有一束鲜花,和葬在先贤祠里的马尔罗相距何其远。 “除了死亡这一绝对的现实,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马尔罗在《西方的欲望》中这样写过。 我告别城堡走下山时,夜幕迟迟没有降临,这份迟滞让人产生生命无尽的幻觉。但那只是幻觉。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际新闻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