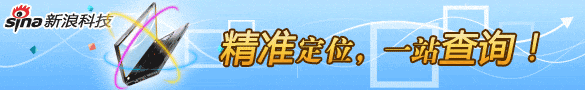探访MIT媒体实验室


创意以一种最纯粹的形式发生
——探访MIT媒体实验室
“以前我们想到技术,总是在谈人工智能,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
记者◎陈赛
关于媒体实验室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他们发明了一个会跑的闹钟,闹钟一响就满地跑,横冲直撞,你必须斗智斗勇,才能抓住它,把它关掉。后来这个发明被改造成了一个流行商品,叫Clocky。有人看不过,批评说,一群科学家聚在一起,就为了发明这么个玩意儿?但是,媒体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不以为忤,反而洋洋自得,认为发明也要有娱乐精神,我们不怕犯傻。即使在MIT,媒体实验室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
MIT的低调平实,反映在校园风景上,简直像一个大工厂,所有的楼都是用数字代码。我眼前的这个建筑也一样,编码E15,事实上,对科学家来说,它未免太精致了一点。从外面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盒子。楼里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白色的。当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玻璃墙,大厅里空荡荡的,你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雪花球。这是媒体实验室的新楼,8个月前才刚刚落成,耗资1亿美元,是日本建筑师槙文彦的作品。
这里有一种奇异的透明度。你在楼里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能轻易看到每个角落的人在做什么。“视觉上的透明,代表了一种智力上的透明。”弗兰克·莫斯,媒体实验室的主任这样告诉我。弗兰克·莫斯一头白发,精力过人,他的热情有一种强烈的传染力。这大概是他作为一位企业家,却能领导媒体实验室的原因之一。他也曾经是MIT的学生,拿到航空航天工程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却转向IT行业。在加盟媒体实验室之前,他经营好几家IT企业和生物科技公司。
因为刚刚搬进新楼不久,很多人的案头还摆满了杂乱的书本、器械和实验材料。上上下下走一圈,很快就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机器的气场。机械腿散落在沙发上,可以折叠的摩托车蹲在角落里,机器人从架子上冷眼看着你。这并不奇怪,媒体实验室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研究人与机器的关系。但是逛久了,你也会发现许多轻盈可爱、充满人情味的发明。
在一个叫Tangible Media的小组,我看到几个设计得非常雅致的玻璃瓶,揭开瓶盖,就有音乐冒出来。如果外面天气晴朗,玻璃瓶会发出鸟鸣的声音,如果下雨,瓶子则发出雨的声音。原来玻璃瓶也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的容器,而且处理得如此诗意。这个小组的导师是个日本人,叫石井裕。“音乐瓶”就是他为自己的母亲设计的。此人似乎很低调,媒体上基本看不到对他的报道。约翰·昂德科夫勒是从这个小组走出去的名人,《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斯戴着手套用手势捕捉屏幕的镜头,就是他设计的。这人在MIT得到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部学位,还是个文艺青年,喜欢在树下读歌德。他在媒体实验室待了十几年,后来开了自己的公司,试图把电影里那种手势界面系统推广到真实世界。
媒体实验室一直对人与世界之间的界面感兴趣。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研究界面的小组“流动界面”,由美丽的比利时女教授派蒂·梅斯(Pattie Maes)领导。她不喜欢一切手持设备,包括iphone,认为都是不自然的界面。她的目标是消灭这些设备,把它们的功能释放到日常生活的材质里。与其让我们“移民”到数字世界,为什么不让数字技术融入到我们的真实世界里来?“流动界面”有一个叫“第六感”的设备,去年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几乎成了媒体实验室的活招牌。在国内时就有不少朋友给我发过视频,可惜“天才”印度学生普拉纳夫没有在实验室,无缘得见。“第六感”由超便携投影仪、摄像头、手机和可穿戴式指套构成,可以挂在脖子上,当一个人带着这套设备靠近任何物体时,信息就会被投影到物体表面上,人就可以与真实物体进行交互了。你可以用手势拍照片,躺在沙发上编辑天花板上的图片,甚至在手掌心里拨打电话号码。其实,“第六感”的每一种技术都已经很成熟,只不过他们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把它实现出来而已。
这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一堆电子积木,叫Siftables,每一块积木都有屏幕和无线装置,彼此之间能互相感应。你可以把它们挪来挪去,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效果。比如,如果两块积木上分别显示两个不同的人像,把他们放在一起,积木里的人像会对彼此产生兴趣。如果被包围的话,他们一样会察觉,会显得有点慌张。就像哈利·波特里那些会说话的人像。它还可以用来做数学题,玩拼字游戏,编辑照片,玩DJ,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小玩具。
“终身幼儿园”小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布置得像个幼儿园,到处都是玩具,颜色鲜艳,窗户上趴着一只乐高玩具做成的大蜘蛛。这个小组的负责人米歇尔·雷斯尼克教授有一个信仰,认为孩子们应该通过建造东西来学习,培养创造力。人们不仅应该在儿童期间玩更多像乐高积木这样的玩具,而且这种爱好应该陪伴他们一生。他利用乐高玩具的原理,为小朋友开发了一个开源的编程语言平台叫Scratch,孩子们可以用这套软件来创造自己的故事、游戏和视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一种发现的过程。而且,作为数字一代,他们愿意互相分享。Scratch已经制造了100多万个故事。
在三层的休息区有一个乒乓球台,两个学生正在玩乒乓球。如果打开旁边的一个投影仪,这张乒乓球桌就变成了一个屏幕,上面有小鱼在游动,乒乓球击打桌面的方向和力度会改变小鱼的游向,于是一场乒乓球赛可以变成一场游戏。这是一个中国女孩萧潇的作品。她在北京出生,15年前来美国,汉语已经不大利落了。她在MIT学计算机科学,辅修建筑学。她从本科开始就在媒体实验室实习,现在正在这里攻读硕士学位。她是一名钢琴手,所以她发明的界面与音乐有点关系。媒体实验室的中国留学生很少,萧潇在MIT接受本科教育,所以很容易就融入这里的文化。但对于那些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却往往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文化适应。
“刚来媒体实验室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学生。我的数学编程能力很强,任何人给我一个题目,我都能很好地帮他解决。”沈大嵬,媒体实验室的一位中国研究员告诉我,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正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我每天缠住导师,问我该干点什么。导师说,那你就干点什么好了。”他说他花了4年的时间,才渐渐适应这里的思维习惯,“你不应该等着导师给你活干,而是自己去找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一个别人没有找到的角度,然后想办法解决它”。
从15年前起,“媒体”这个词早已不再适用于这个实验室。他们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概念的“媒体”:智能车、人工腿、改造大脑、拓展记忆、情感机器人……这些五花八门的研究,如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拓展人类”。
“以前我们想到技术,总是在谈人工智能,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莫斯教授说。
但是,在这里,有一些东西始终没有变。25年前,媒体实验室刚成立的时候,作为创始人,当时MIT的校长杰罗姆·韦斯纳(Jerome Weisner)和尼葛洛庞帝教授就认为,科学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交叉领域。所以,除了科学家之外,他们当时还邀请了许多艺术家一起加盟实验室。从此,“多学科”被作为一种传统在媒体实验室保留了下来。
今天的媒体实验室,一共有25个教授,带领着25个小组,每个小组6个研究员,都是MIT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这些教授和学生很多都是“博学者”,你随便在这里遇到一个人,他很可能精通5个领域的研究。到最后你会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学科的概念。在参观完媒体实验室,弗兰克·莫斯接受了我的采访,谈论他对科技的见解——
“无论世界上哪一所大学,MIT、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或者亚洲的大学,在过去的数百年,甚至更远的年代里,一直都是划分不同的学科。比如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社会科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总体来说,每个领域的研究者都会固守自己的领域,只有偶尔,才会与别人相连。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将无法再单独的领域里面解决,而是必须由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生物学家,彼此互相关联,在一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中共同解决。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健康。很多让我们照顾自己健康的方法,必须结合生物学、计算机、思维与行为科学、化学的理解才有可能实现。”
“媒体实验室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我们的研究是没有方向的(undirected)。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研究型实验室、学院派实验室、工业界实验室或者政府研究所,你所得到的项目资金必须要求你的研究方向一致,比如治疗某种癌症,保证某种计算机网络的隐私安全,这些都是有方向的问题,但我们没有。”
之所以能在科研上有这种自由度,是因为这个实验室独特的筹款模式。他们每年3000多万美元的资助来自60多家知名的大企业,包括Google、微软、Hasbrow、时代华纳、LG、三星等。这些企业掏钱,但并不干涉实验室的研究。作为回报,企业可以派人观察实验室怎么创造,怎么创新,如果他们从某种发明中看到商机,必须向媒体实验室申请授权。
有时候,他们经常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为马友友设计“超级大提琴”时,托德·曼库弗教授发现了一种技术,能测量身体在环境中的位置和姿势,后来一家日本公司看到这个发明,把它应用在汽车的儿童座位上,用来测量孩子坐的姿势对不对,是不是在动,以保护儿童在车内的安全。现在,几乎全世界每辆车里都使用了这样的技术。
“这个时代,技术更新太快,世界变化太快,每个公司、政府、组织,都意识到创新对于未来成功的重要性。你必须创新,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由激情驱动的地方。”弗兰克·莫斯说。
“在这里,你的激情和兴趣决定你的研究方向。休·赫尔教授的激情是消灭残疾,他自己17岁的时候失去了双腿;威廉·米切尔教授(已经去世)的激情是让城市和建筑变得更加智能化;雷斯尼克教授的激情是让每个人的一生都保持孩子在幼儿园时代的好奇心,通过创造和建造事物的方式来学习,从而创造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托德·曼库弗教授的激情是让每个人都能创作音乐,从音乐中获得意义。至于我自己的激情,是让每个人能在余生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当你变老,你需要帮助,但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些老人获得独立生活,但技术可以做到。我的母亲老了,她的背不好,所以总是坐着。每次我扶着她走路时就想,为什么我母亲不能继续走路?我想,总有一种技术,能让她重新走路。她也许不能再跑步,做她三四十岁时候做的事情,但至少可以舒服地走路。人老了,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变得虚弱,手脚、心脏,有太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了。我希望能看到我母亲重新开始走路、逛街、做饭,这是我的激情。”莫斯教授在媒体实验室主持一个叫“新媒体医学”的小组,算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他的目标是改变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弊端,使病人能够平等参与到治疗中,对自己的健康和信息有更多的控制权。“一直以来,MIT解决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人的问题,但是,仅仅为既有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不够的。媒体实验室更看重的是提问,提出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时代的挑战在于,要提出新的,不同以往的问题。时代进步了,我们更健康,经济更发展了,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在提出新问题上是失败的。你看今天的世界,技术给了我们许多信息,你能Google任何问题,但你不觉得自己对这些信息有控制感。尽管有这么多的信息,它并不能减少你对自己的健康、财务的忧虑。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我们怎么利用这些飞速发展的技术,传播技术,信息技术,帮助人们控制自己的健康、财富和幸福?”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