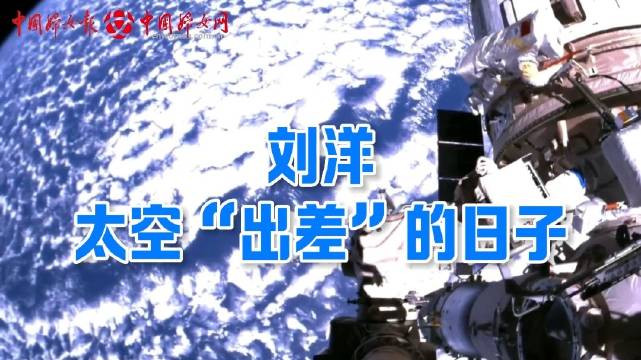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刘心洁抵达校门口时,已经有很多同学在此等车离开了。
刘心洁抵达校门口时,已经有很多同学在此等车离开了。刘心洁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像新闻里那些在外务工返乡人员一样,流落在机场等待命运的安排。那天晚上,这位大学研二的学生,在首都机场里呆坐一个晚上,她才第一次知道,外观看起来现代又气派的机场,在夜里也是会呼呼漏风的。
从11月上旬以来,各地高校陆续以“学生阳性病例增多”“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由,告知学生可以自愿申请返乡;11月25日前后,多所学校催促学生返乡,呼吁“非必要不留校”;至29日前后,部分学校的政策突然收紧,甚至下了“最后通牒”——太原一所高校明令要求学生12月4日前“能返尽返”,否则不予离校。
茫然和不知所措的情绪在学生中蔓延,甚至引起了恐慌,他们搞不清楚疫情究竟有多严重,愈加害怕感染。有些学校尽量做好学生的返乡工作,安排了闭环转运,但也有些学校并没有给予学生应有的帮助。而在这期间,原本安排好的网课也已经不再重要,很多课程考试推迟到下学期进行,四六级考试延期,大家开始哄抢高铁和飞机票,预约单程两千块钱的“天价”出租车,打遍了社区防疫办、市长热线、政府服务热线等举报电话。
而另一个挑战是返乡之后的境遇——“幸运”的学生只需居家观察三天两检,“运气不好”的则要在凌晨的高速路口等待一整晚,在严寒中和防疫人员拉扯,乞求不要遣返。
目前,针对大学生返乡的最新相关规定还停留在今年6月5日,在那天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政府提出“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返乡学生如需隔离,各地应免除学生隔离费用”。而在现实中,返乡之途依然充满各种不确定性——除了拼各地五花八门的防疫政策,还要拼运气。
仓皇之中
11月29日晚,刘心洁所在学校突然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同学们赶紧返乡,“再不走就走不了了”。刘心洁赶紧搜索到第二天的航班,顾不上价钱高低,花了平常机票的三倍价格买到了第二天一早的航班,同时和父母知会了一声,找到了一位还在校的同学一起,拎起箱子便冲出了宿舍。到达校门口时,目之所及全是拎着箱子仓皇而逃的学生。
而就在12小时前的29日凌晨时分,刘心洁刚接到通知说,由于她昨日做的核酸中发现了“十混一”阳性,按学校规定,她需要在学校隔离7天才可返乡,于是她不得不退掉了29日的飞机票,本以为这下走不成了。
那天晚上,宿舍里只剩刘心洁一人,心情起起伏伏。室友和周围宿舍的好友这几日都陆续返乡了,其中一位买不到高铁票,还坐了9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回去。而她本是最早一个买到票的,却在机票被取消两次后落了单。刘心洁想到未知的明天,还有空空荡荡的宿舍楼,忐忑不安。这一晚,她通宵开着灯,半梦半醒地只睡了三四个小时。
29日晚上7点,校方又突然召开紧急会议,让滞留在学校的学生赶紧都回家。于是,刘心洁急忙买了30日的机票,第二天早早就赶往机场。
 广州某学校催促学生返乡的聊天截图。
广州某学校催促学生返乡的聊天截图。到达机场后,时间还早,刘心洁决定先找个宾馆落脚。然而几通电话下来,才发现机场周围的酒店都已经住满了,离机场远一些的酒店则明确表示,“不接收朝阳区来的顾客”。
无奈之下,刘心洁和同学就在候机大厅找了一排空着的座位“下榻”了,四周也都是拎着箱子学生模样的人。那一晚,刘心洁穿着羽绒服,围了厚围巾,仍能感到机场上方不断有风灌下来,冻得她瑟瑟发抖。
在候机厅的长椅上,刘心洁和同学很困却又睡不着。她们眯一会儿再聊一会儿天,再眯一会儿,打发着时间。她们聊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离开学校,还是顾虑回家后学习效率太差;也聊到马上就要面临的找工作的问题——听上一届的学长们反馈,这几年合适的工作很难找,越来越“卷”了。
“感觉这个学期还没怎么过,就又结束了。”聊天中她们感慨道。这个学期,活动区域在一步步缩小:刘心洁住在校外一个单独的校区,9月份,还能通过刷身份证到主校区自习;10月份之后就只能在自己的校区活动,一栋宿舍楼、一个小食堂和一家店面很小的超市是她所有的活动空间;10月底,宿舍楼也封了。。。。。。
天亮时分,几乎一夜没睡的刘心洁拖着疲惫的身躯过了安检。她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机器人,失去了任何情绪,只想把一道道程序走完,“太累了,有情绪只会让自己更加疲惫”。她有些头疼和胃疼,想去买些食物,然而机场所有的商店都关了。她从书包里拿出仅剩的一块面包,就着凉水吃掉了。
窗外是灰蒙蒙的天,刘心洁对自己说:“太阳一定会出来的。”
接下来,刘心洁的航班还是“不出意外”的晚点了。等待两小时,然后起飞,抵达深圳,按要求做核酸、报备,让父母按要求把车停在指定位置,拍照给她,她出示给工作人员看,然后由工作人员“护送”她见到了父母。
终于到了!那天晚上,她闷头睡了15个小时。
就在29日晚,除了在北京上学的刘心洁,广州、郑州的多所高校都突然下达了紧急返乡的通知。有的同学在机场过夜,有的同学在火车站瑟缩着等车,有的同学为了天价包车费和司机讨价还价…
 一名学生返回延安后,被拉去集中隔离。
一名学生返回延安后,被拉去集中隔离。隔离的空房子
事实上,刘心洁算是返乡大军里比较“幸运”的一个,因为她所投奔的深圳市对外地返乡人士没有“层层加码”。而对于许多返乡的人而言,抵达家乡只是另一段漫长征途的开始。
目前,对于大学生返乡后如何进行隔离、居家观测,各地要求都不一样。据记者了解,一些管理较为人性化的地方会要求学生返乡后进行3天到7天的健康检测;但也有一些地区,不论学生是从何地返乡,一律实行集中隔离;若不满足集中隔离条件,部分乡镇会要求学生找一处“空房子”自己进行居家隔离,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均实施这种政策。
金姗姗是在北京念大二的学生,家在甘肃省金昌市。返乡前一日,金姗姗特意问过当地社区抵达后的政策,对方回复目前施行的是“3+4”政策,即3天集中隔离+4天居家隔离,返乡人士到达后会有专人接至隔离酒店。
然而仅一天后,隔离政策就变了。11月28日,金姗姗在中午12时左右抵达金昌,在办理登记报备等一系列流程时,社区工作人员告诉金姗姗,由于目前隔离酒店不足,隔离政策改为“2+5”,即2天集中隔离+5天居家隔离。金姗姗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出示有关文件,对方回应说,“没有文件,开会下达的”。
金姗姗在机场等了4个小时,终于等来了拉她去酒店的包车。司机给她发放了酒店房卡,收取了120一天的房费,并告知酒店不提供食物,三餐需自己解决。
到达酒店后,金姗姗却发现酒店里根本无人看守,也不需要进行入住登记,酒店房间门也可以随意打开进出,“完全不像认真防疫的样子”。
金姗姗刚刚安顿下来,却又突然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政策改为了7天居家隔离,要求不得与他人同住”。此时距离金姗姗入住只有两个小时。
接着,酒店退还了金姗姗60元房费,扣留了行李箱进行消杀,并安排专人盯着,让她“无接触式”返家。金姗姗说,当时酒店那边不准父母来接,整个金昌市又处于“静默”状态,公共交通停摆,她只好自己骑共享单车返家,同时告诉家人去酒店取被扣下的行李箱。最终,金姗姗和妈妈在小区门口隔着大门“相见”,妈妈远远地把行李箱和家里钥匙放下,她去取走,然后回家开始7天隔离,妈妈则去姥姥家借住。
“这一切都太魔幻了。”金姗姗说,隔离政策一天一变,甚至一天几变。就在金姗姗返乡的两天前,她的表弟经历的又是另一个版本的政策安排——当天下午6点到达高速路口后,表弟等了一整晚,直到凌晨4点社区才派人去接,并安排他住进了两人一间的隔离房间。
金姗姗最终得以回家隔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妈妈能够去亲戚家借住,但对于很多学生来说,特别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很多家庭都是三代人同住,找一间空房子进行单独隔离并不容易。
 范存隔离的空房子。
范存隔离的空房子。家在河北省邢台市某村的范存就隔离在一所“真正的空房子”里,与鸽子同住。用她自嘲的说法,自己被隔离在“鸽子窝”里了。
范存从张家口的学校返乡前,曾与家人商量过该去哪里隔离合适。当时,家附近的隔离酒店已经住满,家中是父母、弟弟、爷爷奶奶五口人同住,如果回家隔离,按村里要求家人也都要一同进行隔离,这就会使得作为村支书的父亲无法上班,母亲也无法去地里收苹果,一旦错过收获的季节,损失严重,于是才想到了家里的老房子。
老房子很久没住过人了,相当破败。之前,赶上旅游业旺盛的时候,老房子被开发成了民宿,曾为这个小家庭带来不少收益。然而三年疫情下来,村里的旅游业早就凋敝了,老房子也就一直空置着。在最西边的屋子里,范存的父亲养了近二十只鸽子,范存就住在鸽子屋的隔壁,屋里有一张双人床、一个立式衣柜和一张桌子,还有一整片可移动式暖气片,都是此前做民宿时留下来的。
隔离的日子里,由于大门年久失修全是厚厚的灰尘,范存从不开门,每当有人来给她做核酸,她就到院子南边,踩着鸽子笼扒着墙,探出头去做核酸。做完核酸,她会铲一大勺玉米粒,撒在鸽子屋的食槽里。
范存说,老房子的冷还能忍受,最让她受不了的,是每次上厕所,都要从院子里的西屋穿过一片空地,再踩着一堆杂物走进厕所。厕所里的马桶早就被拆除了,所谓的“厕所”其实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到了晚上,这段路一片漆黑,很吓人。范存只好尽量少喝水,如果晚上实在忍不住要去厕所,就先在屋里的盆里解决,第二天天亮再倒进厕所里。
范存并不敢对村里的防疫措施提出质疑,甚至“害怕被打”。虽然爸爸是村支书,但整个村的民风都很彪悍,有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就会把人给得罪了。范存告诉记者,之前村里有过密接人员,被拉去隔离点集中隔离,但有一位次密接人员也要求一起去隔离,因为在隔离点可以免费吃住,当时范存的爸爸作为村支书没有同意这位村民的要求,结果后来就被这位村民举报了。
很多村民都认为,从外地返乡的人身上都“携带病毒”,而且“这个病毒很可怕”。范存回到家乡的那天,父亲去接她,一见面就给她进行了全身消杀,喷洒在身上的消毒水半个小时后才干透。刚开始时不让她说话,要等20分钟后消杀发挥作用了才能开口讲话。
何时是归期
目前,仍有一些学生滞留学校,在学校催促返乡的通知反复下达之中,进退两难。
家在河南濮阳的李允还在为返乡后不去集中隔离而做最后的争取。她没想到,同一个城市里,不同的区之间隔离政策也可以不一致。她先是问了自己家所在的社区,要求是集中隔离;又问了家中另一套房所在社区,则是居家隔离就可以。
李允感到很纳闷。她连续几天不断拨打了社区电话、物业电话、市长热线、12345等各方电话,结果发现各方相互踢皮球。
李允给记者发了一张“防疫强制措施吵架指北”,表示她为了维权做足了功课,但依然无功而返。“我有个同学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在居家隔离期间告诉社区工作人员违反了国务院的‘九不准’,社区工作人员第二天就给她撤了电子封条,但我这边却无论如何都讲不通道理。”
 刘欣的同学发来的图片,早几日返回右玉县的同学被困在城外的高速口。
刘欣的同学发来的图片,早几日返回右玉县的同学被困在城外的高速口。在山西省太原市上学的刘欣迟迟未离校,则是因为担心回不去家。她告诉记者,她的家在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前几天已经有学生包车返乡了,但到了高速路口,出租车没有通行证便不能再驶入城内。学生询问县城防疫办,要么是电话打不通,要么就是表示不接收返乡学生。右玉县位于山西省最北部,几乎快要接近内蒙古,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学生们就在高速路口整晚整晚地等。后来县城防疫办才同意学生返乡,但要求进行隔离,方案一是去到人员稀少的村子进行隔离,方案二是自己找到空房子进行隔离。
面对这种情况,刘欣找了学校开了返乡证明,但仍然不敢贸然返乡,她既担心自己会沦落在零下十几度的天气里苦苦等待,也害怕隔离的村子里没有暖气,条件太差。
而对于家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的孙颖来说,回家似乎变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孙颖今年刚上大一,这一学期本应是她憧憬的大学生活的开始,然而她不过是从封控中的家乡乌鲁木齐到了封控中的广州,至今还没有踏出过校门。她无法想象,如果回不了家,在这个没有任何熟人的城市,自己该如何生活。
家似乎特别遥远。在封控三个月后,新疆目前虽然逐步解封,但“只出不进”。这一个月,孙颖送走了整个宿舍的同学,甚至整个学校目前也没剩下几个人了。
她的飞机票反复买了几次,又反复退掉。
(应被访者要求,本文所采访学生均为化名)
作者:陈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