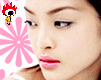| 平鑫涛自述:琼瑶在电影院里气得全身发抖(图)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03/28 17:05 文汇报 |
 平鑫涛 平鑫涛是作家琼瑶的丈夫,也是台湾的资深报人和老出版家。他创办于1954年的《皇冠》杂志在华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海外许多文坛巨星都是经由《皇冠》而崛起的。平鑫涛现仍为台湾皇冠文化集团社长。 我的几次“失去” 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闲荡到我家附近的一所美术专科学校。有一个儿童暑期美术班正在上素描课,我在窗外看得出神,回家就试着练习,第二天再准时去窗外旁听。时间一久,终于被老师发现,知道我没钱缴学费,就允许我进教室“旁听”,还免费供应炭笔、画纸。老师告诉我,他愿意特别向校方推荐,可以免试入学。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向父亲提出这样的要求。父亲说:“我们家那么穷,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你不是不知道,画家,哪一个不是潦倒贫困的?” 老师很同情我的处境,他说他小时候学画同样遭到父亲反对,逼得他离家出走,偷渡到日本,终于学成归国。老师到我家说服父亲,偏偏父亲是个极端固执的人。他们两人从争辩而争吵,最后是老师败北而去。伤心之余,我决定效法老师离家出走,偷渡日本。从不出门的我,走了三个街口,就茫然地坐在人行道的石阶上发呆。父亲找到了我。回家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不得不投降,答应“悔过求新”,答应参加普通初中的入学考试。 这是我第一次“失去”,至今还是记忆犹新。 大学时有一位女同学文静寡言,面目姣好,年轻的我,难免心动。我们每天几乎都有一二小时独处,但都是淡淡的“君子之交”。有一天她邀我去她家温课,发现她家竟然十分豪华。毕业餐聚那天,同学们戏笑着向我们祝福:“向新郎新娘举杯。”她都大方地接纳,似乎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 餐聚后的第三天,突来的机缘,我决定去台湾。满怀离愁,去她家话别。听完了我结结巴巴的述说,她出奇地平静,冷冷问我:留在上海一定不好吗?去台湾一定更好吗?我拙拙地说真希望有她同行。她还是那么平静,说:“你只有一个舱位,我哪能去?再说我凭什么身份跟你去呢?” 离开上海四十年后,我和琼瑶回到上海,在我下榻的饭店欢宴我的老同学们,居然来了二十多位,彼此相见,恍如隔世。琼瑶表示她很希望见到我的“初恋情人”,但她——没有来!并且没有一位同学知道她的下落。 这是我生命中,另一次的“失去”! 离开上海,最使我舍不得的,当然是这个家。母亲把二两黄金密密地缝在我一件外衣的垫肩里,又细心地为我整理行装,含笑地说:“等日子平静了,就可以回来啊。等事业有成了,可以接我们去啊。”当时,我也觉得也许两三年,最多三五年,就可以回来。但没有想到这是永别。这又是一次刻骨铭心的“失去”。 结缘张爱玲 从一九六六年四月,《怨女》在《皇冠》连载而后出版单行本,我们与张爱玲,展开了长达三十年的合作情谊,及至一九九四年六月《对照记》问世,共出版了十六部著作。 六十年前中日战争后期,我在上海读高中,正进入所谓的“吞咽期”,疯狂地吞咽着大量的文学书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从《万象》和《西风》等杂志上读到了许多张爱玲的作品。时光荏苒,辗转流离,我到台湾办起了《皇冠》。一九六五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那时,张爱玲已旅居美国。 《怨女》很快出版,彼此合作愉快,从此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年轻时期的张爱玲和我堂伯平襟亚先生的《万象》杂志结下深厚的文学之缘,而后又和“皇冠”合作,前后五十年,与两个平氏家族的出版事业紧密携手,这样横跨两代的渊源,也许正如她第一本书的书名一样,可说是另一则“传奇”吧。 虽然有这么长期的合作关系,但我与张爱玲却从未见过面,都是以电话和书信往来。平日去信都是透过她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转达,但每次都是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收到传真;即使收到了传真,她也不见得立刻回信,中间可能相隔二三十天。我想她一定很习惯这种平淡却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彼此才能维持三十年的友谊而不变。根据她小说改编的电影,我都会寄去录像带,但她都“不予置评”。 但有件事,她曾主动寻求我们的协助,我觉得她当时真的动了气。那是一位作家搜集了几篇她早期的旧作,未经她同意即径自出版,为此她写信给我,希望我能代她出面争回公道,必要时,她甚至愿意诉诸法律。幸而经过交涉之后,那家出版社愿意回收那两本书,免除了一场诉讼。虽然淡漠红尘,不问是非,但对自己的作品,张爱玲始终严肃以待。 《中国时报》曾于一九九五年颁赠文学上的“特别成就奖”给张爱玲,她欣然接受,并且特别去拍了一张照片,手持一份印有“金日成昨日逝”头条标题的报纸,幽默地表示这是她的近照。后来,她也决定将这张照片放在《对照记》再版时的最后一页,并补写了一段旁白: 写这本书,在老照相簿里钻研太久,出来透口气。跟大家一起看同一头条新闻,有“天涯共此时”的即刻感。手持报纸倒像绑匪寄给肉票家人的照片,证明他当天还活着。其实这倒也不是拟于不伦,有诗为证。诗曰:人老了大都/是时间的俘虏,/被圈禁禁足。/它待我还好——/当然随时可以撕票。/一笑。
(编辑:燕于)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
| ||||||||||||||||||||||||||||||||||||||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会员注册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5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
北京市通信公司提供网络带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