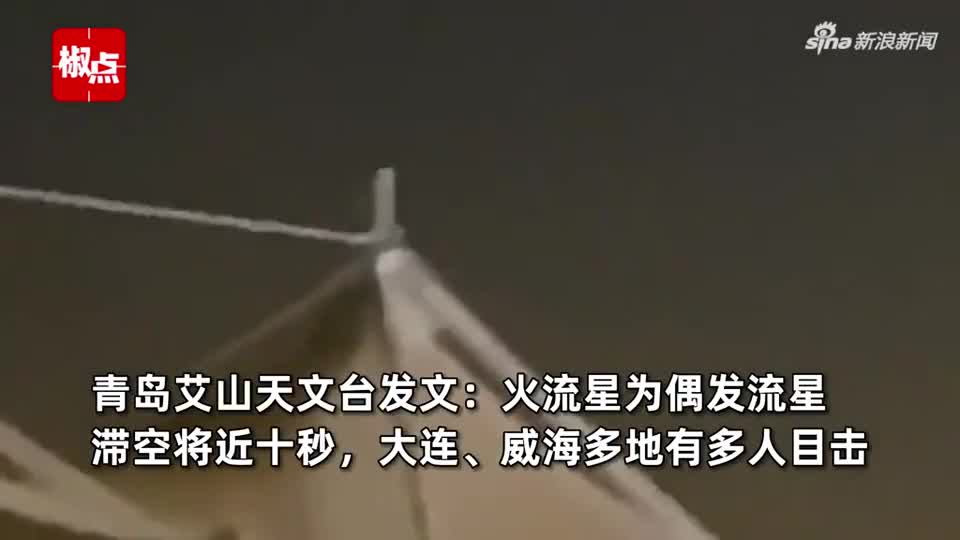[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 编辑/马雪、冯雪]
社交媒体上,我们经常能看到高学历年轻人投身体力活的故事,他们或是渴望逃离职场内卷,或是在就业压力下“脱掉长衫”、“文转腿”(“腿”指体力活)。但体力活会更容易干吗?
2020年,已经失业几个月的胡安焉开始在网上发表随笔,其中有一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记录下他在德邦广东某枢纽当夜班理货员的甘苦。文章很快火了,在豆瓣收获上万点赞,被多家公众号转载。
事实上,近20年间,胡安焉做过19份工作。除了物流公司,他还在广州漫画社当过学徒、在上海做过自行车店店员、在南宁开过女装店、在云南卖过卤味。最近的一份工作是在北京送快递。
打工之外,胡安焉的另一个身份是写作者,他读穆齐尔、卡佛、塞林格,写小说、写随笔,也喜欢记录下碎片式的感悟和想法。
今年3月,胡安焉首部非虚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收录了他过往的工作经历。新书目前在豆瓣上被打到8.7分。读者评论中,“真诚”是出现频率颇高的两个字。前不久,观察者网和胡安焉聊了聊,希望更多地了解他的心路历程。
采访中,胡安焉依然真诚而坦率。他害怕面试,找工作多是“有什么机会就干什么”,在他眼中,“白领”工作和体力活没什么本质区别。他承认,除了个人追求,自己的任性建立在某些“先天的幸运”上——事业单位退休的父母没给他太多赡养压力,“管好自己就行”。
作为资深“打工人”,胡安焉认为,年轻人当然可以去尝试体力工作,但不要仅仅因为对现在的处境不满意,就去美化、浪漫化另一种不同的人生,“这些工作真的没有那么田园诗意,没有那么美好、那么自由。”
 在北京送快递时的胡安焉 受访者供图
在北京送快递时的胡安焉 受访者供图有时候,同事之间就像“零和博弈”
2018年3月,胡安焉辞去德邦夜班理货员的工作,来到北京。一番波折后,他入职S快递,成为小时工。
在外人眼中,S快递堪称“快递界的海底捞”,口碑好。但对快递员胡安焉来说,主管的各种要求、工作中的“潜规则”都让他难以应付。
例如,主管常要求员工在派件时向客户提出帮忙把垃圾带走,还要请客户帮忙打五星好评,好评数排名靠后的会被揪出来。这让性格内向的胡安焉每天都很焦虑。
他还发现,有些小区好送,有些小区不好送,谁送了好送的别人就得送不好送的。他在书中写道:“同事之间就像零和博弈——要不就你好,要不就我好,但不能大家都好。”于是,不好送的小区一般会让新人去送,当新人察觉到不公平、又没有改变的机会时,就会选择离开。
胡安焉刚入组时,同事把难送的那几栋楼分给了他,他既不想和搭档闹翻,又不愿和喜欢占自己便宜的人共事。渐渐地,他“在工作中陷入一种负面情绪里”。
 清晨,快递站正在卸货分拣 受访者供图
清晨,快递站正在卸货分拣 受访者供图这年7月,胡安焉染上了病毒性肺炎。小时工没有医保,一场病连着误工费让他损失了三千多块钱。这时的他有了离职的念头。两个月后,他放弃转正机会,办理了离职手续。
2018年9月,胡安焉跳槽到品骏快递,不再是小时工的他拥有了五险,但工作依然充满着各种糟心事。他被偷过价值千元的快递,也曾自掏腰包为顾客的失误买单。他有一个“报复备忘录”,上面曾记过两个名字,都是让他“气炸了”的客户,本打算离职后上门找他们“算账”,最终还是删掉了。
胡安焉在品骏工作了14个月,直到公司解散。
在品骏的最后那段日子,胡安焉感受到了久违的轻松,他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一旦达不到额定产出值就恼羞成怒、气急败坏”。
他会尝试将原本固定的派件路线反过来走,会在送完快件后坐在商场里,打量逛街的人流和店铺里的售货员,看着送餐员跑来跑去。打量他们的举止,揣摩他们的心情。
结束全部工作之前,胡安焉发了一条朋友圈,仅客户可见,告知了品骏快递将解散,自己将不再负责有关配送的消息。很多顾客在微信给他留言,称赞他的服务态度。
有一名顾客评论道:“你是我见过的快递员里最认真负责的。”
胡安焉觉得,这名顾客的评价是真心诚意的,因为她没必要违心地奉承已经没有业务往来的自己。这也让胡安焉相信,他“曾经做得比一些客户见过的所有快递员都好。”
干过19份工作,“新环境反而让我更放松”
算上求学期间的实习,品骏快递员已经是胡安焉的第19份工作。
这个出生于广州的75后,大专读的是广告专业,“但我读的是夜大,也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凭含金量不是很高。”胡安焉说。
他坦言,在学校时没有刻意想过将来会从事什么工作,当时正好看到广州冬日漫画社有本叫《漫画家》的杂志在招学徒,“我画了个短篇寄过去,就被录用了。”他觉得自己“水平比较低”,“可能当时刚好遇上非典,他们想招外地学徒也不太方便,那一年招的人大多来自广东省内。”
当学徒的日子枯燥乏味,每天要练10多个小时的基本功,打排线、画人像、临摹场景。半年后,胡安焉和几个朋友因为不认同漫画社对待他们的方式,选择了离职。
 胡安焉在漫画社里完成的第一次故事作业(部分) 受访者供图
胡安焉在漫画社里完成的第一次故事作业(部分) 受访者供图此后近20年间,胡安焉走南闯北,足迹遍布广东、广西、云南、上海、北京。
他说自己找工作时不会考虑太多,也没有明确的目标,一般先打开招聘版,看看自己的学历、工作能力可以满足哪些工作,“能满足我就勾出来,再研究这些招聘简章的措辞,看哪个工作的要求相对不高。工作地点、收入甚至工作内容都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我最看重的是不要‘丢脸’,不要等到去应聘时才发现自己根本达不到别人的要求。”
“我害怕面试,也不擅长面试,所以我找工作都是随波逐流的,有什么机会就干什么。”
在胡安焉眼中,工作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所谓的“白领”工作和体力活没什么本质区别,前者不过是平常待在办公室里,“我看待工作很少会区分他是‘白领’还是体力,或者说是复杂劳动还是简单劳动,我也不觉得自己更喜欢复杂的劳动。”
胡安焉是个低物欲的人,生活开销不大,事业单位退休的父母都有保险和退休金,他“管好自己就行”。这种生活看似坦然,但10多年前,30出头的他面对财务自由的老同学,也会自卑。
2012年,他从广州搬到云南下关,在当地的商场找了一份保安工作,后来又被调到烘焙店做学徒。“其实这些工作我在广州也能做,但在广州我有从小到大认识的人。当时我已经33岁,我的一些同学已经财务自由了。面对这种落差,我还是会怯惧。”
 胡安焉镜头下的龙尾关(下关) 受访者供图
胡安焉镜头下的龙尾关(下关) 受访者供图“尽管我知道一个人无论做什么工作,或者收入多少,跟他本人的尊严是无关的,但在33岁那个年纪,我克服不了这种自卑心理。相反,我被自卑克服了,我会觉得羞愧,尽管我不该羞愧。”
胡安焉认为,自卑感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受到外部环境或者身边人的影响,尤其是比较熟的人,“在一个已经混熟的环境里,我受到压力要比在一个生疏的环境里大得多。假如我换一个地方,去了云南,没有人认识我,不要说33岁,就是我66岁去做保安也不会有这种压力。所以,当我去到一个新环境、一个陌生地方,我不仅不排斥,反而会更放松,更自然。”
胡安焉至今很怀念第一次去北京的那段日子。
那是2004年,他辞去了动漫杂志美编的工作,和朋友到北京“流浪和创作”,但他没有真的去流浪。为了生计,胡安焉先是在文印店打工,后来又在早餐店做帮工,住处也从通州搬到更远的河北燕郊。尽管如此,他还是无力负担房租,只能向父母求助。说好的创作漫画也没能坚持下去。
 2004年,胡安焉在燕郊王各庄住所内弹吉他 受访者供图
2004年,胡安焉在燕郊王各庄住所内弹吉他 受访者供图不久后,领头的朋友去了上海,“晃了半年膀子”的胡安焉也回到广州。
尽管这些日子看起来是在虚度光阴,但胡安焉认为,这段经历给了他一个起点。“当时我交往的人都是之前在漫画社认识的,他们都不是社会化的人,可以说是游离在社会边缘,但在他们之中,我能得到一种鼓舞。他们就像给我埋下了一颗种子,让我意识到那些跟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也能够自得其乐,也能在精神上、在价值上获得认同。”
“哪怕我并没有在2004年之后就立刻沿着这条路去追求个性化、边缘化的生活,但他们塑造了我最初的价值观,给了我力量,起码缓解了我的焦虑。”
“这种影响可能在十几年后才真正显现出来,让我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更尊重自己的本性。如果没有这段经历,今天的我肯定是两个不同的人。”胡安焉说。
为什么开始写作?
2006年,胡安焉曾短暂地写过几个月。当时他的父亲中风,身边需要有人照顾。另一方面,工作上遇到的烦心事也让他暂时放弃了上班。
胡安焉想试试能否通过写作解决经济问题,“我跑到书报摊买了一批很low的故事书,比如山寨的《故事会》,还在起点中文网开了连载,写校园小说。”
几个月下来,他只成功发表了一篇文章,是在一本叫《今古传奇》的刊物上,拿到了8、900元稿费。
这次尝试让胡安焉意识到,自己无法仅仅依靠写作养活自己,于是再次外出工作。此后有两年时间,他和朋友在南宁开起了女装店。胡安焉认为,这段经历堪称他人生的“分水岭”。
 胡安焉在南宁的住处 受访者供图
胡安焉在南宁的住处 受访者供图“生意上的竞争是丑陋的,尽管这种丑陋是被迫的,大家不得不表里两套、虚与委蛇、尔虞我诈,否则就生存不下去。我也没办法光明磊落。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每天要承受各种流言蜚语、恶意攻击、诽谤中伤。”
竞争对手的诽谤让胡安焉愤怒,但和此前“说走就走”的工作不同,女装店他是投了钱的,不得不硬着头皮扛下去。直到2009年9月,胡安焉才摆脱这个让他严重不适的环境。
“当时我的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很好了,已经出现了幻听,还有一些妄想,当然现在已经好了。我在2007年去南宁之前,只是一个不喜欢社交、比较害羞、孤僻,不爱说话的人,2009年离开南宁时,情况是比较糟糕的,产生了一种逃避心理,对现实厌恶反感。”
胡安焉说,促成他写作的正是这种逃避心理,“我把写作的价值看得很崇高,把现实看得一文不值。一开始,我的心态就是那么幼稚的。尽管这时候我已经30岁了。”
在女装店的最后几个月,胡安焉经常利用空闲时间阅读小说,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雷蒙德·卡佛、塞林格。这让他更加坚信,应该做自己喜欢和擅长的事,比如写作。
经营女装店的经历并不愉快,却让胡安焉攒下了几万块钱,这也成为他“脱产”写作的资本。
 2008年,胡安焉在南宁经营的第二家女装店开张 受访者供图
2008年,胡安焉在南宁经营的第二家女装店开张 受访者供图在胡安焉看来,他的写作生涯真正开始于2009年10月。当时他写了一批取材自真实经历的小说,贴到一个文学论坛上和其他写作者交流。不久后,有些作品被发表在文学期刊上,但稿费很低。
这段写作的日子持续了两年多。胡安焉觉得,写作不能算一份工作,但他对待写作的认真和投入要超过自己做过的所有工作。
2011年,胡安焉再次被拉回到工作中。此后几年,他又换了很多工作,也去了很多城市,反复地处在打工和写作两种状态中,“当我去打工的时候,我就无法写作,光是工作本身就极大地占用了我的时间,同时它还透支我的情绪,令我在下班后也只想放松和减压,而无力思考其他。”
“很多人可能误解了我的经历”
2019年11月25日,是胡安焉在品骏上班的最后一天。之后,失业的他回了趟云南和广东。等到2020年春节再次回到北京时,新冠疫情已经暴发。赋闲在家的胡安焉干脆重拾写作。
他开了微信公众号,也重新开始更新豆瓣日记,发的大多是随笔。胡安焉没有把这些随笔看成“作品”,他的目标是长篇小说,随笔只是热身,但其中有一篇《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却出乎意料地火了。
这篇随笔记录了他2017年5月到2018年3月在德邦物流广东顺德陈村枢纽干夜班理货员的经历,到目前为止,在豆瓣获得3700多次转发,10000多个点赞。
文章得到热烈反响,胡安焉震惊之余,也想过大家为什么会喜欢这篇文章,“大多数从事这类工作的人缺乏文字表达能力或不善于表达。我在德邦的时候,一些同事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可能其他字都写不好,还有人甚至小学都没毕业。我描写的那种工作方式和环境,对很多人来说是陌生的,他们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信息。”
 德邦陈村枢纽附近石洲村的招工墙 受访者供图
德邦陈村枢纽附近石洲村的招工墙 受访者供图在胡安焉看来,很多人可能误解了他的经历,认为他是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人,为了生计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并出于爱好去写作。“不少读者给我的反馈是报以同情,觉得像我这样干体力活的人,肯定是没有接受过太多教育,没有受过写作训练,所以能写出这种文章就是天分。实际上我都写了10多年了,我从事体力工作也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
“我没有主观地去误导别人,我之前写的日记都没有隐藏,只要网友想看都能看到,但大多数人不会特地去看,可能只读到这一篇文章,对我产生了一种错位的同情,从而对我报以更大的关注或热情。”
这让胡安焉有些惶恐。
过去,他在豆瓣发文时都会顺手把赞赏功能打开,但在《德邦》之前,他从来没有被打赏过,也没想过真能收到打赏。《德邦》发布后短短几天,他收到了1000多元打赏。
从这以后,胡安焉再也不敢开赞赏功能了,“我怀疑有些给我打赏的人,可能收入都不如我高,我接受打赏就像骗人一样。我在品骏快递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有7000左右,公司还给我买五险。”
《德邦》一文让胡安焉受到了更多专业人士的关注。2020年4月,文学机构“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联系上胡安焉,跟他约稿,鼓励他尝试非虚构写作。
胡安焉坦言,当时他对非虚构这种形式知道的不多,也一直没弄清楚非虚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和‘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沟通,想了解非虚构大概要怎么写,有没有模板,有没有好的案例。他们并没有这样的东西。但他们告诉我,我的写作能力、经历、性格,这些因素单拎出一两样,可能会和其他人重合,但结合在一起,可能就不会再有另外一个人。”
在和编辑沟通之余,胡安焉也专门去找了一些书来读。不久后,他写下了反映自己在北京送快递经历的《派件》,这个版本有3万字,主要在文学爱好者中传播。2021年6月,《派件》以《我在北京派快件》为题,发表在了《读库2103》上,更多读者看到了胡安焉的经历。
等到2023年新书出版时,胡安焉已经把这篇文章扩写到4.7万字,文章也有了新标题——《我在北京送快递》。除了这篇,胡安焉扩写了早前发在豆瓣上的《我在德邦上夜班的一年》和《在上海打工的回忆》这两篇,并重新写了一篇关于自己早年工作经历的自述。这些内容一并收入在新书中,《我在北京送快递》也成了新书的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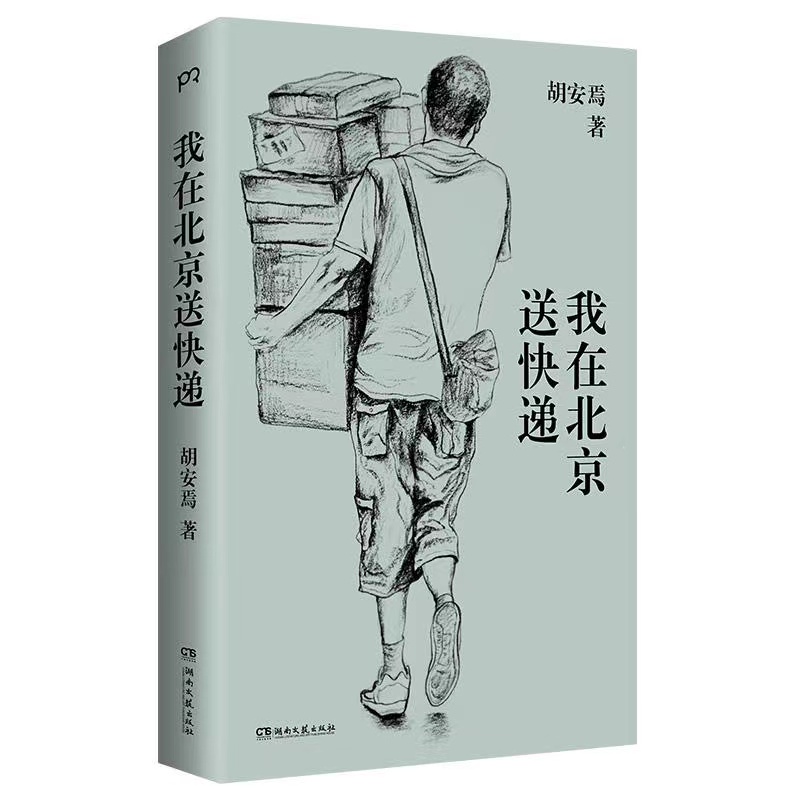
“这些工作没有那么田园诗意”
离开品骏快递后,胡安焉没有再去工作,这三年来他靠着之前攒下的十万多元存款和稿费生活。
他最近刚和女友登记结婚,妻子是早些年在文学论坛上认识的,也喜欢写小说。“我们生活习惯都很节俭,没什么家庭负担,经济方面的压力不大,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空间。”
“在一般人看来,我肯定是任性的,这种任性可能是建立在我先天的幸运上,那就是父母没有给我什么赡养压力。”
“但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其实也放弃了一些东西。”胡安焉说,“首先,我和我妻子价值观比较一致,我们都认同没有回报的写作的价值。其次,我们不打算要孩子,我们的收入根本养不起孩子。第三,我们登记结婚没有通知任何朋友,一分钱没花,也没有摆宴席,没有金钱投入。我们把这些钱都省下来了,大多数人可能省不了,只能硬着头皮去扛。”
接下来,胡安焉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计划。他坦言,相比非虚构,自己还是倾向于写小说。“非虚构对我来说,只能写自己的经历,但我的经历是有限的。我不能像何伟(Peter Hessler,美国非虚构作家、记者)那样,可以为了写一个主题,专门去体验或者做采访,我不具备这种条件,主要是我没钱,也没那个能力。”
“到目前为止,我写的全部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已经结束了的经历,这些经历包括现在出的这本书的内容以及另外写的大约20万字,已经差不多把我想写的都写完了。接下来我还是只能回到小说,因为小说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天地也是无限的,只是读者很少。”
 胡安焉近照 受访者供图
胡安焉近照 受访者供图胡安焉说,他不会把写作当成职业,目前的存款和新书版税收入尚能维持他和妻子的生活,要是将来经济条件不允许了,他还会再找工作。
近20年的时间里干了19份工作,胡安焉在打工人和写作者的身份中来回切换,网友也在他的经历中读到了另一种人生。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历尚可的年轻人渴望逃离职场内卷,去体验不同人生,或是出于就业压力“脱掉长衫”。在豆瓣,去年11月才成立的“轻体力活探索联盟”在半年内就拥有了4万多名组员;在微博,“保安已经当得不想离职了”“985毕业生选择去做体力活”等话题频频冲上热搜。
但在胡安焉看来,体力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做德邦理货员期间,灰尘混合着汗液,在胡安焉手臂上留下的污渍 受访者供图
做德邦理货员期间,灰尘混合着汗液,在胡安焉手臂上留下的污渍 受访者供图“我之前做的那些工作,我怀疑普通大学生根本干不了,当然能干的也有。事实上我看到很多从农村出来,过得很苦的人到了德邦也适应不了,试完工后,真的能留下来的不到一半。这些工作真的没有那么田园诗意,没有那么美好、那么自由。送快递可能没有半夜分拣那么累,但也是日晒雨淋。”
胡安焉认为,如果年轻人真的喜欢从事简单的劳动工作,当然也可以去尝试,“干了之后发现自己喜欢这份工作,那就最好,如果发现和自己想象中不一样,就说明他之前没有看清楚自己。真到了这一步也没什么大不了,人生是需要不断地犯错,在错误中成长,咬咬牙扛过去就行了,但是不要去抱怨。”
“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看清楚自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不要仅仅因为讨厌眼下自己所拥有的工作,对现在的处境不满意,就去想象、去美化、浪漫化另一种不同的人生。”胡安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