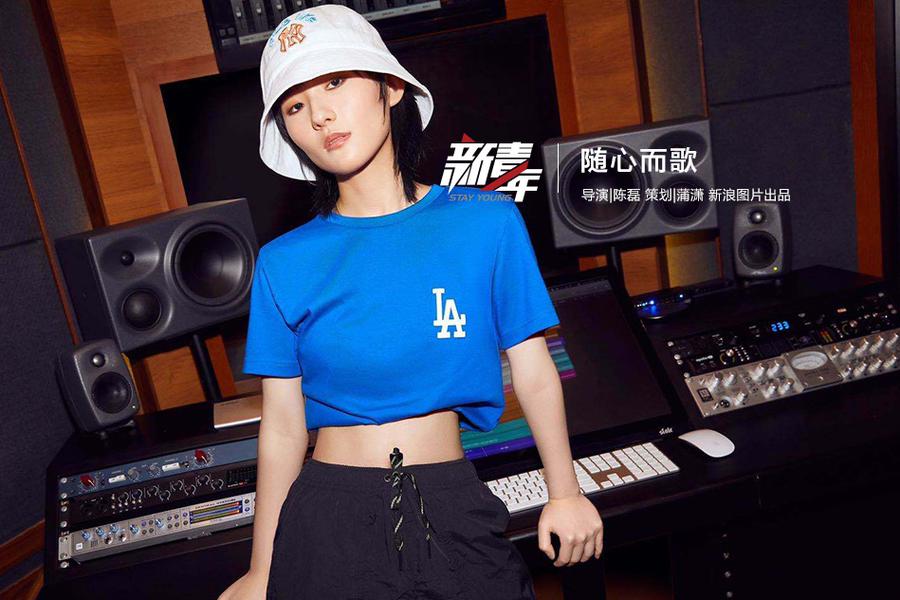原标题:告别金斯伯格,关乎的不是女性独有的权利
上周五,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的消息骤然而至。这位自由派女性终其一生与性别歧视作斗争。她不仅为女性辩护,也曾为遭受性别歧视的男性辩护。在她的推动下,多条因性别而差别对待的法律得到改写。她更让我们看到,男权与女权并非对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的,人人都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同时,金斯伯格始终站在同性恋者、移民等少数群体的一边,成为美国自由派的一面“旗帜”。
金斯伯格的去世令人悲痛,更值得我们警惕。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媒体时表达了对她的赞扬,但接下来,特朗普极有可能提名一位保守派女性接替金斯伯格留下的位置,使得原本就是保守派占据多数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进一步“右倾”。
今天分享鲁思·巴德·金斯伯格的传记《异见时刻》,回顾这位杰出女性的早年生涯。金斯伯格的去世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

《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大法官》
[美]伊琳·卡蒙、[美]莎娜·卡尼兹尼克 著
博集天卷丨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18-9
错误理解女性刻板印象
“我认为我在那十年间致力诉讼的案子,关乎的不是女性独有的权利,而是男女平等公民权的宪法原则。”
——金斯伯格,于 2010 年
1973 年 1 月 17 日,金斯伯格因为怕自己紧张到呕吐而没吃午饭。下午,她佩戴着母亲留给她的胸针和耳环,像是即将上战场的士兵穿戴好铠甲,站到了九位面无表情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前,要求他们承认美国宪法禁止性别歧视。直到那一天,最高法院依然拒绝承认这一点。
最高法院的所有法庭辩论都以同一句话开头:“首席大法官先生,以及各位尊敬的大法官们。”当天的录音中,金斯伯格说这句话时的声音有一点颤抖。这是她第一次在最高法院中辩论。
金斯伯格牢牢地记住了这句开场白,但还是紧张得反胃。努力镇定下来后,金斯伯格告诉大法官们,政府拒绝为空军中尉莎朗·弗朗蒂罗的丈夫约瑟夫提供军官配偶应得的住房和医疗福利,只因为莎朗中尉是女性。
 ▲鲁思·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1933 年 3 月 15 日 - 2020 年 9 月 18 日),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鲁思·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1933 年 3 月 15 日 - 2020 年 9 月 18 日),曾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十四个月前,最高法院在“里德诉里德案”中判定爱达荷州不能仅基于性别而判定母亲无权处理其亡子遗产,因为男性并非一定比女性更有能力处理遗产。但在“里德案”中,最高法院没有明确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是否大多数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都是违宪的。金斯伯格深吸了一口气,要求大法官们在“弗朗蒂罗案”中明确回答这个问题。
金斯伯格指出,“里德案”中的州法律和“弗朗蒂罗诉理查森案”中的联邦法律都建立在“同样的性别刻板印象上,即在婚姻关系中,男性是独立的个体,而女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男性的附庸,而且她们无须承担养家责任”。
通常,金斯伯格在公共场合演讲时都会找寻观众席中马丁的身影,但这一次在最高法院出庭时,马丁只能坐在她身后。他坐的那块区域是专门预留给允许在最高法院出庭的律师们的。
知道马丁坐在哪儿,金斯伯格就觉得心里有了底。她有十分钟可以在美国最位高权重的九位法官面前为此案辩护。对于本案事实及相关法律,金斯伯格比这些大法官懂得多,她现在的任务是把这些内容教给他们。金斯伯格知道该怎么做,毕竟她已经做了近十年的法学教授。
在那天她拿到的最高法院律师执业资格卡上,金斯伯格被称为“鲁思·巴德·金斯伯格太太”。自从“女士”这种称呼出现开始,金斯伯格就要求大家称她为金斯伯格女士。这一天,不少金斯伯格哥大法学院的学生都来看她出庭,他们在听到金斯伯格被称为“太太”之后,挤眉弄眼地让她要求法院把“太太”改为“女士”。金斯伯格拒绝了,她今天的目的是赢得这个案子,而非在这些无须即刻解决的细枝末节上浪费精力。
金斯伯格的论点十分激进。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上坐着的九位男性自认为是好丈夫和好父亲,但他们相信男人和女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女性可以被保护而不用体会真实世界中的生存压力和尔虞我诈是很幸运的。但金斯伯格这个不到四十岁的小女人却想要让这些大法官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女人理应拥有和男人相同的地位。
金斯伯格告诉大法官们,法律对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区别对待不仅暗示了“女不如男的价值判断”,而且明目张胆地告诉女性,即便她们做着和男性同样的工作,她们的工作成果和家庭也不如男同事的重要。“这些区别对待都会导致一个后果,”金斯伯格坚定地说,“它们让女性在社会中低人一等,并迫使她们安于这种现状。”
一年前和金斯伯格一起创建了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的布兰达·费根坐在金斯伯格身后,她面前的桌子上摊放着各种案例,随时准备着给金斯伯格提供她所需要的判例引用。但金斯伯格根本不需要,她对于相关判例的精确引用信手拈来,和自家电话号码一般熟悉。
那一天,金斯伯格的对手是联邦政府,它在辩护状中为自己的政策申辩,这个政策默认女性从属于男性,因此只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允许男性申请家属补助费。毕竟,大多数挣钱养家的都是男性。联邦政府辩护状封面上的署名是欧文·格里斯沃尔德,金斯伯格就读哈佛法学院时的院长。金斯伯格犹记得当年她违心地告诉格里斯沃尔德自己上法学院只是为了做个可以与丈夫闲谈的好妻子,现在的她已与当时有了天壤之别。
大法官们依然一言不发。金斯伯格继续说道:“性别和种族一样,是一种显而易见却难以改变的个人特质,它与个人能力并无必然联系。”把性别和种族类比在美国宪法的语境下有特殊的意义:在“布朗诉教育局案”之后的一系列案子中,最高法院确定了一个原则,即根据不同种族区别对待的法律在原则上全都违反宪法,至少需要通过“严格审查”以确定政府有重大且确切的理由来进行区别对待。在“里德案”中,最高法院的结论是,严格审查标准不适用于基于性别区别对待的法律,但似乎在达到最终判决的实际论理过程中却使用了该标准。本案的问题是,在原则上,是否依据性别而区分对待的法律和依据种族而区分对待的法律都是违宪的?金斯伯格大胆地要求法庭对此做出肯定的答复。
金斯伯格十分钟庭审发言即将结束之时,她直视大法官们,引用了废奴主义者兼女性选举权提倡者莎拉·格里姆凯曾说过的话。“她的语言并不优美,但非常清晰,”金斯伯格说道,“她说,‘我从不以我的性别为由要求特别优待。我对于男性同胞唯一的要求是给我们以基本的尊重’。”通常,在最高法院开庭的律师们会不断被大法官们打断,有时甚至连一句完整的话都没机会说完。但是,今天在庭上饿着肚子的金斯伯格隐约带着布鲁克林口音的演讲却一次都没有被打断。她的发言让大法官们都震惊到说不出话来。
金斯伯格表面镇定,内心却在打鼓。这些大法官真的有认真听她的演讲吗?她要五个月后才能知道判决结果。庭审之后,人潮向外涌去,身材健壮的格里斯沃尔德院长走到了金斯伯格的身边。他刚刚观看了自己手下的律师与金斯伯格及其共同律师的唇枪舌剑。格里斯沃尔德严肃地握了握金斯伯格的手。那一晚,哈利·布莱克门大法官照常在他的日记里给当天出庭的律师打分,他只给了金斯伯格一个 C+。“这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女性。”布莱克门写道。
土地,和女人一样,是注定要被占有的
十年前的 1963 年,金斯伯格对于推进女权运动还没有那么积极。虽然在瑞典时,她曾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感到深深震撼,但除了民事诉讼法,她把在瑞典学到的其他东西都束之高阁了。那时,金斯伯格刚开始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教课。某一天,她的同事告诉她罗格斯法学院正在招聘女性教授,因为该学院唯一的一位黑人教授离职了。当时的哥大法学院没有一位女性或黑人全职教授,但似乎没有人在乎这件事。全美所有法学院中只有十四位可能得到终身教职的女性教员,而罗格斯法学院就占了其中一席。在金斯伯格接受了罗格斯法学院的教职后,《纽瓦克星定报》很快发表了一篇有关她和另一位女教授伊娃·汉克斯的报道。这篇报道在标题中把金斯伯格和汉克斯称为“穿着教袍的淑女”,而且一开篇就描述她们“身材苗条、很有魅力”,而且夸张地表示,“她们长得十分年轻,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学生”。
罗格斯法学院只愿意跟金斯伯格签订为期一年的教授民事诉讼法的雇佣合同,而且工资很低。毕竟,法学院院长威拉德·赫克尔提醒金斯伯格,罗格斯法学院是公立学校,而且她是女人。“他们告诉我,‘我们不能付你和甲教授一样多的工资,因为他有五个孩子要养,而你丈夫的工资收入不错’,”金斯伯格回忆道,谨慎地隐去了甲教授的真实姓名,“我追问道,那么单身的乙教授的工资是不是也比我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金斯伯格不再追问,转而埋头苦干。她每天从纽瓦克坐火车到纽约曼哈顿上班,还发表了许多标题类似于“国际民事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及执行”的文章。她成功熬过了第一年。
然而,很快,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扰乱了金斯伯格家平静的生活。多年前,在金斯伯格和马丁还在念法学院时,马丁接受过治疗睾丸癌的手术。术后,医生告诉他们,马丁接受放射治疗前是他们尝试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最后机会。当时,金斯伯格在法学院繁重的功课、照顾年幼的女儿和未知马丁能否存活的焦虑中挣扎,根本无法想象再生一个孩子。到了 1965 年,就在金斯伯格夫妇快要成功地说服将满十岁的简家里只有她一个孩子也不是一件坏事的时候,金斯伯格发现自己怀孕了。“告诉我,亲爱的,”女医生拉着金斯伯格的手问道,“你是不是还有别的男人?”金斯伯格没有出轨。马丁接受了检查,确认了他在接受放射治疗后依然有生产精子的能力。
金斯伯格怀孕的喜悦中交织着焦虑,她不知能否保住自己在罗格斯法学院的教职。罗格斯法学院将在春季学期的末尾决定是否与她签订下一年的雇佣合同,而金斯伯格不打算重蹈覆辙,一如自己在俄克拉何马州社会保障局因为怀孕而失业。她的预产期在九月,为了遮掩孕肚,她向婆婆伊芙琳·金斯伯格借了许多大一号的衣服,希望不要在暑假来临前让学校发现自己已怀孕的事实。这个方法奏效了。金斯伯格上完了春季学期的最后一堂课,成功拿下了第二年的雇佣合同。她这才告诉同事们自己已经怀孕了。9 月 8 号,金斯伯格夫妇的第二个孩子詹姆士出生了。不久之后,金斯伯格回到了岗位,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金斯伯格所处的环境却开始发生变化。她的一名学生宣称自己是言论自由运动的成员。“每天上课前他都要找个高处坐下,时不时地对我做出蔑视的手势。”金斯伯格回忆道。她刚开始在罗格斯教书时,每门课里大概只有五到六名女性。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被派往越南参战,女性的数量开始慢慢增多。课堂之外,讲述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对于自己困在家庭中的角色不满的《女性的奥秘》一书出版了,该书在第一次印刷时就卖出了超过一百万册。与此同时,1964 年通过的《民权法案》在禁止职场种族歧视的同时,像是临时想起来一般地也顺便禁止了职场性别歧视,而通过该法案的国会议员们则开了很多“妻管严”的玩笑。(议员伊曼纽尔·赛乐开玩笑说,他在家中通常拥有最终发言权:“好的,亲爱的。”)
该法案通过后,金斯伯格担任志愿律师的美国民权同盟新泽西分部收到了大量女性来信。金斯伯格身为女性被派去处理这些信件。她尽责地阅读了所有来信。来信中说,立顿红茶公司不允许女员工将家人添加到健康保险上,因为公司认定只有已婚男性才会有受抚养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工程师夏令营不允许女生参加;新泽西州蒂内克市最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因为是女生而不被允许加入大学运动代表队。还有一些来信让金斯伯格回忆起自己难堪的往事。女教师们在来信中说,她们一旦显出孕肚就会被强制要求离职,有时甚至在显怀之前。学校称之为“休产假”,但这种产假既不自愿又无薪酬,而且在生完孩子之后,她们是否还能再回到课堂也要看学校的心情。一位女兵在怀孕之后被授予了荣誉退役,但是等她想要再度入伍的时候却被告知,怀孕是会导致公民“丧失入伍资格的道德及行政原因”。这些问题并不新鲜。但人们开始对这些事有所抱怨却很新鲜。至少金斯伯格之前从未想过要抱怨这些。
这时在法学院就读的女生们大都比金斯伯格小十岁左右。她们已不满足于口头抗争,而是提出了明确的诉求。她们中的一些来自密西西比州,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2] 中推进民权运动。这些年轻的女性曾亲眼见证律师们奋力推进平权,来到法学院后却发现这里的文化依然要求女生们循规蹈矩。与此同时,各个大学也在社会压力下不得不开始逐步提高女生比例,特别是在 1968 年约翰逊总统领导的联邦政府把性别歧视列为会减少联邦拨款的“罪行”之一以后。
金斯伯格钦佩地观察着这些女生,她们与她自己那一代的女性太不一样了。在金斯伯格的那个时代,女生们根本不敢提出要求,生怕自己太过引人注目。1970 年,在学生们的请求下,金斯伯格开了罗格斯法学院历史上第一门有关女性的法律课。金斯伯格只花了大约一个月就读完了所有讨论女性法律地位的联邦判例和法律期刊论文,因为相关的讨论并不多。甚至,一本著名的教科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土地,和女人一样,是注定要被占有的。”(这是一本讨论土地所有权的书,女人只是被作为比喻以便读者理解。)读完这些材料,金斯伯格暗下决心:她将不再默默忍受自己因为女性身份而遭受的不公了,包括她工资的“女士折扣”。金斯伯格和其他女教授一起提起了联邦集体诉讼,控告大学在薪酬方面歧视女性。她们赢了。
不再默默无闻
1971 年 8 月 20 日,新泽西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一位名叫兰妮·卡普兰的女邮递员写信给美国民权同盟新泽西分部,投诉邮局不允许她佩戴男性邮递员佩戴的邮帽。“女邮递员的帽子是没有帽檐的贝雷帽或者小圆帽,我的徽章没法别在上面,”兰妮在信中解释道,“而且,男邮帽的帽檐可以遮挡阳光直射眼睛,女邮帽却不行。”
当时,金斯伯格正在准备去哈佛法学院做一学期的访学教授,她也已经成功将一些案件诉到了最高法院。但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性别歧视的案件是无关紧要的。“男性邮帽的某些功能特征可以促进工作表现,通过邮帽样式来区分男女邮递员是以牺牲这些功能作为代价的,这样的规定无疑是武断的。”金斯伯格在给邮政局局长的信中写道。这位局长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金斯伯格清楚地知道,写言辞激烈的信件来对抗性别歧视只是杯水车薪。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总会有更多性别歧视的法律规定出现。女权主义活动者应有大局观。不管是在邮帽样式的小问题上还是联邦政策的规定中,美国需要的是更广泛的对性别平等的认同。几十年来,一部分女权主义者认为,达成性别平等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宪法中加入一条平权修正案:“美国联邦及州政府不应基于性别区别对待而损害法律中的平等权利原则。”
1923 年开始的每一次国会会议中,这条缩写为 ERA 的修正案都会被提出,但从未获得通过。金斯伯格觉得这也许是因为现行宪法中已经提供了达到性别平等的解决方案。毕竟,宪法序言的第一句话就以“我们人民”开头,女性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虽然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受到了各种限制,但女性难道不配与其他人民一样得到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下承诺的平等保护吗?问题是,金斯伯格要如何让最高法院上的至少五名大法官认同她对于宪法的理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唯独最高法院还故步自封。也许,如果可以把一个合适的案子诉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一天晚上,金斯伯格照常在卧室里工作,思考着诉讼策略。“有个案子你一定要读一下。”照常在餐厅里工作的马丁突然大声说道。“我不读税法的案子。”金斯伯格回应道。但她后来很庆幸自己读了这个案子。
 ▲鲁思·拜德·金斯伯格与丈夫马丁·戴维·金斯伯格,马丁同样是一名律师。
▲鲁思·拜德·金斯伯格与丈夫马丁·戴维·金斯伯格,马丁同样是一名律师。查尔斯·莫里茨是位经常需要出差的推销员,他跟自己八十九岁的老母亲一起住在丹佛市。每次出差,莫里茨都需要雇人照顾自己的老母亲,但当他想要申报这些费用来申请税务减免时却遇到了麻烦。美国国税局只允许女性、鳏夫或者妻子丧失行为能力的男人申报照顾家人的费用来减免一部分税务,但莫里茨却是个从未结过婚的男人。显然,政府从未考虑过男人也有可能需要独立承担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读完这个案子,金斯伯格咧开嘴笑了,她对马丁说:“我们来接这个案子。”这是她和马丁第一次职业上的合作。
表面上,“莫里茨案”很不起眼,莫里茨雇人照顾母亲的费用不过区区六百美元。而且此案与对女性的不公似乎也无太大关联。但马丁和金斯伯格有着更长远的打算。在他们看来,政府毫无正当理由,而是仅依据性别就拒绝给予某个性别的公民政府福利。如果法院判定该政策有误,此案将作为判例广泛促进对于性别平等的认知。
金斯伯格写信给了她年少时在夏令营认识的老朋友梅尔·沃尔夫寻求支持。沃尔夫现任美国民权同盟的全国法务总监,他决定支持金斯伯格夫妇对该案的诉讼。沃尔夫后来告诉作家弗雷德·斯泽贝夫,自己知道金斯伯格在新泽西做一些“底层的女性权益工作”,他还向斯泽贝夫吹嘘他要让金斯伯格“从默默无闻中脱离出来”。他会帮她诉到最高法院。
金斯伯格夫妇在辩护状中提出,“当男女的生理差别与问题中的事务并无关联时”,政府不可区别对待男性和女性。金斯伯格把撰写好的辩护状发给了沃尔夫。她知道美国民权同盟已接下“里德诉里德案”在最高法院的辩护。在“里德诉里德案”中,爱达荷州的法律规定男性相较于女性拥有处理遗产的优先权。在此案中,莎莉·里德的丈夫塞西尔·里德常对莎莉拳脚相加,后来又抛妻弃子,但当他们的儿子自杀后,按照爱达荷州的法律规定,因为塞西尔是男性,因此他拥有处理亡子留下的不多遗产的权利。金斯伯格认为,如果把“莫里茨案”和“里德案”合并成一个案子诉到最高法院,就有可能让大法官们意识到性别歧视对所有人都是一种伤害。
“这些材料里应该有对‘里德诉里德案’有利的东西。”金斯伯格在 1971 年 4 月 6 日给沃尔夫的信中写道,信里附有她撰写的“莫里茨案”的辩护状,“你有没有考虑过也许加一个女性共同辩护律师会对此案有利?”金斯伯格几乎从未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要求别人给予她特殊考虑,但她觉得如果这么做可以让她去最高法院辩护,那也是值得的。很多年之后,沃尔夫告诉斯泽贝尔,“好吧,也许我并没有让金斯伯格从默默无闻中脱离出来。也许是她自己让她不再默默无闻了”。他没说错。沃尔夫告诉金斯伯格他确实需要她的帮助把莎莉·里德的案子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从未见过一个它不喜欢的性别区分案
把“里德案”诉到最高法院存在巨大的风险。如果最高法院还没有做好推翻把女性作为二等公民判例的准备,“里德案”可能会使最高法院在这条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仅十年之前的 1961 年,一位名叫格温多琳·霍伊特的女性被完全由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判定谋杀丈夫的罪名成立,她对该陪审团的组成提出了质疑。在佛罗里达州,男性公民必须履行陪审员义务,而女性则需要主动选择成为陪审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认为,女性是否参与社会公民活动无关紧要,毕竟,女性还“依然被认为是家庭生活的中心”。“霍伊特案”表明了最高法院对待性别议题的态度从 1948 年开始就没有进步过。1948 年,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大法官——那个拒绝雇佣金斯伯格为法官助理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在一份意见书中遗憾地表示,允许女性做酒吧调酒师可能会“导致道德缺失并引发各种社会问题”。
金斯伯格念法学院时曾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个暑假,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名叫泡利·默里的黑人女性律师。当时的民权运动中,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一般被认为是两码事。但默里充满激情地在民权运动的各部分之间建立纽带,她认为男性在民权运动中占据了太多主导地位,而女权运动者又常对种族议题不甚了解。尽管金斯伯格是那个让最高法院向着一个新方向前进的人,默里却是这条路上的第一位开拓者。
早在 1961 年,默里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即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本身就足以为女性解放提供法律依据。默里及其美国民权同盟的同事多萝西·凯尼斯试图找到一个推翻“霍伊特案”判例的方法。1965 年,默里与他人合著了一篇对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进行比较的论文——《被歧视压迫的女性与法律》,当时正在罗格斯法学院授课的金斯伯格把这篇文章纳入了课程大纲。该论文提出,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各自独立,但又相互关联。在这篇文章发表的一年后,默里和凯尼斯想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于是,她们对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判决提出了质疑,在该案中,完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陪审团认定杀害了两位选举权运动积极分子的疑犯们无罪。她们赢得了该案的胜利,但由于败诉的亚拉巴马州决定不上诉,这个案子没能诉到最高法院。
在金斯伯格即将声名远扬的“里德案”辩护状中充满了默里提出的理论的痕迹,而且该辩护状还少见地引用了西蒙娜·德·波伏娃、诗人阿尔弗雷德·罗德·坦尼森,以及社会学家冈纳·米达尔的话。金斯伯格女权主义法律课中的学生们也参与了该辩护状的撰写。该辩护状指出,世界对女性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但相关法律却停滞不前。在向最高法院提交辩护状前,金斯伯格在扉页的作者一栏中加上了“多萝西·凯尼斯”和“泡利·默里”。金斯伯格后来说,她想要大家能够清楚地知道,她是“站在了她们的肩膀上”。
“你不该这样做。”金斯伯格当时在美国民权同盟的同事伯特·纽伯恩记得自己曾经这样告诉她。纽伯恩认为多加这两个名字是“违反规定”的。
“我不在乎,”金斯伯格回答道,“她们本就应该得到重视。”后来,金斯伯格表示,自己不过是继续了凯尼斯和默里未竟的事业。而她的幸运之处在于,这个世界终于做好了倾听的准备。
女权项目的诞生
早期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寄出信件上的邮票图案十分出人意料,这些邮票上居然印着花花公子兔女郎。至少有一位收到这样信件的人对此表示过愤慨。但这完全是因为《花花公子》杂志是美国民权同盟的大赞助商,这些邮票是它对女权项目的物品捐赠。美国民权同盟中的这个女权分部刚起步时一穷二白,它的第一位全职员工是后来成了女权运动家的哈佛法学院毕业生布兰达·费根。金斯伯格的学生们也会时不时地来帮她干一些跑腿的活儿。
尽管经费和人员都有限,金斯伯格对该项目仍抱有远大的理想。在赢了“里德案”后,金斯伯格向美国民权同盟提出了自己对于女权项目的发展计划。除了《花花公子》杂志创始人休·赫夫纳,欧文·格里斯沃尔德也是一位出人意料的女权项目非官方赞助者。金斯伯格夫妇在第十巡回法院赢了“莫里茨案”后,就任联邦副检察长的格里斯沃尔德向最高法院抗议,认为最高法院必须推翻第十巡回法院的判决,否则上百条联邦法律都会被判定为违宪。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格里斯沃尔德在辩护状中附上了附件五,其中包括了所生有区别对待男女的法律规定。金斯伯格马上意识到了这份附件是什么:她要推翻的法律清单。
当时美国出台了各种法律禁止工资、雇佣及教育歧视,但是金斯伯格明白纸上的承诺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文化和法律中都存在性别歧视的大背景下,女性想要得到平等的权利道阻且长。”金斯伯格在 1972 年 10 月的一份计划书中写道。美国民权同盟的女权项目有三大任务:教育公众、改变法律以及在美国民权同盟各地分部的帮助下进行女权案件的诉讼。
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意味着对各个方面都提出质疑。尽管在社会的压力下,最高法院判定堕胎合法,但是“实施堕胎手术和堕胎过程中可享受的医疗福利都依然受到过度限制,这些问题都应受到进一步质疑”。女权项目的其他优先任务,金斯伯格写道,还包括“自由选择绝育的权利”——医生常劝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不要绝育——“和不被强迫绝育的权利”——有色人种女性和被认为“心智不健全”的女性常常会被迫绝育。该项目,金斯伯格写道,会对教育和培训项目中存在的歧视,房屋抵押、信用卡、贷款和房屋租赁中对女性的限制,在监狱或军队中对女性的歧视,以及“因为性生活活跃而将少女囚禁在少管所中”的做法提出质疑。该项目也会对歧视孕妇的机构提出质疑。
1973 年 5 月 14 日,最高法院对“弗朗蒂罗诉理查森案”做出了判决,这是金斯伯格第一次独立在最高法院出庭的案件。从理论上来说,金斯伯格又一次获得了胜利:最高法院推翻了认为女性军人莎朗·弗朗蒂罗的工作对她家庭的重要性亚于男性军人对他家庭重要性的规定。威廉·布伦南大法官撰写的判决书听起来似乎是女权运动的胜利。“传统上,这种歧视常被认为是‘浪漫的父权主义’而被正当化,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并不是将女性捧在高台上呵护,而是将她们关进了充满限制的牢笼。”布伦南大法官写道,这完全就是女权律师的原话。但在该案中,金斯伯格还是没能成功地让五位大法官赞同一个更广泛的原则,即大多数基于性别区别对待的法律都是违宪的。威廉·伦奎斯特大法官是该案中唯一的异议大法官。他告诉《洛杉矶时报》:“我老婆很久之前就已经接受了自己嫁给了一个男性沙文主义猪的事实,而我的女儿们对我做的任何事都毫无兴趣。”
但在这个案子中,金斯伯格学到了将伴随她终生的一课。她一直在试图教化其他大法官,而且她也不打算放弃。但她后来承认:“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一个观念。我认为,社会变革需要逐步累积、循序渐进。真正的、可持续的改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才会发生。”她必须保持耐心。她必须计划好策略。而且她偶尔需要装聋作哑。
金斯伯格的女权运动伙伴们时常火急火燎地想要马上改变世界,这时候金斯伯格就会说服他们从她的角度看待问题。“她坚持我们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去改变法律,”金斯伯格在美国民权同盟的同事凯瑟琳·帕拉提斯后来说,“‘只向最高法院提交符合逻辑的下一个案件,’金斯伯格总是这样提醒我们,然后下一个,再下一个。‘不要争多求快,不然可能会输掉本应赢得胜利的案子。’她经常说,‘这个案子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我们一般都会听从她的意见,每次我们不听她的时候就总是输掉诉讼。”
(本文摘自《异见时刻》)

扫描左侧二维码下载,更多精彩内容随你看。(官方微博:新浪新闻)
推荐新闻
- 【 新闻 】 华为高管回应“在澳裁员” 现场一片笑声
- 【 军事 】 印巴两国的造舰实力能有多大差距?
- 【 财经 】 纽约年轻CEO被分尸 现场还有插电的电...
- 【 体育 】 詹姆斯三双穆雷28分 湖人逆转未果负掘...
- 【 娱乐 】 陈妍希自弹自唱再次悼念黄鸿升
- 【 科技 】 新浪5G Open Day第二日!数十位大咖发...
- 【 教育 】 等待上岸的公考生:考上能让人“高看...
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4000520066
举报邮箱:jubao@vip.sina.com
Copyright © 1996-2020 SINA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新浪公司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