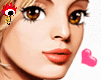| 河南四成艾滋患者退出治疗 部分地区产生耐药性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30日13:28 新京报 | |||||||||
 一个由母婴渠道感染艾滋病的9岁女孩正在打吊针,这只能减缓她的一些并发症状,真正的救命药还是抗病毒“鸡尾酒”套餐。  柘城县双庙村一位村民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口腔内部已经出现霉菌感染,前来巡诊的张可医生将症状拍了下来,用做今后的研究资料。本报记者 李冬 摄 本报记者高明北京河南报道 本报记者李冬摄影 ●头疼头晕、视力模糊、四肢发麻、腹痛腹泻……是艾滋病感染者服用“鸡尾酒”套餐后的普遍反应,调查显示:目前河南地区有四成患者退出治疗。
●艾滋病感染者不规则用药带来“耐药性问题”,这成为卫生部门关注的一个新问题。 专家对此表示忧虑:“一旦出现大面积耐药反应,我们将缺乏替代药物方案”。 ●相关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病人发病时机偏晚。专家指出:这使得患者出现症状时免疫功能就已偏低,治疗时机被耽误。 ●培训有临床经验的一线村医是改善感染者治疗的一个关键。收入偏低是村医们面临的现实难题。“对于村医不能光讲奉献,补贴和培训问题都应该解决。” ●印度、泰国生产的S30在艾滋病高发区很抢手。该套餐的治艾骨干药物是拉米夫定,由于专利原因,这一药物目前尚不能在国内生产。 王秀玲的手一碰到药盒,心就揪了起来。 撕开药袋,把袋中的白色粉末倒入搪瓷杯里,添些水,用筷子搅和几下,闭着眼睛仰头喝下去,她的胃立刻疼了起来,伴随着恶心手脚开始发麻、无力,头也晕沉起来。随后服用的还有两颗胶囊和一粒片剂,同样难吃。 这三种药搭配在一起便是“鸡尾酒”套餐———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由国家免费发放,村医说“吃了就可以救命”。 15天前,王秀玲第一次领到药———“像抱着刚出生的儿子”。 说明书上说,吃药后会产生不良反应,但她却没想到会如此严重:端起碗就犯恶心,吃啥吐啥,身体像被抽了筋似的轻飘无力,甚至在床上翻个身也会气喘吁吁。 第16天,王秀玲把床头的药扔到了床下,不再服用。 双庙村免费发药之后 尽管谈药色变,但双庙村几乎所有病人家里都堆存着大量药物,能坚持服药的人却只有10% 上述场景发生于去年6、7月间。今年3月4日,42岁的王秀玲已卧床不起。 王是河南商丘市柘城县尚旺乡双庙村村民,3年前,她与丈夫张子玉同时被查出是HIV感染者。 双庙村是河南省艾滋病高发区之一,2003年被确定为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在年前的一次普查中,该村HIV感染人数已达到474人。 2003年6月,双庙村开始免费发放抗病毒药物。 “按人头共发放了474份。”卫生所村医朱渊伟说,不到1个月后,他发现大多数领药者停止服药了。 “又酸又咸还有些甜,真不知道是什么怪味。”一位村民说,本来还能下地干活,身体也觉得不错,可一吃药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头疼头晕,视力模糊,四肢发麻,腹痛腹泻,浑身生疮。 另一些村民则反映,吃药后肝功能也变坏了,有人去医院还查出了严重贫血。 王秀玲正是停药者之一。大约半年后的2003年底,她开始发病,体重骤降了20公斤,全身长疮流脓。每顿饭只能喝些稀粥,由于嘴里严重溃疡,一天也很难吐出两个字。 44岁的张子玉说,他清楚妻子活不了多久了,他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每天四处凑钱去买一瓶七八元钱的消炎水,给妻子吊瓶。看着药水一点点往下滴,他心里会踏实许多。 尽管谈药色变,双庙村几乎所有病人家里都堆存着大量药物。 “免费的东西不领白不领。”朱渊伟说,有次他在村头的垃圾堆里捡到了几盒没有拆封的药。从那以后,他就挨家挨户上门说服教育,今年1月,停药的村民才基本不再来领药了。 目前,朱渊伟总共发放88人份的药。 “但坚持服药的也就几个人,还有几个人断断续续地服用。”朱渊伟说,“绝大多数的患者已经退出治疗,严格说,双庙村能坚持服药的人最多只有10%。” 张可医生的不完全调查 “根据我的调查,目前在河南地区应该有四成患者已退出治疗,其中绝大多数人在1个月内停止服药。” 一边是奄奄一息的病人,一边是尘土覆盖的救命药。 “我现在真是心急如焚。”到双庙村巡诊的张可医生说。 张可,北京市佑安医院传染科主治医师,艾滋病防治专家。1999年加入艾滋病临床治疗工作,5年来他几乎跑遍了河南省的主要艾滋病重点村庄。对艾滋病情况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是张的一个工作重点,其次则是帮助这些地方培训村医。 3月3日至3月18日,张可再下河南,对艾滋病高发区的免费治疗情况进行了一次不完全调查。通过与当地防疫站人员、村医和患者的接触,他得到了初步调查结果: 商丘市睢县东关村:免费发放30多人份抗病毒药,坚持服药者占90%。 开封市尉氏县邢庄乡水黄村:发放56人份抗病毒药,1人退出治疗,1人减量服用。 开封市尉氏县邢庄乡屈楼村:发放37人份抗病毒药,2人因副作用退出治疗。 南阳市宛城区溧河乡十里铺村:发放68人份抗病毒药,退出治疗者超过40%。 周口市沈丘县白集镇:发放1200人份抗病毒药,700人已退出治疗。小李庄村免费发放170人份,约40%左右患者退出治疗。 周口市商水县:免费发放37人份抗病毒药,32人退出治疗。 驻马店市上蔡县:免费发放1700人份抗病毒药,400人退出治疗。 驻马店市新蔡县:免费发放300人份左右抗病毒药,68人退出治疗。 记者随张可医生调查所见,许多村医和防疫站人员都强调,所谓的“坚持治疗”也就是坚持领药,至于病人回家后究竟有没有吃?有没有完全按要求吃?很难掌握。 “根据我的调查,目前在河南地区应该有四成患者已退出治疗,其中绝大多数人在1个月内停止服药。”3月20日,张可伸出四个指头说。 吴仪副总理反复叮咛 她到河南视察农村艾滋病防治工作,每次与艾滋病患者握手,总是要问“有没有坚持吃药啊?”临走时又会反复叮咛“一定要坚持服药啊” 2003年3月,卫生部与11个省的卫生厅长签订了《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全国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在河南、河北、山西、安徽等地启动。在示范区内,感染者得到了免费药物治疗。 同年9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联合国会议上作出承诺,中国将为5000名城乡低收入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 “免费药物挽救了大量艾滋病感染者的生命,目前一些重点村的死亡率与前两年相比已大大降低。”3月10日,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治疗与关怀室主任张福杰说。 让张可感到欣慰的是,此次河南调研的过程中,免费药物的效果已在许多患者的治疗中体现出来。睢县东关村43岁的杨四群一年前开始发病,体重降到了60斤以下。去年6月坚持服药至今,他的体重已升到了116斤,如今已能下地干活。 “政府免费发放药物的政策是中国艾滋病感染者的福音,在国际上是绝无仅有的。”根据张可医生的介绍,河南新蔡县2002年的艾滋病死亡人数是40人左右,免费药物发放后,去年死亡人数下降到6人,今年至今为止死亡人数为零。 但张福杰也承认目前农村吃药情况并不理想,他提供了两组数据: 截至2003年10月底,在全国九个省范围内,5289名艾滋病感染者接受了免费药物,两个月后仍服用药物者4247人,退出比例达到20%。 截至2003年12月底,全国接受免费药物的艾滋病感染者增加到了7000多名,但退出治疗的人数比例目前上升至25%。 张福杰坦承,由于农村工作的复杂性,目前中国CDC(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对免费药物的服用情况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也缺少一手的调查资料。 张福杰提供的另一个细节是———2003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到河南视察农村艾滋病防治工作,她每次与艾滋病患者握手,总是要问“有没有坚持吃药啊?”临走时又会反复叮咛“一定要坚持服药啊”。 某些地区出现耐药问题 “不规则地用药,会造成病毒株的耐药性,这种耐药性非常难治,再传染给别人就更可怕了” 一个更为严峻的事实是,艾滋病感染者不规则用药的危害不仅限于其本人。 卫生部艾滋病临床专家组副组长李太生介绍,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长期治疗过程,目前来说甚至是终生用药。 “用两天停两天,还不如不用药。”李太生说,“不规则地用药,会造成病毒株的耐药性,这种耐药性非常难治,再传染给别人就更可怕了。” 李太生的意思是,产生耐药性的病人如果再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则被传染者同样具有耐药性。 “另外,由于药物的毒副作用,不规则用药会使病人加速死亡。”李太生说。 3月10日,张福杰透露:“近期,中国CDC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对小范围内的免费服药患者进行试验发现,目前某些地区已出现了耐药问题。” “局部地区的耐药有可能扩散到全国范围,而我国抗病毒治疗药物资源有限,一旦出现大面积耐药反应,我们将没有替代药物方案。”张可对此忧虑重重。 当场吃药仍有冒领者 在河南,部分地方政府向艾滋病感染者每月提供50元—200元的代金券,发放现场却出现了冒领者。 3月4日中午,柘城县卫生局局长杨学林带着两辆采血车赶到双庙村。 “又要抽血化验!你们都抽了不下20次了,代金券承诺1月发,可到现在也没见影。”一位村民指着杨的鼻子质问。 “其实代金券已经到位,之所以拖着不发,就是因为名单里混进了太多假冒者,这次抽血化验就是要做最后筛选。”杨一脸苦笑地作出解释。 在河南,部分地方政府向艾滋病感染者每月提供50元—200元的代金券,患者凭券支付发烧、腹泻等感染并发症的治疗和药物费用。 一些贫困的村庄里,希望获得这种代金券显然不仅是艾滋病人。而冒领者甚至出现在发放抗病毒药物的现场。 双庙村艾滋病感染者朱学元回忆了第一次领免费药时的情景—————防疫站人员要求当面把药吃下去,否则不给药。 “这简直是胡闹!”朱学元说,他回家看了说明书才知道,有些药必须在饭前吃,有些药则要求在饭后吃。 “要求当场吃药也是迫不得已,就是要吓退那些来冒领的人!”朱渊伟当时参与了发药工作。这位村医说,一些没病的村民找来已感染的亲戚或朋友顶替自己抽血,试图领取免费的药物。 “即使采取了(当场吃药的)措施,最后发放的474人份药物中,至少还有100份是被冒领的。”朱渊伟说。 记者在上蔡县文楼村所见,村民们排队在村卫生所领取各种免费药品。而村里几乎所有三轮车上都竖着一根棍子,在村民家的屋里屋外,墙上都钉满了钉子。 棍子和钉子是用来挂吊瓶的。当地的一位村干部说,不管身体舒不舒服,领药输液在村民眼里已成了一种待遇和享受。 “我去过文楼村,在卫生所我把他们的药单翻了翻,发现大多数药对治疗起不到丝毫作用。”张福杰说,泛滥输液不但浪费有限的防治资金,还带来大量医疗垃圾如何处理等问题。 CD4+细胞计数与用药时机 CD4+细胞计数的降低是引起人体免疫缺陷的主要原因,但我国病人的发病时机偏晚,使得治疗时机有可能被耽误。 实际上,药物发放中存在的问题还不仅于此。 张可介绍,目前免费药物主要由各县防疫站或村医负责发放,但并不按治疗标准,而是按人头发放———只要在验血中测出HIV阳性者即可领取。 “这就存在一个问题,用药时机完全没有科学性,有的病人CD4+细胞在500左右也开始盲目服用。” 张可解释说,CD4+细胞是艾滋病病毒最主要的靶细胞,正常人的CD4+细胞计数一般在500—1500左右,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CD4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就明显降低,这是引起人体免疫缺陷的主要原因,而CD4细胞计数是预测疾病进程的最重要指标。 “艾滋病患者服用病毒药物,早了会产生耐药性和过多的药物毒性,晚了又可能失去救治机会。”张可说,CD4细胞计数正是决定药物服用时机的重要依据。 张可2004年2月发表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杂志》的一篇研究报告称,对160位已确诊的HIV/AIDS患者进行跟踪随访发现:中国成人经输血感染的HIV/AIDS患者在CD4+>200时机会性感染出现频率较少,CD4+<200时机会性感染的频率明显增加,但发病主要集中在CD4+<100时。 张可说,“欧美感染者发病时,CD4+一般在200左右,但中国农村成人发病时CD4+绝大部分已降到了100,甚至50以下。” “这意味着中国病人的发病时机偏晚。”张可解释说,目前农村地区主要依靠临床症状来确定抗病毒治疗时机,但实际上国内患者出现症状时免疫功能已经偏低,“治疗时机可能已经晚了。” 中国艾滋病治疗现行标准完全按照欧美的CD4细胞计数350确定。张可认为,“这作为国家标准尚可行,但农村地区的临床治疗标准应重新考虑。” 检测费背后的药品账 “目前的免费治疗还存在很多问题,当初我们有很多事没有准备好。” 目前,河南能做CD4+细胞检测的单位仅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家,每次检测费大约200元。不少防疫人员认为,对一个数千人的治疗群体来说,CD4+细胞检测花费太大,而且操作不便。 张可认为:“把患者血样交给各县市防疫站,再统一送郑州检测,每人一年也就检测一次,这不是什么麻烦事。” 他还算了一笔药品经济账:如果一个村HIV检测阳性者有500人,按人头发放需500份免费药物,每份药按每月500元计算,一年需300万元;如果给每人做CD4+细胞检测,根据研究结果,则可筛除70%暂时无需服药者,算上每人200元的检测费,一年只需100万元。“一个村省下200万元。扩大到全省,节约的费用将是个天文数字。”张可说。 但眼下还需要更多的人来算这笔账。3月10日,张福杰接受本报采访时坦言:“目前的免费治疗还存在很多问题,当初我们有很多事没有准备好。” 一线村医排在培训队尾 村医的水平决定治艾工作的成败,但一个现实是每逢临床技术培训,站在治疗最前线的村医却被排到了队尾。 在张可为期两周的调查中,一个特例出现在尉氏县邢庄乡水黄村,该村56人中只有1人退出了治疗,1人减量用药。 “同样的药,同样的病人,在不同的地方效果却完全不一样,这时村医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张可说,很多地方把药发下去就算完事,但如果有村医能及时地对一些可控制的副作用进行说明和化解,就可使更多人坚持治疗。 水黄村47岁的村医刘广岭对自己的成绩非常自豪———去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来河南视察时接见了他。“我与吴仪副总理单独谈了半个小时。”刘广岭说。 事实上,水黄村共有6名村医,愿意给艾滋病人看病的人却只有刘广岭一人。 “在河南地区,有临床治疗艾滋病经验的医生非常少。”张福杰说。 张可则把这个数字具体到了“两位”。“只有参与治疗才能谈得上有临床经验,据我所知,目前河南省只有郑州六院的郑云大夫和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张国范大夫两人在接诊艾滋病患者。” 张可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县级以上的医务人员绝大多数不愿参加艾滋病的诊治工作,因此所有的重担几乎都压在了村医身上。 “他们的水平和能力将决定中国农村整个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成败。”张可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对村医的培训,在每个村培训一至两个骨干力量,并尽快将比较实用的诊治方法传授给他们,使患者就地治疗、就近治疗。 张可本人正在做这件事,而这件事并非他一人所能够完成。 一个矛盾的现实是,每逢临床技术培训,站在治疗最前线的村医却被排到了队尾。 张可说,自1999年以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河南省卫生厅多次组织艾滋病防治培训班,但有村医直接参加的却并不多。 “我们根本学不到任何实用的东西。”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医抱怨说,现在的培训一般是逐级培训,中国CDC先培训省级医务人员,省级再培训市级,市级培训县级,但到了村级却往往戛然而止。即使有培训,也大都是找本书读读了事。 “目前培训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有临床经验的师资力量,”张可说,“如果培训者本身毫无临床经验,则培训意义不大”。 收入低影响村医积极性 张可认为,对于村医生不能光讲奉献,补贴和培训问题都应尽快解决。 对于积极参与艾滋病治疗的村医们而言,收入偏低是又一个现实难题。 水黄村的刘广岭说,他每月的收入不及村里其他村医的五分之一。“以前每月收入五六百元不成问题,但自从开始给艾滋病人瞧病后,村里人吓得都不敢再跨进我的诊所,如今每月能赚100元就不错了。” 现在,艾滋病感染者成为刘广岭惟一的收费来源。 “他们去县级以上医院,没钱是不会有人给他们看病的,但到了我这里就不同了,大家都乡里乡亲的。”刘广岭说,“有的人一进门,就嚷着烧得受不了。你一提钱,他就会说‘你就眼看着我死了吗?’心一软,我只好给他们看,该打针的打针,该给吃药的吃药,账只能赊着。下次他来了你再提起旧账,病人还会生气,‘我就这三五天死了吗?不用怕,等我好了会把钱还你。’” 艾滋病人的死亡是一件寻常事,在刘广岭诊所西屋的废纸箱上,放着4厚本用铁夹夹住的发黄纸张。 “这些都是烂账。”刘拍了拍铁夹说,“算算应该能有个3万元吧。” 为了养家糊口,现在刘广岭必须下地种田。谈到自己所承担的另一些义务,他也有几分怨气。 “每月领取、发放免费药物都是我们村医的工作,但来回县里20元的车费得自己掏;县里一旦需要一些涉及艾滋病孤儿、孤老和孕妇的数据,我们要去挨家查询、统计。做这些工作,我们没拿到给一分钱补助。” 双庙村村医朱渊伟说,县里当初指定他专门负责村里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曾许诺将代金券面值的18%作补贴发给他,后来又说干脆直接发补贴金,但最后却没了说法。 张可认为,对于村医生不能光讲奉献,补贴和培训问题都应尽快解决,不然他们的积极性必然受挫,最后受影响的将是农村整个艾滋病防治工作。 神秘的S30 S30也是一种治艾“鸡尾酒”套餐。在艾滋病高发区,搞到一瓶S30是很多危重病人最后的奢望。 在张可巡诊农村的过程中,经常有村民拉住他悄悄发问。S30也是一种治疗艾滋病“鸡尾酒”套餐。很多村民说,S30几乎没有副作用,吃一个月花费还不到500元。最主要的还是特别见效,很多眼看着要死的病人吃了S30竟能奇迹般转好。 在艾滋病高发区,搞到一瓶S30是很多危重病人最后的奢望。 据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医生透露,目前,S30主要是通过病人出国和非政府组织两个途径带入国内。如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红树林支持组织(MSG)、广州“艾滋关怀”和上海血友病协会等都在帮助病人联系这些药物。 “虽然是非赢利性行为,但由于手续不全,他们的药物经常会被海关查扣。”这位医生说,在艾滋病高发区的农村,这些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往往比临床专家更受病人的欢迎。 据张可介绍,我国政府能提供的免费药物基本为四种:齐多夫定、去羟肌苷、司他夫定、奈韦拉平。这四种药物只组成两种“鸡尾酒”方案:齐多夫定+去羟肌苷+奈韦拉平;或者去羟肌苷+司他夫定+奈韦拉平。 “是药三分毒,任何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对人体都有毒副作用,在治疗的同时对人体机能也有破坏作用。”谈到河南患者的服药反应,张可说,目前国内使用的四种药物毒副作用确实比较明显,主要反应在抑制骨髓再生、肝脏损害和影响外周神经系统等方面。 “服药反应因人而异,出现贫血、影响视力或者手脚麻木、腹痛腹泻等都属正常。”张可说,“根据调查,治疗中两种方案疗效基本一样,副作用也基本相同。因此,患者不能用方案1时,意味着方案2也无效。” S30的基本组方则是拉米夫定+司他夫定+奈韦拉平。“虽然只换了一种成分,但药效却完全不同,拉米夫定是治艾的骨干药物,就像烧菜必须要放盐一样。” 张可介绍说,与我们现有的药物相比,拉米夫定的毒副作用轻微得多。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所有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组方中,都包含了拉米夫定。而在国内现有四种药物的基础上,若有拉米夫定加入,5种药物可以组成5~6种套餐,患者选择的余地就大多了。 “心腹之痛”拉米夫定 治艾骨干药物拉米夫定由于专利原因,无法在国内生产。专家认为,有效解决办法是强行仿制。 拉米夫定是葛兰素史克公司(GSK)的专利药品。虽然中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曾多次与该公司协商,但对方始终拒绝给予在国内生产的许可。张可说,多年来,葛兰素史克在中国销售主治乙肝的含有拉米夫定的双汰芝,却始终没有上市针对艾滋病的单一剂型的拉米夫定。 “用双汰芝治艾价格相当昂贵,每月需要1800元,再加其他两种国产药物,每年患者为此要支付约20000元,不论是政府和个人都难以承受,并且在配方选择上会受到限制。” 张可介绍,目前国际上有20多种抗艾药物、10多套鸡尾酒治疗套餐,病人可以选择的余地较大。而国内生产和免费发放的4种药属于专利期已过和未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仿制药。同时亦有资料显示,上述4种国产药物在国际上均为早期治艾药物,目前已不属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艾滋病一线用药。 “但现在我们别无选择,拉米夫定一直是我们的心腹之痛。”张福杰说。 一个事实是,现有的四种免费药物已经是目前中国政府全力而为的结果。2002年,在国家发改委组织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快速审批,齐多夫定、去羟肌苷、司他夫定三种药物分别由东北制药总厂和上海迪赛诺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上市。 张可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强行仿制,实现拉米夫定的国产化。 “强行仿制”是2001年世贸组织多哈协定的一个条款,指挽救生命的药物可以不受专利保护,如果发展中国家出现某种非常严重的流行疾病,政府有责任来保护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就可以宣布进行仿制。 据张可透露,上海迪赛诺正是拉米夫定的原料药生产者,印度和泰国的仿制药原料也来自于这家公司。 与葛兰素史克“谈判顺利” 强行仿制拉米夫定最大的绊脚石是“行政保护”协约,相关谈判尚未提及“强行仿制” 有消息显示,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面对国内艾滋病泛滥,几年前就开始强制仿制拉米夫定,抗病毒药物的价格从每年的几万元降到了现在的2000元—3000元人民币,由此挽救了大量病人的生命,国内艾滋病的疫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 事实上,河南病人所说S30正是来自印度和泰国的仿制产品。 但中国为什么迟迟不进行强行仿制? “中国强行仿制拉米夫定最大的绊脚石不是专利保护,而是在加入WTO前签署的一款‘行政保护’协约。”张福杰说。作为中国CDC人员,张参加了与拥有艾滋病专利药所有公司的谈判—————包括施贵宝、葛兰素史克、默沙东、雅培、勃林格殷格翰等。 据国家商务部WTO司的官员介绍,所谓“行政保护”,是指加入WTO前中国政府与70多个国家签署了协议,承诺在一定时期内,为对方企业的知识产权提供行政保护。 “国家卫生部与葛兰素史克的谈判和交涉从没有间断过,而且最近进展顺利。”张福杰说,“相信几个月内,拉米夫定的问题能得到解决。” 至于结果会是强行仿制,还是有条件的大幅减价,张福杰称“不便透露”。 张可对谈判的结果则并不乐观:“我国是个乙肝病患者大国,1998年双汰芝在中国上市以来,葛兰素史克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对这块肥肉他们不会轻易松口,我们必须强行仿制。” 3月28日,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媒介经理肖伟群透露,目前该公司与中国政府关于拉米夫定的谈判仅限于政府采购,如谈判顺利届时药品价格将比走商业渠道优惠很多,而强行仿制并不在此次谈判内容中。 相关专题:河南76名干部进驻艾滋村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河南76名干部进驻艾滋村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