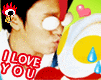| 新闻追踪:艾滋新药临床实验疑云重重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4月20日14:54 青年参考 | |||||||||
|
香港《文汇报》关于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新药试验的报道是否可信?那些艾滋病患者到底在接受试验前是否完全知情?几位患者的死亡与新药试验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地坛 本报特约记者 陈磊/发自北京 疑云一:朱茂龙之死 2003年6月26日,从北京地坛医院回家23天后,HIV患者朱茂龙在河南柘城县岗王乡双庙村的家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37岁的妻子赵玉玲独自为他操办后事,一件新衣服,一口棺材将丈夫葬了。赵玉铃现在也不明白,丈夫为什么去了一趟北京之后就这么快去世了。 赵玉玲称去北京前,朱茂龙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烧、出麻疹,但身体总体状况还不错,在家里也照常从事农活、驾驶等劳作。 但于2月份和其他患者一起到北京进行了两天治疗后,赵玉玲接到丈夫的电话,说打了两针就出现发烧症状并出现了皮炎,第三针之后,朱茂龙被医院停止了实验,返回了河南老家。回到河南后三天,朱茂龙的情况有所好转,这时医院打来电话,得知朱茂龙情况好转时,又将他叫回了北京,继续完成了整个疗程。 赵玉铃回忆说,当朱茂龙结束疗程回到河南后,她发现他的体力大不如以前,已经不能从事农务,经常咳嗽、发烧、胸闷,体重也开始下降。 到后期,朱茂龙开始出现持续高烧、胸闷的症状,已经不能进食,每天只能靠鸡蛋汤维持。其间,朱茂龙告诉妻子自己非常难受,“我实在熬不下去,还不如死了!”这是不爱说话的丈夫对赵玉铃留下的最后几句话。 疑云二:“幸运”的HIV患者 “让这些人参加人体试验,是我帮他们联系的。”双庙村HIV患者朱进中告诉《青年参考》。 2002年年底,朱进中在北京市佑安医院,作为该院第三期人体试验自愿者接受试验治疗。治疗期间,为帮助同村HIV患者寻找治疗机会,朱进中找到了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临床研究中心,向该中心医生赵红心讲述了同村艾滋病患者的悲惨遭遇,希望地坛医院能够给该村的患者提供人体试验的免费治疗机会。 2003年2月,北京地坛医院医护人员来到双庙村采集血样。“当时化验的现场,秩序相当的混乱,几百名HIV的患者都要求对自己进行采血化验。”陈一凡说,最后共采集了100多个HIV患者的血样,带回北京化验,后来有18个人被选中到北京进行药物试验。这些化验的结果和入选者的名单,就由朱进中带回了老家。 年仅30岁的村民范伟就是被选中的18人中间的一员。“当时得知自己被选中到北京的医院接受治疗,我感觉真是太幸运了。”范伟回忆当时的感觉是,说不定这次去北京病就能治好。 陈一凡在解释当初在村里筛选受试者的标准时说,按照美国公司方面的要求,医院选择的都是病情比较严重的患者,CD4的指标全部要在200以下,以上的,表示虽然是HIV病毒的携带者,但还没有进入发病期。而在200以下的,就是已经发病的危重病人,一般情况,寿命都在半年左右。 疑云三:36名受试者7人死亡 据朱进中介绍,他带队来地坛医院的这些病人住在地坛医院的一区病房,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来自河南睢县东关村的另外18名受试者,他们与双庙村的受试者进行的是同一人体试验。 对朱茂龙的死亡,朱进中并不感到奇怪:“他是自己要求到地坛医院进行人体试验的,他并不在18人的名单中。朱茂龙当时实际上已到了晚期,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但在试验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又死了一个叫朱瑞华的人,这个人在18人的中选名单中。他的同伴王化强告诉记者,朱瑞华死时的情况要比朱茂龙惨得多。朱瑞华的死亡时间在2003年10月12日,症状也是持续的高烧。最初的注射完成后,7月份还随同王化强一起到地坛医院接受化验,到8月份的时候,朱瑞华的双眼就因为持续的高烧而失明。随着病情的逐渐恶化,后来的定期化验,朱瑞华就再也没有参加。 让双庙村受试者更不安的是,在7月份第一次观察期内返回北京进行抽血化验时,患者们从东关村受试者口中得知,他们村也有两位受试患者观察期内死亡。4位患者观察期内死亡,对其他受试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12月16日,同属双庙村18人中42岁的王爱琴也因病情恶化而在家中去世。 到目前为止,据王化强掌握的情况,包括2003年6月份东关村死亡的两人在内,东关村18位参加实验的患者中已有4人死亡。两个村共36名参加试验的患者共有7人死亡。 疑云四:CD4(免疫功能)200以上 对于其他名单中受试者的死亡,朱进中则回答:“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局面!”最初带领村民看病的朱进中对出现的问题感到迷惑:“当时这18个受试者都是经过化验挑选的,按理说接受人体试验都应该是安全的。” 陈一凡认为,朱进中的看法是错误地以为医院筛选病人的标准是要求CD4指标在200以上的HIV病毒携带者参加。“我们当时也有疑问,按照以往的通常情况,药物试验的厂家都要求寻找CD4指标在200以上的患者试验,只有这家公司专门寻找危重病人,我们也有担心,万一死了人怎么办?”陈一凡说。但是,最后医院还是按照公司的要求选择了符合标准的病人。 王化强说,他们曾找到地坛医院医生赵红心和卢连河询问患者的死亡原因。据称,当时卢连河医生表示,死者的死亡原因没有必要跟你们说,给你们药,还给你们钱,你们这些人回去。要是没有抗病毒药物,只能活上两个月。受试者希望医院解释同伴药物试验不久死亡的要求同样遭拒绝。 “从地坛医院来村里给大家抽血化验、治疗开始,一直到11月2日观察结束,医院的工作人员每次抽血之后都拒绝将化验单交给患者。”王化强说,在出院后最后一次在地坛医院化验时,在他们一再坚持下,医院将当时的化验结果交给了患者,王化强等人发现这次化验单上显示的CD4(免疫功能)指标比接受试验治疗前低了很多。 关于对受试死亡者的死因解释问题,陈一凡说,这些受试者有些虽然是在观察期内死亡的,但死亡的时间是在离开医院以后,地点都是在河南老家,客观上,医院无法获取足够、可靠的信息对患者的死亡做出说明,出具相应的报告,医院现在无法做到这点,他们只能在此项试验的最后结论小结中注明出现死亡的情况。 而王化强等受试者则在后来的公开信中提出:“在观察阶段,双庙村18人中有2人死亡;患者病死率高于同期我村感染者平均的病死率。2003年,我村大约因艾滋病死亡10人。” 疑云五:患者事先是否知情? 2003年3月5日,36名试验者外加一名自费要求参加试验的双庙村患者朱茂龙一同被要求签署一份“患者知情同意书”。 据“患者知情同意书”显示,他们将接受16针药物注射治疗。据当时参加试验的HIV患者王化强回忆,当时他只记得医院医生赵红心告诉他们:“能够得到这次治疗,是幸运者,这个针剂好得很,可以延长生命,保证20年没有问题。” “当时,医院让我们签‘患者知情同意书’。我们当中没几个人识字,更别说中间的英文字母。也不清楚这些即将注射进自己身体的药物,到底是叫治疗还是叫研究更为合适。”范伟回忆说,当时出于对医务人员的信任,患者们都毫不犹豫地签署了这份“患者知情同意书”。签完字后,同意书就由医院收了回去。 2003年5月17日,当药物注射疗程完毕,进行几天的观察之后,试验患者被通知回家,治疗转入了观察期,地坛医院给每人支付了1950元的报酬。 “我们确实不知道这次治疗的是研究,也不知道会带来风险。”王化强说,在“知情同意书”中写明:此次临床治疗的主要观察方和美国病毒基因公司希望每位患者都了解以下内容:被详细告知此次实验的性质和目的,被详细告知药物的试验补助和实验用药,被详细告知可能因药物试验而产生的各种不适和症状……被详细告知患者在试验中可获得的利益。 “现在想起来,我们是在被欺骗的背景下签署了这份‘知情同意书’的。我们没有得到知情同意书副本。”王化强介绍说。而后来得到的“患者知情同意书”中却明确说明:“参与治疗的患者将得到已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及权益书的副本”。 陈一凡认为,当时患者是知道他们是作为药物试验的自愿者参加进来的。“我们的工作人员逐一在病房向受试者宣读了‘知情同意书’,并要求他们在上面签字。” 疑云六:“知情同意书”副本 11月2日,患者找到卫生部,反映地坛医院给他们治疗的过程中出现的伤亡并询问有关试验补偿情况,当时的接待者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专家张福杰。张福杰告诉他们,如果怀疑药有问题,他们可以到法院通过起诉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几位患者并不信任张福杰,因为就在北京地坛医院门诊部的墙壁上,张福杰同时作为地坛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名字就贴在那里。 11月,王化强和其他几位病人经介绍,找到“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万延海求助。2004年1月,万延海和王化强等人一起来到北京地坛医院,索要患者“知情同意书”。 王化强等人发现,当时医院要求受试者签署的“患者知情同意书”上只有患者签字,而无地坛医院签字。万延海和几位受试者要求医院提供“知情同意书”副本时,地坛医院的卢连河医生才将签字补上了“知情同意书”。 而“知情同意书”中,关于“胸腺核蛋白制剂(TNP)用于治疗HIV-1感染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的试验目的,和“我们也许不能从这项研究治疗中直接受益,但是通过研究可以获得胸腺核蛋白制剂注射安全性和有效性资料,研究人员可以将它应用于长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治疗”的权益表述,王化强表示,这实际上也是他们在找到万延海之后才得知的。 对未有将患者“知情同意书”的副本交与患者,陈一凡说,这是他们的失误。当时他们认为这些HIV患者有文化的很少,要了也没有用,所以就没有将副本给付患者。 相关专题:青年参考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点卡 ● 天气 ● 答疑 ● 交友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青年参考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