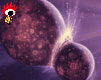| 中国西南防艾新探索:“小姐同伴教育”进行中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15日14:39 南方周末 | |||||||||
|
西南的防艾新探索:“小姐同伴教育”进行中 关键词 中英项目——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英国政府出资,与我国合作,旨在提高我国对艾滋病的有效应对能力,遏制日益增长的艾滋病传播速度。 小姐同伴教育——培养性工作者中的骨干人
当性传播成为艾滋病蔓延的主要途径时,对性工作者这一传播链条关节点的干预,就成为不得不面对的任务。 一项名为“小姐同伴教育”的防艾探索正在云南和四川两地推行。记录人物故事的同时,我们尤其关注其间的政府角色。 政府究竟应如何行事?从打击“卖淫嫖娼”,到直面性工作者——这的确是一个挑战。 杨姗姗:小姐领班的双重生活 □本报驻京记者 刘鉴强 7月1日下午2时,28岁的杨姗姗身着艳丽的傣族长裙,袅袅娜娜走在云南保山的街道上。她没有为裙子配上漂亮的傣族式小包,而是肩挎一个大大的黑色布包。 “你知道我为什么用这么个大包吗?”她说,“我可以用它装很多安全套。” 在云南防治艾滋病领域,杨姗姗是个不大不小的名人。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以下简称中英项目)的一些官员和工作者,会时常提到她的名字。在昆明,一位性工作者也对记者提到:“保山有个杨姗姗……” 杨姗姗是“小姐同伴教育”的一名工作人员。她的状况有点特殊,即使在全国也很难找到类似的第二个人。她做过舞厅小姐,现在是小姐领班。夜里与客人喝完酒,小姐妹们散去,她关上大门,大睡一场,第二天下午,就背着大包,里面装着安全套,走街串户,去找那些站街的性工作者,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知识。 杨姗姗顺着保岫东路悠然走过。保山是云南西部的一个城市,别称“兰城”,以种植名贵兰花得名,但经济并不发达,街道上闲人很多,男男女女在路边站着,坐着,蹲着。 杨姗姗脸上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眼睛却已扫过了路边的所有女子。“这个是站街小姐。”她轻轻对记者说。那是一个30多岁,身穿白色套裙,坐在路边花坛上的女士。“那个也是。”她眼睛望着远处。那是一位年纪更大的女士,站在路边的树荫里,无所事事。“她们在等客人。”杨姗姗说,“我都认识她们,但是因为你在我身边,她们不会与我打招呼。平时我一个人,她们老远就冲我笑。” 走到保岫东路208号,一个沿街的铺面,上写醒目的大字:“中英项目欧洲前景集团健康亭”。杨姗姗弯腰开锁,将卷帘门“哗啦”打开,笑道:“到了。这就是我的地盘!” 这个被称为“健康亭”的地方,是中英项目的一处据点,针对那些流动性强的“站街”性工作者,提供卫生咨询服务。杨姗姗被聘为这里的负责人。 屋子的墙壁上贴满了防治艾滋病的宣传画,门右边摆着一张麻将桌,左边是一个玻璃橱柜,里面摆着一些健康宣传小册子,成盒的安全套,还有一个塑料男性生殖器,这是杨姗姗向性工作者传授健康知识的道具。 有时候,她会呆在这里,和那些“姐妹们”看电视,聊天,打麻将,谈论防病知识,期待这里成为性工作者们喜欢的俱乐部。 杨姗姗坐在藤椅里,眼睛看着外面的车来车往,一边等她的姐妹们,一边讲她的故事。 “保护我舞厅的小妹们” 我从来没想到会做这个工作。本来,我白天卖手机,晚上在舞厅当领班,很忙。 两年前,中英项目办的宋鹏飞医生找到我,希望我做“同伴教育”的工作人员,在小姐中培养一些骨干,再让这些骨干在小姐中宣传防治艾滋病的知识。我去听了两次课,觉得做这个事情挺好。这个工作如果没人做的话,艾滋病不就蔓延得特别快吗?能保护自己舞厅的小妹们,并且一传十,十传百,像网一样,把知识传播开,不是很好吗? 我给父亲打电话说这个事——家里都知道我在舞厅工作,我从不向他们隐瞒。父亲很支持我,我就把白天卖手机的工作辞了,听老师讲课,晚上回去给小妹们讲。 我采取的方式是与姐妹们逛街,打麻将,到我家里做饭吃。这些场合都可以聊。我会问:“昨天客人怎么样?有没有用安全套?” 你要讲艾滋病,就要把生活带进去,一见面就讲艾滋病,谁会跟你玩?我给她们讲知识,就是在一起玩的时候。她们打牌,我给她们做“菲佣”,倒水,捏背,讲故事。 我们很多姐妹喜欢看《知音》,我也喜欢,我虽然文化不高,但还看得懂。最近有一期讲一个艾滋病人的故事,他有一次在发廊里发生了高危性行为,得了艾滋病,并传染给了妻子。我就和姐妹们聊这个故事。 她们要赚钱,肯定是要出台的(与客人发生性关系)。我会提醒她们,客人怎么样?是熟客吗?一定要用安全套。 有些客人对家庭负责任,会提出用套的。而有些素质低的、对家庭不负责的,根本不用。 我和我舞厅的小妹们感情特别好,有一次我去昆明接受培训,才几天,回到保山,小妹们就抱着我哭。她们特别信任我,也特别尊重我的意见。做小姐的,赚钱不容易,我不扣她们的台费。小姐的领班,一般是要扣小姐的坐台费和出台费的,比如小姐出台赚100,领班会扣10元20元。我的工资每月800元,所以姐妹们说,我是保山最穷的领班。 现在她们出台,会先跟我要安全套。有时我也会做客人的工作。晚上来了客人喝酒,问我:“白天请你出去喝酒,你怎么老不去?”我说我白天在做预防艾滋病的工作,没时间。他们问:“保山有艾滋病吗?”我说:“有啊,多着呢。”他们说:“吓死我了!”现在,当我舞厅里的小姐要出台的时候,有时她们自己不跟我要安全套,但会有客人主动跟我要。 “我与站街女姐妹相称” 做舞厅小姐的很可怜,她们“站街的”就更可怜,要多给她们一点关爱。 我把这里的性工作者分为三类,第一是舞厅小姐,第二是发廊小姐,第三是站街小姐。前两者文化素质高一点,工作场所比较稳定,还好沟通,站街的性工作者就太难沟通了。以前的防治工作,往往很难涉及到她们。 今年,中英项目办想在“站街”的性工作者这方面作出突破,问我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见到这些站街的性工作者,我总是特别难过。 她们岁数都很大,大多数30岁以上,有的40多岁,价钱很低,最多几十元。住的地方只有一小间,除了一张床,就是一个小柜子。她们大半是结过婚的,其中又有半数离婚,家庭很困难,特别可怜,聊到伤心的时候,她们不哭,我自己先哭。 站街的性工作者为什么从事这工作?如果问她们,百分之百是因为家里没钱,孩子要上学,老公没本事,老人要供养。谁不愿意在家里好好过日子?一个住旅店的性工作者告诉我,这几天老下雨,生意不好,她赚了100块钱,给自己买了一把雨伞,给女儿买了一箱方便面,剩下的60块钱捎回家买化肥农药。 我第一次去找她们时,她们以为我是疯子,不理我,有的把我当成推销安全套的。我对她们说:“我是来和你们做好姐妹的。”她们会问:“你怎么可能和我们做姐妹?”我说:“怎么不可以?我也是在舞厅里做过小姐的。” 我与她们姐妹相称。我对她们说,你们不必告诉我真名字,只要随便说个名字就行了,姓也可以。我不能冲她们“哎,哎”地叫啊,我就称她们“赵姐”,“李姐”,有个年纪小的,才17岁,我就叫她“小宝贝儿”,“小乖乖”。 有时候我给她们材料,她们会说:“小妹,我不识字啊。”我说没关系,我也没文化,我讲给你听。说真的,书本上的语言,我自己都不是很懂。有一次我对项目办的老师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我特没文化,和她们好沟通,才找我?” 跟她们交流,做艾滋病知识的宣传,不能照书本上的讲,要是这样讲的话,她们一是文化程度低,听不懂,二是会想,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文化程度比我高?怎么那么神气? 去找那些站街的性工作者时,我会把戒指、项链全拿掉。站街的性工作者自尊心和自卑感都特别强烈,我不能表现得比她们优越。 我做了一些调查,问她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知道她们的回答是什么吗?其中一条是能得到免费的安全套。 “送你安全套,只要你们用!” 我们建立这个健康亭,就是要小姐们来聊天,看电视,打麻将,同时能了解到性病、艾滋病知识。但是,她们太忙了,要拉客人,没时间来这里,我只好到外面去找她们。 我得说服她们用安全套。我们项目的安全套成本是4毛钱一只,但她们还是不能接受,一般是买两毛钱一只的,“反正不漏就可以了。”所以我申请了一批半卖半送的安全套,两毛钱一只,如果她们实在没有钱,那就送给她们。没关系,只要你们用! 有些性工作者会这样想:客人用不用套我不管,只要多给钱就行。很多客人也不想用套。 我跟香港的老师学的,要教她们说服客人,说什么样的话,用什么样的语气,有时我会用一个小妹的身体做模特,教给那些性工作者一些方法。 我还告诉她们,姐妹们要一起来保护自己。只要大家都坚持用安全套的话,客人到了别的地方,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用你们开口,就会主动用安全套。 现在,我已接触了180个人左右,这样,整个保山市隆阳区的街边性工作者,我已接触了一半。现在已经有人主动向我买安全套了,也有人身体不舒服,就打电话找我,我会打车带她去看病,还借钱给她。 “我脸皮再厚,也会害羞” 当我去和那些性工作者聊天时,她们以为我这个工作能赚很多钱,我就乐:“你看我像不像二百五?” 做这个工作,我的月收入就是250元。做公益事业肯定没钱,如果是为了钱,也就不做这个工作了。 为什么做这件事?做见得了阳光的事,内心没负担。自信来自哪里?我现在做的是好事。 我从小就自己选择生活方式。15岁当酒吧老板,是德宏州芒市最小的“老板娘”我坐过台,但没卖过身做过导游在赌场发过牌也赌过钱。我有过痛苦的经历。你看我这手腕上的几道刀疤,我后来买过很多祛疤的药,也去不掉。小时候如果别人关心我,我也不至于把自己糟蹋成那个样子。 那种被歧视的滋味太难受了。别人歧视过我,所以我不歧视别人,我要帮助别人。我从继父那里学会了宽容,要宽容地对待别人。我原来不叫杨姗姗,这是继父给我起的名字。我做防艾的事情,希望给这个名字增添一点光彩。 但是,我很累,那么多的性工作者,我一个人,怎么聊得过来啊?有时我就乱想,赶紧找个人,把自己嫁出去,晚上不必到舞厅上班,专门做白天的工作。 现在我在小姐中发展了6个宣传员。我想,既然是同伴教育,她们在一起,比我更容易沟通。我对她们说,你看,有那么多的姐妹,我一个人也聊不了那么多,你们帮我和姐妹们聊。我教育这几个小妹,如果我的身体吃不消,做不下去的话,她们接着做。如果她们不做,希望一定有人做下去。 小妹们说我的脸皮特厚。为什么呢?因为我找那些性工作者,很多时候她们不理我。她们会说,我忙啊,打麻将呢。她们有的打麻将,有的睡觉,有的接客,有的不见人影。如果有人理我,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晚上多喝两杯,如果不理我,我回来就生气,不许别人理我,说“我烦着呢”。 前几天实在不想做了,因为去跟她们谈,好像我是在求她们,对我根本不理解。我脸皮就算再厚,也会害羞的。 我只希望她们能理解我,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得病,就是对别人好,对社会好。 7月2日下午5时半,杨姗姗与舞厅里的小姐QQ——她两年来的铁杆“跟屁虫”,一起走进一条小巷,去给宣传员发放小证章。几位三四十岁的性工作者坐在临街房的门口,有的打毛线,有的看杂志,正在等着客人。看杨姗姗来了,远远地就笑着打起招呼。 “我前两天病了,你们也不来看我。”杨姗姗嗔道。“哎呀,你也不捎个口信,我们去看你啊。”大家叽叽呱呱地说,“现在好了吗?” “好了”杨姗姗笑着,拿出证章,并拎出一大串葡萄送给她们,“有空了到我那里坐坐啊。” 告别姐妹们,杨姗姗微笑着回家。吃完晚饭,她就要回到舞厅去做另一份工作。她说:“白天的工作让我充实,在做这工作之前,我不知道她们需要我,不知道这个社会需要我。” 相关专题:第15届世界艾滋病大会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第15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