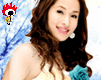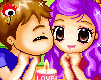| 器官移植大市场悄然兴起 器官来源面临尴尬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16日12:06 三联生活周刊 | |||||||||
|
器官移植:悄然 兴起的大市场 从公正性和有效性的角度考察器官移植,“不掺杂经济和其他因素的考虑”是一个基本原则,而有了官方的准入制度的建立,这一原则才会有实质的保障。
世界各地人们寿命的提高都源自医药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改进,而在医学和技术的突破中,器官移植所带来的震撼力体现在一系列数字上:到2003年,全球器官移植的总数达到936万例。人们对器官移植的依赖也日益加重,在美国,每16分钟就有一个人加入到等待器官移植的行列,而全世界目前等待合适供体器官做移植手术的病人有30万人。 最近,将前沿科技纳入公共谈资的新闻事件是著名演员傅彪的患病。9月2日傅彪因患晚期肝癌,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手术。这是一个初步看来成功的手术,傅彪接受肝脏移植手术的当晚就已苏醒,第二天早上能自己饮水,进少量流食,体征平稳。 仅从外科手术的角度来看,有专家形容我们目前的手术水平达到了十多年前做梦都想不到的高度。武警总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刘振文接受采访时说,过去“换肝”的技术不太成熟,但目前肝移植的长期预后已经和肾移植没有太大区别。作为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惟一有效方法,肝脏移植已经成为一种常规治疗手段。 资料提供的肝脏移植“常规化”体现在数字的飙升:1991年到1998年这8年间我国施行肝脏移植数为78例,并开始出现长期存活的病例;随后移植数量成倍增加: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118、254和486例,到2002年登记处的统计累计是996例次。 谈及被列入到20世纪人类医学三大进步之一的器官移植,美国在该领域占有的重要地位则不可忽视:1954年12月,美国医生约瑟夫·默里第一次成功地进行肾移植手术,1956年美国的唐纳尔·托马斯进行第一例骨髓移植,他们在1990年分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而在1963年,美国斯达卓教授成功地进行了第一例原位肝移植。 不过现在美国的地位受到挑战,挑战来自中国。记者在天津采访时,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说,截至记者采访时止,今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本院内已完成的肝移植手术达到311例。相比较而言,去年美国完成肝移植手术最多的一家医院,总例数也不过是300多例。美国做肝移植手术最多的一个移植中心曾经的最高记录是在500到600例之间,郑虹很有把握地说:“目前看来,今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有望完成的肝移植手术例数,很有可能与这个最高记录持平,甚至超过它们。” 郑虹的自信一个方面源自于对技术水平的掌握。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近日于沈阳召开的2004年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上说,我国器官移植技术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在类似场合,黄洁夫也曾表述说,器官移植技术已发展成为一项成熟的实用性专门技术,我国已掌握了该技术的各个方面。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不完全统计说,截至2003年,我国累计完成器官移植5.5万余例。其中,肾移植5万多例,目前每年完成超过5000例,数量仅次于美国;肝移植3000多例,仅去年就完成1500例。心脏移植取得突破,还开展了胰肾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心肺联合移植等高难度手术。 人们对从医疗系统中获益的追求,使得器官移植手术在中国正在形成一种巨大的需求,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接受采访时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算是个器官移植大国,国外的病人都到中国来寻找供体”。 从官员的角度,黄洁夫描述这种需求的巨大说:目前全国开展肾、肝、心等器官移植的医院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有的医院以为能够做器官移植,就代表着医院的医疗技术达到了一定水平,觉得很荣耀,结果片面追求器官移植例数。 陈忠华则说,目前我们遇到的已经不是技术问题或者是经济问题,而是立法和制度方面的问题。他说:“捐献问题有两个层次,首先是将已经宣布志愿捐献器官的脑死亡病人的器官移植给需要的受体,另外一个就是亲属之间的活体移植,在这两个方面上,我们国家没有任何条例,法规,也没有办法进行管理。” 同样看到问题所在的黄洁夫强调提高器官移植的准入门槛迫在眉睫,他说:“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相关标准、法规建设上跟不上,就可能出现大问题。” 技术之道 著名心外科专家夏求明严格地秉承着传统的价值观念,低调而保守。如今有媒体直接称其为中国的“换心人之父”,不过不事张扬的夏求明在采访中则倾向于强调“集体的功劳”。 中国第一例换心手术并不出自于夏求明,我国的心脏移植记录起自1978年,不过里程碑式的变化发生在1992年,夏求明所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心脏移植获得成功,成功的标志在于,1978年的一例只存活了一百多天,而1992年的心脏移植者杨玉民到目前已经健康存活12年,是我国目前存活时间最长的,这个纪录在亚洲来看也名列“最长”之列,而目前世界上临床器官移植最长生存期限是25年。 回顾那段时期,夏求明定义那是“特殊时期”——“器官移植是在传统治疗手段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治疗方法。心脏移植是当前国际公认的治疗终末期心脏病的有效治疗手段,但只是能够延长人类生命的姑息性治疗,它的代价太大。” 技术问题是最初面临的关口,夏求明说,“心脏移植最先开始时面对的还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大家关注‘排斥’问题”。 1992年前后世界范围内心脏移植的技术指标是,国外器官移植相对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进行原位心脏移植术,在手术最为成功的美国,其存活率只是50%。 杨玉民的手术当时估计的成功率是40%,而在技术上,所有准备工作甚至要前推几十年大量的研究性实验的保障,这其中包括上世纪50年代一度轰动世界的狗头移植术后存活5天的纪录。70年代,肾、肝、甲状腺等多种器官在临床开展的移植工作,就在1992年这个手术之前的1989年,他们进行了心脏移植研究,有6次成功的动物实验。 当时手术的场面相当宏大:1992年4月26日清晨6点,来自血液、麻醉等20多个科室的上百名医护人员一齐上阵,手术先后进行了4个小时,总计缝合1000余针。 从那时候之后,中国的心脏移植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面,有资料说,从1994年至2000年底,我国累计施行心脏移植82例。全国共计有33个单位开展心脏移植,而在此前的1978到1993年的15年中,我国只有6个单位施行7例心脏移植手术。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陈实曾这样表述说,杨玉民这例手术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心脏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心脏移植技术的发展。 心脏移植只是中国器官移植一个技术上的突破。石家庄器官移植研究所李永辉对记者回顾说,我国临床器官移植的开展已有40余年历史,器官移植在我国经历了高潮和低潮的几次反复后,在90年代进入稳定、快速的发展期。 此前李永辉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他说,同济在我国的器官移植方面搞得最早,1958年就进行了狗异体肝移植的尝试。之后一直断断续续在做。器官移植的第一个高潮在李永辉看来是70年代,而高潮的标志应该是1977年,当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林言箴等完成了首例原位肝移植,这一事件被称为是“自日本60年代进行两例肝移植后,亚洲地区肝移植项目的重新启动”。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说,中国开展器官移植的时间,相比国外晚了十多年,基础较差,手术效果也比较差。以肝移植为例,第一例手术在70年代末,而1983年美国健康卫生院已经把肝移植确认为治疗肝病的有效手段。 在李永辉的印象中,70年代中国的器官移植总体状况是做得零零星星,但当时由于国内免疫抑制剂类的药物很少,在用量上掌握得不好,而且免疫抑制剂当时也有很大的副作用,这些因素使第一个高潮很快地结束。 1981年是另一个需要记住的年份,一方面从1977年及其后不到5年的时间里,统计表明全国共有19个单位完成肝移植54例,后来证实,这54例中存活半年以上仅有6例,存活最长的一例活了264天,死于肝癌复发。 在此期间,肝移植基础研究和临床实践十分活跃,器官移植登记处在1981年成立,成立后相当活跃,“其在报道国内器官移植动态、促进交流、互通情报、协调工作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由于各种原因,这样繁荣的景象很快就过去了,有说法说,肝移植工作在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的高潮过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随后,1985年武汉国际器官移植学术会议召开,全体中国代表发出了“关于急需解决器官移植工作中供体来源问题”的呼吁,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快车道 李永辉对比器官移植在我国80年代出现的高潮和90年代出现的高潮说:“80年代相继有一些单位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去做器官移植,也相继做出了几个有名气的移植案例,而进入90年代,普及的速度很快,而且这个高潮来了就一直没下来。” 以肝移植为例,1995年因“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暨全国中青年优秀论文评奖会议”召开,使得已经停滞10年之久的肝移植重新起步。这其中有海归们——一批致力于肝移植的留学回国的中青年学者推动,技术壁垒的突破是重要原因。有学者说,“这一阶段,肝移植技术明显提高,效果明显改善,累计总例次、长期存活病例和肝移植中心分布等都有了新突破”。 李永辉总结说,在90年代,器官移植进入了稳定、快速的发展期。以尸体器官移植为主是我国的特点,活体器官移植占我国移植总量不及1%。 如果用进入快车道形容这期间中国的器官移植概貌,肾移植有相当的代表性。自1989年以来,每年施行肾移植在1000例以上,到1994年底就累计13594例次。李永辉说,在技术不成为主要障碍之后,门槛是经济的门槛。 我国乃至亚洲存活时间最长的“换心人”杨玉民本来是个农民,以开杀猪作坊谋生,能够成为接受心脏移植者,他的经济背景不容忽视。有报道说,在1989年患上那场使他致命的心肌病的高烧前,他已经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万元户了。 不过因为他的特殊性,更确切地说,因为心脏移植当时的特殊意义,“医院考虑他的经济困难,决定免去约12万元的手术费”。 夏求明细算起来从杨玉民这一例心脏移植到现在,12年中他所在的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总共做的病例有20多个。数量这样少,除了在世界器官移植界普遍存在的、十分严重的同种心脏移植供心短缺问题,“费用是很大的一块”。这里的费用不仅包括住院费、手术费、还有长期服用抗排斥反应药物,定期接受检查和治疗的费用。 以肾移植为例,有人估算健康供体的手术及住院费用大约在两万到四五万元之间,而在我国健康供体的手术及住院费用不能用医保报销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肾移植成功率非常高的亲属间的捐肾行为。再有一笔账是尿毒症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血液透析和肾脏移植,有人估算前者每月的花费在5000元左右,后者术后的药物维持费用约为3000元。 肾移植是我国临床开展最早、例数最多也是技术最成熟的大器官移植。这些限定词在最后归纳则是必然的结果:普及,因而肾移植的费用在器官移植中已经算是进入门槛较低的。 有统计数字说,在2001年我国已经登记的106个单位共施行肾移植5561例,年移植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开展的医院和移植例数都在逐年增加,而年度移植数超过100例的医院有18个。在枯燥的数字背后,一个陡升的曲线既表明技术的改进,也表明经济因素在里面起到的作用。 夏求明说,在学术界不承认器官移植有“市场”的问题,以心脏移植为例,心脏移植到目前还只是一个研究课题,每年4%的死亡率也是一个客观现实。但同时他也承认,“随着医学发展,心、肾等大器官移植在技巧上基本不存在什么问题,已经成为常规的治疗手段。心脏移植作为外科手术,切开、止血、缝合等真正的手术时间只需几十分钟”。技术门槛的降低使得一些单位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变成了经济效益。 他说:“每种治疗手段都有适应症,做心脏移植手术的规定是,判定患者自然存活时间不到一年。”而在现实中,随着现代社会冠心病等心脏病的大量增多,这种规定被执行的尺度也开始受到质疑。 关于“准入” 黄洁夫将目前器官移植领域存在的混乱定义为:无序竞争状态。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将在中国推行准入制度理解为“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他说,“我对中国现在器官移植现状的概括是:起步较晚、治疗不规范、发展不平衡、一哄而起”。 郑虹举例说,有很多方面都显示我国目前器官移植与国际的接轨还处在摸索阶段:有些单位甚至是为了做移植而做移植,现在不少没有条件的单位也在上移植手术——山东一个小县城的医院甚至也敢接移植手术,自己没有人员,从我们这里借医生去做手术,病人术后的药物治疗方面,很专业也很重要,但有很多医院并不具备这样的专业素质和实力。 从制度层面上,黄洁夫说这是一种形式主义,也与现行制度有关。比如,一家医院要通过三甲医院考核,其中一个硬指标就是必须完成5例以上器官移植,这就导致一些医院为了达标不择手段,从外面请专家带着病人到本医院做手术。“没有本医院医生参与,也没有自身技术,这实际上是一种弄虚作假行为。卫生部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不久将会取消医院升入三甲与器官移植挂钩的规定。”黄洁夫说。 黄洁夫曾在去年11月在上海透露说,有关器官移植立法的指导方针、立法原则等都已经基本确定,对器官移植的规范化管理和建立技术准入制度,将促进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走上与国际接轨的良性、健康发展道路。 《器官移植准入条例》制定早在2002年就已经进入状态。夏求明说接到卫生部关于器官移植准入条例起草的通知,“全国的心、肾、肝等器官移植的各方面各组织一帮人,给卫生部提供一个可操作的准入标准”。夏求明等人负责起草的是心脏移植部分。他告诉记者,现在做心脏大循环手术的医生几乎就可以做心脏移植手术,因为手术方法已经规范化,因此他的意见是,准入的一个原则是临床医生不能随便参与器官移植,而要有专门化专业化的背景。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实施器官移植也应该是一个团队的专门化工作,而不是请个人来就做了。也就是从医生的资格、医院的资格等方方面面去限制。 同时夏求明说,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不能参与脑死亡的判定,脑死亡的判定由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器官移植准入条例》特别限定器官不允许买卖,更不允许偷盗。 上述几点也是国际上的一些通行做法。郑虹说,引入准入制度非常必要,从国外的发展来看,也是一种必然。在欧美、日本等移植技术发展得比较完备的国家,以前移植技术最初发展的时候,这些国家里也只有少数的医疗机构可以开展移植手术,对医院的要求同样非常严格,只是到后来技术越来越成熟,相关的研究越来越专业,成功率也逐步提高之后,才普及开来。比如日本,最早只有两家医院具备移植手术资格,现在发展到每个县都可以做。所以,中国引入准入制度,对于移植技术在中国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并不能简单地看做是要提高门槛形成垄断。 夏求明说,从2002年到2004年的两年间,专家们讨论过多次,从分组讨论扩展到伦理、法律等方面,最后他说,当这个制度由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制订出来后,将具有“红头文件”的约束力。记者◎金 焱 王鸿谅 相关专题:三联生活周刊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三联生活周刊专题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