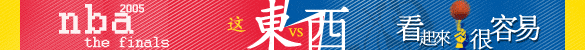路上小坑已被填平 抓拍记者谈心路历程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14日16:44 东南快报 | ||||||||
 “拼命”的摄影记者柳涛  见报当日路上大坑被填平 2005年5月9日下午,一名骑车人冒雨经过厦门市厦禾路与凤屿路交叉路段时,因自行车前轮突然陷入一个水坑,身体失去平衡摔倒。 本报摄影记者柳涛用他的镜头纪录了摔跤全过程,本报第二天刊发了照片。随后,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北京青年报、东方卫视以及新浪网纷纷就这组照片展开讨论。一场关于“职业道德”和“记者良心”的争论几乎将柳涛淹没。
在本报的休息室里,柳涛关上了大门,向记者阐述了拍这组照片的经过以及这几天艰苦的心路历程。 “没看清他怎么摔 更别说看取景框” 5月9日下午2点半左右,我没有任务,按照习惯,我背着照相机包出去搜街。 那天下着小雨,天色很暗。我预感会有大雨,而大雨天通常容易出新闻。我希望能够拍几张照片,体现这场大雨给市民带来的影响。于是我沿着厦门凤屿路向人员集中的火车站走去。 快走到凤屿路口时,风突然大了,伞被吹得翻转过来,大雨随后而至。我忽然想起了99年的那场台风。可能会出大新闻,我当时想。 匆匆拍了几张雨景后,雨实在太大,我浑身被打湿,镜头也有些水花,不得已跑到路口的银河酒店门口避雨。当时,在酒店门口避雨的大约有20多人。 一名市民见我挎着照相机包,就说:“你是记者吧?这路口有一个坑,经常害人摔倒,你们可以报道一下。”他的话提醒了我。 我选了一个位置,给相机换上80-200的长焦镜头,镜头上光后,我发现角度很小,电话亭、树和过往的车经常会挡住视线。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坑到底在什么位置,小镜头可能捕捉不到。 于是,我又换了一个离路口更近的位置,同时把长焦镜头换成12-24的镜头,这样角度比较大,容易捕捉需要的信息。然后又把相机设置成连拍。 行人一个一个从眼前经过,我都用镜头留住,但是没有一个人摔倒。我开始怀疑这个路口是否真的有坑,足以让路人摔倒,我也怀疑自己今天能不能拍得到。 大约1个小时过去了,我有些灰心。我把相机挂在脖子上,一手扶着相机,一手按在快门键上。 一个戴白色帽子、打着伞的人骑自行车从眼前经过,突然听到“哗”的一声,我下意识把镜头对准那人,右手按下了快门。 我没看清他是怎么摔倒的,更别说盯着取景镜头抢拍。等我回过神来,那个人已经慢慢爬起,他的车没坏,人也没受伤,朝我望了一眼,就走了。 有些网友说我没有人性,见死不救。事实上,如果那个人有生命危险,我肯定先救人而不是拍照。 随后我查看自己刚拍的照片,连自己都被镇住了,那个人不是预料中的从侧面倒下,而是向前倾,这种冲击力效果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当时非常兴奋,知道自己拍到了一张难得的好照片。 兴奋之余,我突然回过神来,我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我在附近找了一根约2米长、10厘米粗的棍子,想立在坑内警醒路人,结果木棍无法立稳。经路人提醒,我在附近工地上找了一个修路的提示牌放在路口,这才挎着相机回到报社。 第二天,雨停了。我觉得有必要做跟踪报道,于是又来到路口,发现那样的小坑还有三四个,幸好已经被人填平了。跟踪报道没有必要了,我心里有些安慰。 “我是一个记录者而不是旁观者” 9日回到报社后,我没吱声,就把图片交给了编辑。 由于我同时是新华社签约摄影师,晚上8点左右,我又把那组照片发给了新华社。新华社随后打电话给我,核实情况后告诉我,这组图片不错,新华社将发通稿。 我以为这跟平时的通稿一样,当时没在意。 10日早上去报社上班,一名同事笑着对我说:“柳涛,这下你出名了。”我愣了一下,同事打开网页让我看。 网页上显示的是关于我那组图片的议论,基本上是骂声一片。但我并不气愤,只是觉得很委屈,毕竟没几个人了解我们摄影记者。 当天下午5点左右,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求采访。这时,我才感到事情闹大了,好不容易有些平静的心情又波动起来。我还是向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复述了当天的经过。 之后,我因为这组照片“出名”了。媒体一拨拨找上门来。 5月11日下午,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栏目组电话联系了我,随后又是东方卫视。 5月12日上午,福建电视台找到我,随后央视另外一个栏目组找到了我(实在记不清楚了,头脑太混乱了)。下午,央视的《社会纪录》栏目组,厦广音乐台又找上来了。 我是一名记者,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而身在这个漩涡中,不要说别人,我自己也非常难受,这些天,我每天都要到凌晨4点才睡得着。 网上的骂声、赞扬声我都能够理解,但他们大多数人不了解一个记者的苦衷。同行的记者,包括北京青年报、《中国周刊》等媒体的记者纷纷打电话安慰我,并表示支持。新华社的工作人员还特意打电话安慰,表示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我想风波快点过去,我对这些记者这些媒体重复了对北青记者说的话。记者 柳涛/口述 冯逵/记录 “拼命”的摄影记者柳涛 柳涛迟早会出好作品,因为他干活很拼命。这是我跟一些同事在讨论摄影记者的时候得出的结论,但没想到,他的好作品会让他如此痛苦。 柳涛最欣赏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拍的图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的不够近。所以柳涛总是愿意冲在最前面,即便是面对火灾、车祸等危险的事情。 柳涛自己也说,如果没有任务,为了搜街找图片,他每天要走数十公里的路。从报社到火车站,再到金榜公园,然后转到白鹭洲公园,最后经过南湖公园回到报社。这条路线是他经常走的,当然还有更远的到轮渡,到会展中心。 没有几个记者跟他一样,会为了拍一个专题,连续几天半夜爬起来跟着清洁队跑;而在我们做厦门无居民海岛专题报道的时候,他经常自己掏钱租船上岛。有时候对图片不满意,即使天黑了,他还会租船,再上岛一趟。 有人说,已经30出头的柳涛,需要成家,成家需要钱,所以他干活很拼命,他是为了钱。一个人拼命工作究竟为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柳涛潜心钻研的精神确实让我们叹服。他会经常琢磨从哪个角度拍效果会更好;他也经常拿着自己拍的像片跟其他优秀摄影记者拍的对比,找出不足。 所以,尽管柳涛已经干摄影那么久了,但他的作品仍然不拘泥于一种风格,依然变化多端。在这个行业中,他几乎从来没有摆拍过。 关于柳涛,通俗一点说,他是拼命;说得雅一点,就是敬业。 一个经常和柳涛合作的同事/文 我还想说,如果仍碰到类似的事情,如果不会危及到拍摄对象的生命,我仍然会用我的镜头真实地记录一切。我是一个记录者而不是旁观者。 错就错在他是一个记者 当摄影记者柳涛处在这个漩涡中的时候,笔者的头脑中一直闪烁着一个名字:凯文·卡特———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得主。 11年前,南非“自由记者”凯文·卡特以一张《饥饿的小女孩》获得1994年普利策新闻特写摄影奖。3个月后,即1994年7月27日夜里,警察在南非东北部城市约翰内斯堡发现了凯文·卡特的尸体,他用一氧化碳自杀身亡。 据媒体报道,在凯文·卡特自杀身亡的前三个月中,他本人一直处于冲突的痛苦之中。当时,人们纷纷质问,身在现场的凯文·卡特为什么不去救那个小女孩一把?!就连凯文·卡特的朋友也指责说,他当时应当放下摄影机去帮助小女孩。 死者已矣!笔者面前的柳涛形容憔悴,手机响个不停,却不能关机好好清静一下。 幸好这次还只是一个跟斗,与人命无关。否则,即使上升到法律程序也未必不可能。中国人似乎习惯用情绪表达,用道德说教。 柳涛错就错在他是一个记者。一个凯文·卡特能够救下非洲那么多贫困的小女孩吗?同样,一个柳涛能够填好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那么多坑吗? 柳涛的确够残忍,拍下了一个真实的瞬间。但是,诸位可知道,真实本来就很残忍,否则人们也不会用喜剧去麻痹自己? 柳涛的确不够诚实,面对媒体,他对真相做了筛选。但是,诸位可知道,他也是一个人,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残忍的时候,难道他希望往自己的伤口再撒一把盐吗? 错就错在他是一个记者。因为记者是被特殊划定的人群,肩负了不一样的东西。他不去参与抢救,并非因为道德缺陷,而是因为总需要有人去做记录的事情,就像过去的史官,只负责记录,不负责纠正主公做错的事。 记录下来的东西,虽然有时候也是为了钱,虽然有时候记录的代价很大却仍然难以得见天日。但记录还是有必要的,因为它毕竟是把真相反映给公众的唯一渠道。如果没有记录,可能一些东西被遗忘了,永远得不到关注。就如那个小女孩,凯文·卡特可以救她一次,那么以后,当记者不在场的时候,谁去救他? 柳涛被放在了口诛笔伐的最前端,而更多的旁观者呢?也许更有甚者会搬张凳子,跷起二郎腿专门等着看笑话。一个柳涛让他们颜面得以保存,甚至,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再对柳记者鞭挞一番。 同样庆幸的是,柳涛是一个记者,不仅因为他记录了一个真实的瞬间,还因为他终于战胜心魔,走在舆论的最前端,把全部真实展现在大众面前。 等待他的也许是更猛烈的风暴,但是他走出了一步,他不仅是一个摄影记者,也是一个男人。 小黑/文
相关专题:记者抓拍骑车人雨中摔跤引发争议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记者抓拍骑车人雨中摔跤引发争议专题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