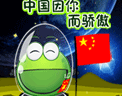巴金在成都编辑的杂志被查封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14:39 成都晚报 | |||||||||
|
巴金是一个对政治缺乏“敏感”的书生。1948至1949年初,当解放战争的炮声已经震耳欲聋,他依然在唱着 他那“诅咒旧时代”的老调,埋头而尽心尽职地做他的文艺杂志编辑。 巴金供职的《半月》杂志,是四川新文化运动中第一家被查封的刊物
1921年(民国十年)2月,17岁的巴金看到成都《半月》刊第14号上登载的《适社的旨趣和大纲》后,很感 兴趣,写信给《半月》编辑部要求加入。3天后,编辑来访,说明适社在重庆;此后巴金便参与《半月》刊的工作。在同年四 月,巴金用“芾甘”的笔名,在《半月》刊第17号发表了题为《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是巴金目前所见公开发 表的第一篇文章。1921年5月15日,巴金在成都《半月》杂志发表了《世界语之特点》的文章,并加入该社并成为编辑 之一。他与杂志的编辑同仁先后举办了世界语星期班和暑期速成班,在成都播下了世界语火种。同年的五月,他还参加纪念“ 五一”活动,第一次上街散发鼓吹“社会革命”的传单。并参加组织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秘密团体“均社”,发表《均社宣 言》。他们办刊物、通讯、散传单、印书、开秘密会议。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 在《半月》工作期间,巴金自己常常在上面发表文章。在很短的时间内,《半月》发展成了一个研究和传播新文化的 阵地。7月,当时四川军阀刘存厚把持下的、代表封建势力的警厅发布一条荒谬告示:《严禁妇女再剪发》,将妇女剪发视为 洪水猛兽,告示颁布即遭到进步人士的批判和抵制,《半月》杂志第24号于7月15日出版,他们对警厅告示首先发难,刊 登了《女子剪发与警厅》《禁止女子剪发的谬误》等文章,句句在理地批驳了警厅的告示。殊不知这惹恼了反动军阀,居然以 反对禁止剪发的罪状查封了《半月》杂志。据史料记载,这是四川在新文化运动中第一家被查封的刊物。不畏强暴的《半月》 同仁继而办起了《警群》月刊,继续发表驳斥警厅倒行逆施的文章,后来亦被查封了。 事实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个勤奋的“作家”和态度诚恳负责的“编辑”的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厚厚的大书中 的 巴金是一个对政治缺乏“敏感”的书生。1948至1949年初,当解放战争的炮声已经震耳欲聋,他依然在唱着 他那“诅咒旧时代”的老调,埋头而尽心尽职地做他的文艺杂志编辑。因此,他关注的“社会现实”是:“小孩子在哭,中年 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论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序跋集》)影响他此时 思想判断的是“寒夜”式“眼光”,“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 两天来收路尸一百多具’的标题”;(《〈寒夜〉再版后记》)而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国革命党人和法国民主知 识分子反抗王权与争取个性自由的思想传统。1948年前后的上海,为读者摄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杂志编辑和校对工作时 的“身影”。他留在历史键盘上的“声音”,也是巴金所独有的,带有巴金式的姿态和气味:1948年4月29日,他在致 一位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上海很少有书店愿意接印新稿(要是长篇,赵家壁还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书,难有赚钱希望 。肯出适当价钱买版税的,可说是没有。”当年5月5日,致沙汀书说:“您问起去年二月以后您的版税结过没有,这事情我 已打电话到书店去查问过了。据说您的书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税是旧版书的最后一次版税。《淘金记》《还乡记》都是去 年年底重印的。书店会计部另有回信寄给您。” 7月25日,致信范泉说:“据寄上,请查收。原稿收到,谢谢。要是方便,请您再寄一本刊载《惩戒室》的那期《 文艺春秋》。”8月14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税这期有四十多万,已嘱书店通知重庆分店转汇。”10月26日,又告 诉敬之:“我已与会计科讲好,预支版税五十万元,由渝转来,今天同时寄一信给济生,请他照办。”12月21日,对来约 稿的《文艺春秋》杂志主编范泉“诉苦”道:“近日仍忙着看校样,新春随笔之类无法写,请原谅。稿费当于见面时奉还。” 12月29日,接着告知敬之:“版税已嘱书店早汇,大概仍由重庆分店划付,不过书店办事难免不拖几天。”再查巴金1949 年6月至8月的书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编辑”“写作”与“人事”方面的苦恼。如6月10日致作家田一文书:“我一直 忙,《安娜》也有几十页待OK。房子问题弄得我头痛。我实在无法写信给你。”又如8月29日致友人书:“我去北平前几 天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应回沪后办交代。现在是康嗣群做总经理,朱洗做董事长。我无权请 你回来了。”……“敬之”是此时作家沙汀在四川安县家乡隐居时的化名,他当时就用岳母黄敬之的名字与人通信,包括向巴 金催要版税。 纵观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难免给人“世俗”的、同时也非常真实的印象。那场决定着民族生死命运和前途 的战争,对巴金好像没有太大的触动。当上海已经“城破”,浓厚、刺鼻的硝烟还在街道上到处弥漫时,他关心的却是文学作 品的出版问题,是“版税”“写稿”“人事纠纷”和其他一些看似琐碎的编辑业务。然而,它们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1948 年前后的巴金,仍然是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事实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个勤奋的“作家”和态度诚恳负责的“编辑”的 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厚厚的大书中的。这是他给自己、也是历史给予他的“定位”——只不过在50至70年代暂时“ 偏离”了一段时间而已。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关心的仍然是:就这时巴金真实的心态和处境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是 怎样安排与筹划自己的文化命运的?而这种“安排”与“筹划”,他对现实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对一代作家未来的命运究竟会 意味着什么?巴金是自觉地投入大革命的怀抱,真心诚意地选择了历史的吗?如果不是,那它又显示了怎样一种思想命题?这 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 (节选自《巴金书信集》)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巴金逝世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