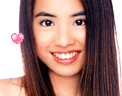走向全民医保的制度选择:公费医疗制还是社保制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16日10:49 南方新闻网 | |||||||||
|
顾昕 医疗负担已经成为民众反映较大的意见之一,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公平地说,各级政府对此并非无动于衷,而是绞尽脑汁想办法解决“看病贵”的难题。可是,尽管政府招数频发,例如控制药品价格、兴办“平价医院”、治理整顿医院乱收费等等,但总是治标不治本。问题在于,这些招数全招呼在医疗服务的供给方,但是对于其需求方,也就是医疗保障体
实际上,就医疗体制改革问题,政府的最大职责之一应该是推动建立一个普遍覆盖的医疗保障体系,也就是“全民医疗保障”,简称“全民医保”。这一工作的重要性,首先在于能极大地促进医疗负担公平性,同时更为重要而且也更为现实的是,全民医保还能收到抑制医疗费用快速上涨之功效。换言之,全民医保正是医治“看病贵”、“看病难”的妙药。 这其中的道理很清楚。姑且不提那些带有坑蒙拐骗等违法行为的天价医疗案,既使是正常合理的医疗费用,如果让病人在短时间内筹措,在很多情况下一如大山般沉重。一旦所有的民众都获得了医疗保障,那么医疗费用不仅可以在健康人群和病患之间分摊,而且是在人民健康与生病时段分摊,从而可以避免我们目前大部分医疗费用均由病人在生病期间负担的局面;一旦所有的民众都获得了医疗保障,低收入者自然不会因为费用问题而对医疗服务(尤其是门诊服务)望而却步;一旦所有的民众都获得了医疗保障,那么医保组织者就可以成为医疗服务的购买者,成为民众的代理人,民众也就不必作为单个病人出现在医疗服务点听凭医生们摆布。如此一来,医疗服务买卖双方市场力量对比便可以从卖方向买方倾斜,医疗服务提供方(无论市场化与否)都不能为所欲为地多收费、多开药、多检查。 可以说,对于缓解中国医疗体制所面临的两大难题,即费用高涨、公平欠佳,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具有一石二鸟之效。毫无疑问,建立一个全民医疗保障体系,乃是中国实现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全民医保的重要性不必多言,问题是我们能否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少决策者看到“全民医保”这一字眼时往往会暗中叫苦,因为他们担心财政不荷重负。因此,要回答我们能否实现“全民医保”这一目标,首先必须要对中国城乡目前的医疗总开支心中有数,同时也要对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的总盘子心中有数。其次,我们必须对全民医保的制度安排进行战略选择,因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对医疗费用的分摊方式不同,从而对于政府财政造成的压力也不同。 中国城乡的医疗总开支 除了会计师,算账的事情总是令人头痛,但大体算一下粗账足以令我们了解事情的原委。要搞清楚目前中国城乡的医疗总开支,理论上应该把所有医疗开支加总。具体而言,开支的大头有如下几项:1)城乡居民个人医疗开支;2)公费医疗开支;3)城市基本医疗保险开支;4)农村合作医疗开支;5)城乡商业性医疗保险理赔开支。由于后两项数据尚缺,况且其覆盖面比较窄,因此我们可以暂且忽略不计。我们以统计数据较为齐全的2003年为例,对城乡医疗支出总额进行了匡算 (框图-1)。总体来说,城乡民众用于看病花费了4308.8亿元,而当年政府财政开支总额为24649.9亿元。 如果建立了全民医保,那些原来因没有任何医保而尽量不去看病或住院的人们显然会改变行为,因此医疗费用有可能会提高。但是,全民医保的建立意味着医保机构拥有了更大的医疗服务购买力,从而面对医疗服务提供者时具有了更大的市场谈判力量,因此可以设法降低医疗费用。具体的变化情况,我们无从预测,但可以假定实现全民医保后,目前的医疗费用总额不变。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选择何种制度,对大约4000多亿的费用进行分摊。 走向全民医保的制度选择 医疗保障制度有多种选择。无论是从历史还是比较的角度来看,人类所能发明的医疗保障制度无非是图-1所展示的 7种模式。下边的两种模式均基于自愿原则、由民间组织提供医疗保障,保障者要么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要么是非营利性社区组织。上边的5种模式均有国家介入,其中仅有“自愿保险”一种坚持自愿性原则,其他均实施强制。 无论是卫生政策理论还是人类历史上的实践经验都证明,如果坚持自愿性原则,那么要想实现全民医保简直是难于上青天。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发达经济体中惟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其原因正在于美国坚持以自愿性商业保险为其医保的主干。在自愿性基础上兴办医疗保险,哪怕国家给予保费补贴,总是会有一些人愿意赌一把,不愿意参保。类似的情形在我国农村正在试点之中的新型合作医疗中屡见不鲜。最初参保的民众如果一年内身体健康而没去看病,不少人就会因为感觉不划算而来年不愿意继续参保。 这意味着,医疗保障不能依赖于自愿性医疗保险(无论是否商业化),国家运用其合法的强制性乃是建立全民医保的一个必要条件。医疗救助制度仅仅覆盖低收入者,可以成为医保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无法成为全民医保的主干。个人账户制度仅仅做到了人们的医疗费用在健康时段与生病时段分摊,缺乏在健康人群与病患之间分摊的机制,无论在风险分摊还是在社会共济方面都不能令人满意。 因此,政府要推动全民医保,在基本的制度架构上,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公费医疗模式,即政府直接从国家税收中为民众的医疗服务埋单;二是实行强制性医疗保险,也就是社会医疗保险,让民众个人、工作单位和政府都出一点钱,共同分担医疗费用。在世界上,凡是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只有这两个招数。 公费医疗制还是社会保险制? 究竟公费医疗制好,还是社会保险制好,理论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世界各国的实践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实际上是各有利弊,优劣难分。公费医疗体制对于国人来说并不谋生,也令很多人向往。它的好处,尤其是公平性,自不待言;但是,这一模式主要的问题是医疗筹资几乎完全来自国家,对财政的压力较大,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或者企业身上。 那么,建立全民公费医疗体制究竟需要多大的国家预算呢?根据框图-1的匡算,政府为了满足民众现有的医疗服务需求,如果设定20%的高自付率,公费医疗的开支仍然需要3447.0亿元(4308.8 ×80%),大约是当年财政卫生总开支的3倍,财政总支出的1/8。事实上,现行卫生财政支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医学科技的研究与发展等等,并非全部用于看病。由此可见,在现有财政体制以及现有财力的约束下,全民公费医疗方案似乎不大可行。 另外一种选择是国家继续扮演保险者的角色,在现行制度架构中通过制度调整实现全民医保。目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主干,在城市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而在农村是新型合作医疗。问题在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医疗保障的普遍覆盖还远没有实现。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显示,65%的城乡居民(其中44.8%的城市居民和79.0%的农村居民)完全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都是医疗保险,只不过前者是强制性的,属于社会医疗保险,而后者是自愿性的,属于一种准社会医疗保险。 就城市而言,实现全民医保并不困难,无非是现有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具体措施是:1)城市所有用人单位的所有从业人员(当然包括农民工),一视同仁地全部纳入医保体系;2)参保人可以为其家庭中没有工作的成员投保; 3)政府通过医疗救助制度支持贫困家庭投保。 第一条具体措施就是现行的政策。实际上,一部分城市已经开始把灵活就业人员,主要是个体经济工作者,纳入到医保体系之中;农民工参保的障碍也不大。因此,就这一条而言,关键是落实。 第二条具体措施是新的制度安排,旨在弥补现有制度中仅以从业人员为单位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保的缺陷。究竟是通过工作单位强制从业人员为其家庭受抚养人员(主要是未成年人)投保,还是通过教育系统(包括幼儿园)为这些人投保,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应该不难解决。根据框图-2中的匡算,在城市中,每一个从业人员仅仅负担不到1人,因此即便在不增加用人单位负担的情况下,让从业人员个人全部负担受抚养者的医疗保险缴费,应该也不会遭遇多大阻力。平均而言,每一位从业人员每年只需缴纳大约870元,全家就可以获得医疗保障。 第三条措施实际上也是国家的现行政策,正在一些地区进行试点。从医疗保障体系的管理角度来看,将医疗救助基金同医疗保险基金整合,有利于在各地区形成医疗服务的单一购买者。国际经验证明,医疗服务的单一购买者有利于费用控制。这样,主管医疗救助的民政部的主要职责可以放在其擅长的甄别困难人群,从而确定受益者对象上,而把基金支出管理和医疗服务购买的职责交给现有的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更有利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平稳运作。基于匡算,即便国家为所有城市低保人员投保,财政支出总额仅为147.6亿元,完全在国家财政的可承受能力之内。至于各级政府如何分摊医疗救助的费用,则是另外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公共财政问题。 就农村而言,实现全民医保最可行的措施是同城市一样,采纳社会医疗保险的模式,将现行新型合作医疗从自愿型改为强制型。如果设定20%的自付率,农村居民人均年缴纳保费40元,国家只需人均年补贴52.8元,那么国家财政只需要支付406.6亿,就可实现农村的全民医保(参见框图-4)。至于农民如何缴纳医疗保险费、费率究竟如何定、国家财政补贴如何在各级政府中分摊、中央政府如何补贴地方政府以实现“财政均等化”,都值得深入研究。其中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农民以何种费率缴费。很显然,如果每一位农村居民,不论其家庭收入高低,一律缴纳40元,固然可以节省行政成本,但无疑有违公平的原则。如何将农民医疗保险的缴费水平同其收入水平联系起来,是实现农村全民医保的最大挑战。 投资于医疗保障=投资于“社会性基础设施” 无论如何,在现有社会医疗保险的制度框架进行渐进式的改革,主要是通过现有政策的落实和完善,而不是进行伤筋动骨式的改革,就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全民医保。在社会保险的制度框架下,实现城乡一体化也没有什么制度性的障碍。城乡总计仅仅需要各级财政多支付大约554.2亿元(147.6+406.6),就可以达致目标。如果在此基础上就一些花费高、但得病概率低的病种发展补充性商业医疗保险,那么政府财政的开支增量会比这一匡算值还要低一些。 500多亿的财政投入增量多不多呢?实际上,2004年财政收入达到26356亿元,比上年增长4641亿元。2005年的财政收入数字还没有出来,但是保持2004年的增长速度从而使财政总收入突破30000亿元是毫无问题的。因此,我们大体上把财政收入增量中的1/9拨出来,就可以建立一个全民医保体系。 当然,收入增加再多,也总是有无穷多的花钱之处。政府究竟应不应该在财政总盘子中切出这么一块投资于医疗保障,完全取决于各级政府的施政战略。我们姑且把社会公平的考量放在一边,哪怕是从追求GDP成长的角度来思考,政府也绝对应该在医疗保障上加强投入的力度。有关数据显示,到2005年底,人民币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经突破14万亿元,创造了历史新高;但是,我国10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低接近20个百分点,而近5年来这一数字持续走低。人民富裕了却不敢消费,其中医疗负担之重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政府500亿元的医疗保障支出完全有可能在短期内促使14万亿元居民储蓄的一部分,哪怕是其中的5%转化为消费,就能有效地扩大内需,从而推进中国经济走向可持续性的发展。 从当代发展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来看,在医疗保障制度上投资绝非具有消费性,乃是一种“社会性投资”,具有极大的生产性。姑且不论医疗开支本身是内需的一部分,而医疗服务业乃是第三产业的重大支柱之一,因此投资于医疗保障可以直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我们从另一方面来考察。众所周知,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对于人力资本的增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民众不因无力负担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病,那么因病致贫的现象就可大大缓解,而疾病已经在2004年成为中国贫困发生的第一因素,而贫困发生率的降低便可直接促进我们经济的成长。因此,医疗保障,甚至更加广泛的社会保障,在国际上被称为“ 社会性基础设施”。在医疗保障体系上投资,其经济社会效益绝不亚于在“物质性基础设施”上的投资。 我们的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物质性基础设施”对于经济成长的重要性,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社会性基础设施 ”不仅对于社会公平,而且对于经济成长同样具有直接的影响。在财政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性基础设施”,似乎更愿意增加投入,以显示政绩,但是对于“社会性基础设施”,依然不够重视,这实在是深受过时经济学教科书影响下的短视行为。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有关政府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推进全民医保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已经提出了要在2010年至少实现城市全民医保的政策目标。这是中国走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一步,但是距离我们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还远远不够。把全民医保视为中国走向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战略制高点,已经正当其时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来源:南方周末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南方周末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