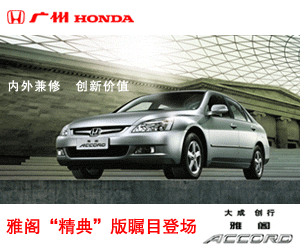|
|
|
|
|
三位学界名人的转折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29日18:47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他们的生活从安稳走向苦难,他们的精神从传统走向现实 “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1937年是个最具奇特色调的年份,知识分子的生活最具悲剧色彩,但也最能显现其生命 的韧性和高贵价值。”致力于“1937年中国知识界”研究的马嘶分析说,它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转折点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中国学人从安稳走向苦难的转折;另一方面又是他们从传统士大夫思想模式走向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新型知识阶 层的转折。 陈寅恪:一代大师的流亡 战乱使学人文士们失去了温馨的家园,成为迁徙逃亡的文化流民,饱尝现实的磨难与艰辛。在国学大师、史学大师陈 寅恪身上,最能体现中国学人从安稳走向苦难的转变。 1926年,年仅36岁的陈寅恪,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的 几年中,陈寅恪已被公认为大师级的学者。 那些年里,陈寅恪生活稳定,常常去好友吴宓家中畅叙,或一同出去散步闲谈。他们谈学问,谈诗,也谈时局。陈寅 恪当时的收入也颇为丰硕。1936年下半年,他的月薪已达480元,为清华教授中的高薪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津师生大举南迁。陈寅恪也于1937年11月初,打算携妻子、三个女儿逃离北平。 “平津亲日伪政权为阻挠文化界人士离开北平,在车站设卡,严格检查旅客行李。”马嘶说。陈寅恪扮做个生意人。 为了防止一家失散,他让孩子背熟了沿途及目的地有关地址和人名。孩子们牵着父母的衣角,总算通过了日本兵和中国警察的 检查,离开了北平。 在济南车站转车时,又遇到了人群骚乱,大家相互传言:日本鬼子要来了,快逃!人们见车就上,也不管班次和时间 ,车站混乱至极。幸好,一位友人已在车上,帮助陈寅恪一家一个个从窗口爬进去,又让给了他们三个座位。一路上,大人们 直挺挺地坐着,两个大孩子睡在地板上。这样,过了24个小时,才到徐州。又后经郑州、汉口,才到长沙。 从11月3日晨由北平出发,到11月20日晚抵达长沙,这一路,走了17天。 陈寅恪到长沙后,得知长沙临时大学已于11月19日开学。此时,长沙已临近战争前线,临时大学将西迁昆明,改 为西南联合大学。于是,陈寅恪又筹划着西行昆明。辗转多地,1937年末,陈寅恪抵达香港。在香港友人的帮助下,他安 顿了家眷后只身一人匆匆赶往云南蒙自的西南联合大学了。 家国沦丧,陈寅恪感到痛心。面对强敌,他恪守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1941年,日本占领香港,持日金40 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被陈寅恪严词拒绝。1942年春,日方请他到已被日军占领的上海讲课,他又一次拒命。 抗战胜利后,由于长期的颠簸与劳累,陈寅恪患上了严重的眼疾,双目失明已成定局。但他仍执教于清华园,继续从 事学术研究。 陈寅恪一生致力学术,即便在双目失明的晚年,仍不惮辛苦,编撰旧文,对于1937年遭遇的流离,一生都心有余 悸。 萧红:才女的苍凉离世 1939年,萧红应端木蕻良的邀请,去香港编辑《大时代丛书》。在战时香港杂乱的社会环境中,萧红的心境是抑 郁的。不过,她还是陆续写出了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以及剧本《民族魂——鲁迅》。 1941年春,史沫特莱归国途中路过香港,特地来看望萧红。此时,萧红正患着肺结核。这个病,在当时是不治之 症。在史沫特莱的帮助下,萧红住进了香港玛丽医院。但她已病入膏肓,不久,病情一天天加重起来。春夏之交,萧红回家养 病。此时,她已虚弱得寸步难行,多半时间躺在床上。 这一年,她发表了《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呐喊着:“东北流亡同胞,为了失去的地面上的痛心的一切的记忆 ,努力吧!” 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攻打香港,萧红被头顶上的隆隆的飞机声吓坏了。“身染重病的她,在战火连连中 感到失望、愤怒。”马嘶说。 这年圣诞节,香港沦陷。在沦陷的前两天,萧红旧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萧红知道自己再没有复原的可能,但她 又有着强烈的求生愿望,因为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马嘶讲述说,骆宾基去医院看望她时,萧红湿着眼睛低声说道:“这样 死,我不甘心……” 在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她转入玛丽医院时,萧红已经不能开口讲话了。而当时医院中所有的外籍医生都被扣留在日军 集中营里,其他医生和修女不是被抓,就是已经逃走。 就在萧红转院的第二天,玛丽医院被日军接管,在医院的大门口,挂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医院中的 所有病人都被迁走。这一天清晨6点左右,萧红就昏迷不醒了。 1942年1月22日,一代才女萧红病逝,年仅31岁。 闻一多:从自由学者变民主斗士 战争的阴云尚未笼罩清华园,校园里也还算得上静谧安详。黄昏将至,一个教室的灯亮了。闻一多走进教室,怀里抱 着一大撂线装书和稿本。他穿着黑色长袍,鼻梁上架着一副银边眼镜,好像古代的高士。 在讲台的椅子上坐下,闻一多慢条斯理地掏出一个烟盒,抽出一支烟,对着学生一笑:“哪位吸?”学生们默不作声 。闻一多擦着一根火柴,点上烟,吸一口,抑扬顿挫地开始讲课了:“士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可为真名士。” 1937年前,闻一多志在书斋里治学。早在1932年,他刚来到清华,就制定了一个庞大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 计划,决心在学术领域做出成绩。“然而,日寇侵华战争的爆发,使他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迁徙中 ,他对社会下层生活有了真切地了解。同时他本人的生活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马嘶认 为,这些为他日后从一个“自由学者”成为斗士,埋下了思想转变的种子。 闻一多是1937年7月19日携眷南下的。他走得很匆忙,只带了《三代古今文存》和《殷墟书契前编》两部书。 在火车站,他碰见了臧克家。臧克家问他:“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长叹一声:“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 破书算得了什么!” 几经辗转赶到长沙,又遇南京陷落,日军直逼武汉,长沙临时大学再也无法维持正常教学了,于是学校决定西迁昆明 。“当时,师生们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入滇。”马嘶说,“闻一多也在队中”。徒步旅行中,闻一多蓄起胡须,以明其 志。逢人问起,他调侃地称,要做个美髯公。 “经过了艰辛的逃亡、流浪,到了1940年前后,知识分子暂时有了落脚的地方,但由战争引发的物价飞涨和货币 贬值,使一向生活优越的他们一下子跌入了生活的低谷,变得贫困、清苦。”马嘶说,“他们的经济收入不仅难以养家糊口, 有的甚至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凄凉境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生活最为低下难堪的时期”。 闻一多支撑着一个8口之家,每天为吃饭发愁,妻子又经常患病,他每月的薪水,连最低的生活水准都难以为维持。 他有时候也写写文章,投投稿,但稿酬极低,根本不足以缓解紧张的家庭开支。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闻一多在朋友的劝说下,做起了刻章的营生。他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昏暗的灯光下刻章, 累得眼花,手腕手指酸痛,中指也磨出了大疙瘩。 “闻一多治印并不单纯为了挣钱,他有着极严的操守,有所为有所不为。”作家马嘶举例说,在他家庭生活最为困难 的时候,曾有人用优厚的稿酬,诱使他撰写违背自己意志的文章,他断然回绝了。美国一所大学邀请他去讲学,而且可以携带 家眷,也被他婉言谢绝了。此后,他仍每天拎着一个旧书袋,拄着手杖,步行20多里,到城里上课。下了课回家就埋头在用 几块本板搭成的书案上读书,备课,写作,刻章。 “而这时,也就快到了他长思7昼夜,拍案而起的时候了。”作家马嘶说。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 在昆明发售。书中,蒋称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深受五四影响的闻一多,被书中的“义和团精神”吓 了一跳。他说:“《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不久,他又读到了一些描写延安的文学作品, 对“那样的新社会秩序”充满向往。 “闻一多从一个‘自由学者’到‘民主斗士’的转变是迅猛而彻底的。”马嘶说。1944年,他加入民盟,从此全 身心地投入到民主运动的洪流中。1946年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他做了《最后一次演讲》,下午即被国 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