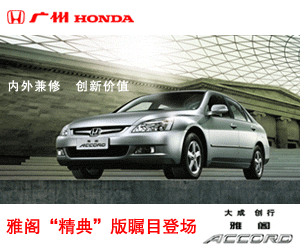|
|
|
|
|
一位北京平民的私人史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12日11:36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张鹭 一位建筑师用手绘出了上世纪的老北京,那些属于私人史的个人记忆为人们理解刚刚过去不久的历史提供了活证 建筑师关庚用手绘还原了北京城一个世纪的变迁,那些与他有关的私人记忆跃然纸上,一本名为《我的上世纪》的私人史在坊间悄然流传,已经消失的老北京“复活”了。 作为一名建筑师,关庚曾经参与北京东方广场、国家大剧院等工程的设计施工。2000年,他开始用签字笔和办公用纸,信手画下那些已经消逝的老北京的玩意儿。妹妹看到他画出的部分手稿,惊讶地说,“哎哟,你怎么连这些东西都记着呢”,并鼓励他继续画下去,“画好了给全家人看”。 就这样,关庚的回忆慢慢复苏并鲜活起来,跨越一个世纪的家庭生活与个人经历逐渐被还原出来。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利用上班时间早到的一个小时,画下了厚厚的三大本。其中的600余幅图画,配上500多篇短文,在2007年3月,以《我的上世纪》为名结集出版。此时,距离他初中时第一次看挪威漫画家古尔布兰生的私人绘本《童年与故乡》,已有半个世纪。 在关庚家中卧室的床头柜上,有一张1950年的北京市地图。泛黄的地图被装裱在玻璃木框里。三四年前他无意间买到这幅地图,没事的时候,他喜欢拿起来看看,寻找以前去过的那些地方,关庚觉得,这样“能回忆起一些事情来”。 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包办壁报的关庚,有着扎实的白描功底。1950年代,他还很年轻,那时候在十三陵水库劳动时,他也就开始在账本上记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四合院生活 2000年,关庚动手画下《我的上世纪》中的第一幅作品是有关“蜜供”的。当时他在一张报纸上看见“蜜供”的照片,突然间有了想画下来的冲动。“蜜供是祭祀祖先时最常用的供品,春节到来之前,要去饽饽铺订,完了就挑着送到家里来。”他的妻子还记得他们小时候,孩子们偷“蜜供”吃的情景,“冻柿子化了之后,给它嘬,吸干了之后就剩空壳,完了吹起来再码回去,大人一抓,就剩一层皮了”。 “蜜供”只是关庚幼年过的传统大家族生活的一个缩影。 1939年,满姓为“瓜尔加氏”的关庚出生在北京欢畅大院的一个满族家庭,从这个四合院的高处往东北方看,不远处就是朝阳门。这个传统的满族大家庭有10口人,还有使唤小子和老妈子侍侯。出生3个月后,关庚被过继给自己寡居多年的姑姑。从此,姑姑成了他的娘。娘带着他住在后院,呆呆(生父)和大舅妈(生母)住前院。每次吃奶时,娘都把他从前院的后窗递给大舅妈,吃完奶又给递回来。 满族人谨严的礼仪和家庭秩序在这里仍有体现。每年过年都得祭拜祖宗板子,一位祖先在战场上中的箭头,直到他出生的年代都还被当作神物祭拜。平时见面时,“男的得打谦儿,穿着花盆底鞋的女人就蹲安”。每天早上,女人们都必须到老太太(奶奶)房里请完安才能开始一天的生活。 这个令他魂牵梦萦的四合院有着复杂的布局——前院、后院、走廊、阁楼、可当冰箱用的井。30多平米的前院里,有参天的大树、清脆的鸟鸣、满院的花卉、假山和池子。“到了秋天的时候,各种虫都有。逮就能逮不少,就够玩的。我那时有个蛐蛐罐,老养着东西,不养蛐蛐了就逮个肉虫养着。”不但家里的孩子喜欢在院子里玩,他的同学也经常把这里当成玩耍的乐园。 到1970年从这里搬出为止,关庚在这个四合院里住了31年。他的童年、少年时代都在这里度过,甚至在迎娶妻子后,二人也仍住在四合院的后院里。关庚说,所有的画里,关于欢畅大院的几幅是他画得最细致的。 老北京 新北京 4岁那年的某一天,娘带着关庚走在瑞丰号门口。他手里拿着自己最爱吃的枣切糕,“拿着正要咬,突然间后面伸出一只手就给抢走了”。娘气得用满语朝抢食的乞丐骂了一句。让他对这件小事印象深刻的,不是被抢走的切糕,而是娘愤怒之中的骂声。那句老北京味道的骂声,加上卖日杂用品的瑞丰号,构成了他对北京生活最早的记忆。 再大一点,华北大学毕业的娘开始要求他背《三字经》,“一段一段的必须给它背下来”。但在大多数时候他还是快乐的,因为像套圈、捅彩、放风筝、抖空竹、竹蜻蜓、滚铁环、弹球、纸球、扇三角、挤狗屎、抓拐、跳房子,这些老北京孩子玩过的玩意儿和游戏,他都玩过。还有豌豆糕、冰桶、云豆饼、羊双肠、糖炒栗子、雷击疙瘩等零嘴。上小学时,他经常在东来顺楼下的大棚里吃面,上面浇上一层由唰羊肉下脚料做成的卤汁。关庚常常感叹现在的小孩的可怜,“现在的小孩,就是变形金刚什么的”。 尽管经过几次搬迁,但关庚的住所一直都在北京老城里头,尤其对东城区比较熟,一些老一点的地方“闭着眼睛都能找着”。其中位于王府井的平安电影院是他幼年时代看电影的地方,影院经理老赵是他父亲的朋友,曾带他看过几场电影,让他印象比较深的一部是由40年代著名女星李丽华主演的《血溅姊妹花》。 平安电影院改成中国儿童电影院后,他仍在里面看了不少电影。1994年建东方广场时,这家电影院由他之手被拆除——关庚当时担任东方广场的副总设计师。平安电影院的拆除让关庚伤感不已,他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影院里走来走去,试图寻找自己当年坐过的地方,关庚回忆说:“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因东方广场的建设同时被拆除的,还有老王府井新华书店。上小学时,关庚常和哥哥去那里买革命领袖的宣传画,这些画买来后被挂在他家东屋的墙上,一直保存到他1970年考上清华大学。老王府井新华书店被拆除时,关庚一晚上没回家,用录像机将整个爆破过程录了下来。 作为一名建筑师,关庚见证了许多北京老建筑的消失,这在他的绘本里也有所体现。位于朝外东大桥现朝阳医院东侧的空地,曾是侵华日军及家属的坟地;现在的工人体育馆和使馆区,过去是杂草丛生、塔像林立的和尚坟;老北京的建国门,其实只是一个豁口;现在的隆福大厦是隆福寺庙会的原址,关庚说:“那原来就是一个大庙门。”1993年,隆福大厦失火,他参与了重建过程。 私人史 大历史 1976年是关庚在《我的上世纪》中最为着重描绘的一年。 那一年的1月8日,周恩来逝世。当天下午,关庚在西单路口,站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目送了周恩来的灵车驶往八宝山。7月6日朱德逝世时,他蹬着三轮车送哥哥去火车站,走到北京饭店前正碰上出发的灵车。9月9日,关庚从广播里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一个月后的10月初,朋友来到他家,偷偷告诉他们“中央出事了”,结果在几天之后的10月6日,传来了“四人帮”倒台的消息。 无论是对于这个国家还是对于关庚,1976年都是一个拐点。在此之前,关庚目击过建国大游行时姐姐准备的五角星形大纱灯,体验过文革时免费旅游般的串联,也经历过下放劳动时扛钢筋的辛苦。而在这以后,关庚的生活逐步发生了转折。80年代初,他照着日本的服装书给同事的孩子裁剪喇叭裤,看完家具厂的展览后,也会给家里打些新潮的家具。喜欢看电视的关庚在70年代还只能在妻子教书的学校里蹭看那台14寸的电子管电视,而现在,他家的每个房间都摆着一台电视。 而这一切,在《我的上世纪》中都得到了栩栩如生的再现。 为《我的上世纪》担任特约编辑的萧盈在2006年3、4月间,定期到关庚家协助他对细节进行补充。萧盈认为:“这些图画和文字为我们理解那些刚过去不久的历史提供了活证。”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