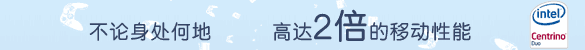|
|
|
|
|
朱大可:文坛是垃圾的工业化生产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6日18:15 财经时报
 朱大可:“父亲去世时,病床前就我跟我母亲,亲朋好友都逃得很远。” 访谈 文坛:垃圾的工业化生产 □本报记者 吴怀尧 《财经时报》:从图书销量上看,近几年80后作家异军突起,你如何看待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你读他们的作品吗? 朱大可:他们的书占有了巨大的市场份额,这是市场资本催化所带来的市场价值。人们可能觉得书卖得好,文学价值就高,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市场繁荣不等于文学繁荣。他们的作品有时我会看一下,文学性大多不足。新生代作家都面临一个严重的瓶颈,那就是如何完成市场价值向文学价值的转型,从市场英雄变成文学英雄。 近年我能够看到的这代人,李傻傻(《红X 》作者)是个例外,我想他可能是其中最有前途的小说家。韩寒,我欣赏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文化反叛的犀利立场。他是中国最优秀的博客写家之一。至于郭敬明,王朔已经有过很好的评判,我就不再多嘴了。 《财经时报》:在过去,抄袭是件非常可耻的事情,但今天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你怎么看待这种文坛以及学院论文造假的现象? 朱大可:这个是整个社会道德机制瘫痪的结果。国人的道德防火墙不仅没有更新,而且被卸载了。当然,腐朽的道德机制是应当被卸载的,尤其是对身体过多的禁锢。但道德自律的全面崩溃,却引发了另外的危机。 《财经时报》:你曾经说中国文学成就最高是先秦,相对于先秦文学,你怎样评价当代文学? 朱大可:当代文学,诗歌的成就最高,弱一些的是小说,散文最差。到今天为止,包括中学作文、甚至高考作文的题目,都受杨朔文体矫揉造作、奇酸无比、粉饰太平的风格的支配。这种散文后来被叫做“歌(功颂)德派”,是当代文学的历史性耻辱。一直到现在为止,各大学的校刊,中文系学生写的散文,还继续沉溺在“杨朔体”里。这是令人失望的事情,我认为散文的问题相当严重。 《财经时报》:你早期的文学评论几乎把“终极价值”视为最高甚至唯一的标准,并有浓重的基督教神学的价值取向。但你对“后朦胧诗”之后的诗歌评论很少。是不屑于评,还是阅读有限? 朱大可:那个时期大约是我去澳大利亚之前,也就是从1988年到1994年这段时间,大概有五六年左右吧,我进入了神学写作时期。写作的母题和核心价值,主要环绕基督教神学,而现在,我转入了新的阶段。中国诗歌总体上是退化的。80年代一度到过一个高点,90年代再次发生退化,整个中国文化都在退化,诗歌自然是小命难保啦!退到现在,好像已经所剩无几了。现在所谓的80后写作,根本就没有接过优秀的传统。他们的话语方式,继承的是50年代杨朔、秦牧之类、以及中学作文程式的传统,跟80年代的文学成就没有任何关系,这是我觉得特别可悲的一点。中国文化是断裂式的进化,每一次都回旋到原点,从零重新开始。你说这是悲剧吗?我看是的。 《财经时报》:你怎么看待当下的文学生态和现状? 朱大可:当下的文学生态,就像一个“工业化”的垃圾生产流程,跟用激素、化肥、杀虫剂弄出来的农作物一样。出版物很多,看起来琳琅满目,可以拿来吃,但却大多是问题食品。现在也丧失了基本的检验标准。文学的核心价值究竟在哪里?它人间蒸发了,完全不能支撑作家灵魂的内在超越,作家书写的目标只是基础价值,也就是市场和版税,而不是终极价值,甚至不是中间价值。中国文坛是空心化的,它已经荣升为一个庞大的垃圾厂。 《财经时报》:你在澳洲修过哲学博士,怎么看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区别? 朱大可: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的差别,而差别是被蓄意夸大的。简单地说吧,西方古典哲学以康德为代表,强调理性的价值,而中国哲学却是主张感性的,老庄都特别感性,孔子也是这样,这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本质区别。但是西方哲学后来在尼采那里发生了巨变,突然折回到了感性,用隐喻表达思想,包括以后的现象学。这是哲学内部的革命。但感性应当被限定在文化的范畴。亚里士多德开始的理性传统,是建构合乎人性的社会制度的支柱。 《财经时报》:诸子百家之后中国就没有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博士,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大可:我同意这个说法,后来出了很多哲学家,但都是阐释者,不是原创者。朱熹、王阳明、以及五四以来的几代文人,像熊十力和牟宗三,都是优秀的阐释者。我本人也是阐释者之一,如此而已。要超越先秦的高度?那是说笑了。 《财经时报》:中国作家有很浓的诺贝尔情结。你觉得诺奖是世界文学最高的荣誉和价值标准吗?中国作家离这个标准还有多远?高行健能代表汉语写作的真实水平吗? 朱大可:边缘国家都有强烈的诺贝尔情结,渴望被主流国家所认可。相对而言,所有奖项都有自己的缺陷,但诺奖还算是一个世界公认的重要奖项。当然它本身也在二流化,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评估。大师们正在离去,世界文坛已经变得空空荡荡。全球文学都面临萎缩的危机,这是因为新的媒体、新的娱乐和阅读方式,已经取代了文学。 高行健是个不错的作家,但他不能代表汉语写作的最高水平,这是一个文化隔膜造成的误解。中国大陆作家里,比他写得好的起码有20人,余华、苏童、北村都比他写得好。 《财经时报》:外国文学的翻译对当代文学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你认为现代汉语的发展与翻译家关系大不大? 朱大可:当然关系很大。汉语的现代化依赖的不是作家,恰恰是那些出色的翻译家,他们的贡献远远超出作家本身。中国作家的作品,只是他们的复制摹本,比如马尔克斯的汉译本,就是一个被无限模仿的范例。翻译家为80年代中国文学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成就,超过了作家本身。这些年出版了一千多种文学史,却没有一本提到这点,这要么是文学史编撰者的无知,要么就是他们害怕说出真相。我要再一次强调,如果没有这些优秀的翻译文本,中国文学的进化是无法想象的。 《财经时报》:于丹等人通过电视媒体走红的同时,也将大众的视线重新带到了传统文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这是否意味着国学的复兴? 朱大可:我看这不过是一种有限的文化复苏,还远远谈不上文艺复兴。前两年,新儒学曾经喧嚣一时,他们把孔子和儒家文化作为唯一的核心价值,排斥其他一切学派,这其实就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立场,跟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性解放,相距十万八千里。国学热还好点,它至少还承认有道家、墨家和佛教等多种文化形态的存在。对待孔子,应当以平常心来解读,把他当作一位有趣的老师和朋友,而不要像儒学家那样,把他捧到至圣的地位。 《财经时报》:文化和经济密不可分,冒昧问一下,你炒股吗?你怎么看待“全民炒股”的社会现象? 朱大可:我从不炒股。但这个问题倒是可以谈一谈。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炒股基本上就是一种赌博行为。由于没有建立可靠的宗教信仰体系,东亚居民成为全世界最好赌的群体,它不仅包括中国人,也包括韩国人、日本人和越南人等等。赌博的原理就是跟上帝、神和自己的命运博弈。没有信仰的人往往会更热衷于赌博。现在的这种股票投机的方式,很能迎合国民的赌博渴望。当然,赌博文化有着上万年历史,早就被基因化,成了一种“基因性行为”,长达半个世纪的无神论教育,强化了这种国民心理结构。跟那些炒股的朋友们相比,我不是赌徒。我在自己的信念里生活。我很早就洞察了我自己的命运。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