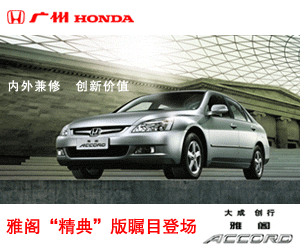|
|
|
|
|
杨德昌的“八部半”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9日17:58 新世纪周刊
-本刊记者/梅倩 “你自己看不到,所以我拍给你看。”他正是这样一位拍“看不到的东西”给观众的电影导演 戛纳电影节将2000年的最佳导演奖授予杨德昌,用以表彰他在电影《一一》中展现的才华。《一一》是杨德昌的 第八部作品,此时,距离他投身电影事业整整20年。 2007年6月29日,与结肠癌搏斗了7年的杨德昌在洛杉矶去世,享年60岁。年轻时代的杨德昌曾迷醉于意大 利导演费利尼的《8部半》,说自己“看了很多遍才明白其中的含义”,而他留给世界的电影作品也是“8部半”——从19 80年开始参与电影创作至今,在漫长的27年里,这位台湾新电影运动旗手留下了8部作品以及拍了一半的《追风》。 担任戛纳电影节主席30余年的吉尔·雅各布认为杨德昌“不仅拥有伟大艺术家的特质,他的电影更让亚洲电影成为 国际瞩目的焦点”,他是“戛纳电影节永远的朋友”。戛纳始终关注着杨德昌的创作,雅各布说:“我们从《牯岭街少年杀人 事件》、《青梅竹马》等电影中,发现他微妙的叙事方式,作品中充满丰富的人性与智慧,延续到在坎城影展获得最佳导演奖 的《一一》。” 在《一一》中,8岁的简洋洋总是拿着相机到处拍别人的后脑,他说:“你自己看不到,所以我拍给你看。”杨德昌 正是这样一位一直拍“看不到的东西”给观众看的电影导演。 旗手的成与败 1977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一次电影首映式上,德国新电影旗手赫尔佐格说:“我的第一部电影是用我当铁匠 存的钱拍成的。”当时三十而立的电脑硕士杨德昌备受鼓舞,他立即返回台湾,开始了他的电影旅程。 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正在经历经济上的起飞,新民歌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如火如荼,让许多向往电影的青年心中充 满热情和希望。回忆起那段时光,同为台湾新电影运动先锋人物的导演侯孝贤说:“杨德昌有块黑板,上面总写满了各种对电 影的想法,以及类似梦工厂那种未来打算为合作所取的名字,充满了对电影豪气万千的梦想。” 但那时,年轻人进入电影事业的机会并不多。无论是台湾当局的中央电影公司还是民营公司,都延续着手工业者模式 的师徒制。而台湾当局对于电影题材、拍摄方式的种种限制,使得电影工作者不得不“带着镣铐起舞”。反共宣传片、武侠片 和琼瑶式的爱情文艺片是大银幕的主流,而关注现实,表达青年一代对社会看法的影片既得不到当局的支持,也无法获得市场 的认同,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就曾遭遇上映3天便下画的尴尬。 直到1980年,杨德昌才第一次有机会接触电影创作,编写了《一九五○年的冬天》的剧本,两年之后,他迎来了 电影人生的转折点。 财政的亏空迫使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在新一代电影人身上寻找出路,于是便有了1982年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 张毅联合执导的《光阴的故事》。影片的四段故事包含着个人的成长、人际关系的疏离与台湾社会30年的变迁,它像一阵清 新的风吹皱了台湾电影的一潭死水,寄托着太多文化诉求与文艺理想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就此拉开了序幕。 1987年,包括杨德昌、侯孝贤在内的台湾、香港两地52名艺术家联合发表《1987年台湾电影宣言——给另 一种电影一个存在的空间》,将新电影定义为“一种有意识的创作活动”、“一种艺术形式”,“带着反省与历史感的民族文 化运动”。在这一年,台湾当局宣布改革电影工业现状,推行电影法案,新电影运动也完成了它的使命,成为台湾电影史上的 一个坐标。 然而,新电影运动并没能拯救台湾电影工业,5年期间新电影总共生产了58部,还不到那期间台湾电影总产量的1 4%,对台湾电影产业结构影响微乎其微。而1987年之后,新电影导演几乎全部停产,虽然杨德昌、侯孝贤继续坚持拍摄 文艺片,但他们却不得不面对一种尴尬,即在国际上能拿大奖,却赢不了国内市场。 前金马奖主席王晓祥表示:“不管是柏林、戛纳还是威尼斯,小众的东西在那里受到了肯定,也让他们非常爱惜自己 ,一味地拍小众。”王晓祥认为:“那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到了人们的背弃,因为题材不够开阔。”但他同时也说,“ 台湾电影萎缩的原因很多,也不能全部推到几个导演头上。” 握刀的知识分子 台湾金马奖主席、著名影评人焦雄屏在杨德昌去世后,接受台湾《联合晚报》采访时说:“杨德昌对台湾电影的影响 ,来自于突破了传统的本土电影语言,用西方的概念,呈现当代台湾社会、家庭与人文的状态,手法犀利,但充满人性关怀, 并提出醒思,无论是早期的《海滩的一天》,到后来《一一》都是。” 在新电影运动存在的5年里,杨德昌拍摄了《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和《恐怖分子》被统称为“台北三部曲” ,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关注都市题材,用冷静的手法揭破当代社会人际关系的风格已经逐步确立。他仿佛以摄影机为手 术刀,层层剖开现代都市人的人生困境。这是一项细致而烦琐的工作,需要勇气与责任,更需要一个知识分子的冷静、睿智与 坚守。 以“台北三部曲”为例,在《海滩的一天》中,不断寻求自我价值的都市女人,得到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落与冷漠 ,以及道德上的自责;在《青梅竹马》中,人们前行的步伐已跟不上都市的现代化的速度,人际关系的变化产生的斥力让“青 梅竹马”的恋人渐行渐远,传统的价值观被弃如敝屣;在《恐怖分子》中,家庭危机和事业危机让一个一贯以软弱忍让为宗旨 的男人以决绝的暴力方式展开了报复。 到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种“残酷”的风格发挥到极致。外界评论这部电影是以“令人震惊的 人性力量,给冰冷的现实社会以还击”。 这部电影取材于上世纪60年代少年杀人事件的真实案例,而杨德昌恰好与凶手是同校学生,于是这部影片成了杨德 昌最带有自传性质的写照。影片拍摄的背景与90年代初台湾青少年犯罪率的增长有关,但这并非单纯归咎于青少年肾上腺素 的分泌旺盛。杨德昌说:“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小明(影片中被杀的少女)自己都是凶手。” “儒者不惑” 从1994年到2000年,杨德昌的最后三部作品《独立时代》、《麻将》、《一一》构成了“新台北三部曲”。 在2000年戛纳电影节期间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他说:“我的电影谈善的,也谈恶的,因为这样才真实。”从这些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为敏锐、豁达,甚至温和的杨德昌。 被杨德昌自定义为“喜剧小品”的《独立时代》有着难得一见的黑色幽默色彩,纷繁复杂的人物不见了深沉和冷酷, 反而多了一丝世俗小民的滑稽。杨德昌用这样一部片子来表达“儒者的困惑”,将台湾社会面临的道德一股脑地抛到观者面前 。 而最后一部影片《一一》对于杨德昌来说,可算是一个完美的句号。影片以一场婚礼开始,以一场葬礼结束,讲述着 一个台北普通家庭的喜悦与哀伤。如何面对家庭的责任、感情的取舍、生与死、哀与乐,导演举重若轻的叙述让人看完觉得通 透,又觉得心头有挥之不去的无奈。8岁的简洋洋在影片结尾独自念着给逝去外婆的信,他说:“我觉得,我也老了……”似 乎预见了那些成人世界的无奈也必将发生在自己身上。 逝者已矣,但从这些电影遗产中还是可以窥见台湾电影曾有的昨日荣耀与尴尬,以及明日的希望。杨德昌曾经的伴侣 、歌手蔡琴说:“时间会给他所有的作品一个公道,他的付出不会寂寞。”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