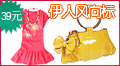|
|
|
|
|
论知识分子对国家权力的态度转变(下)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27日10:47 南风窗
贺照田 本文的上篇(刊于本刊2008年第8期)质疑近年积极为现中国国家权力解释与辩护的知识分子,并非意指知识分子不能对权力有认同与热情,而是试图关注近年来的“新政”(特别是其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及相应实践思路与措施),虽然针对了当下许多急迫且重要的问题,但其基本观念和赖以执行的国家权力机体,也蕴含了多方面的结构性紧张,和多方面的历史性困难。 知识分子的这些辩护与解释,不仅无助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本身的自我丰富与改善,而且可能会误导制定者与执行者对历史-现实的感觉与理解。本文的质疑,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意在关怀——通过什么样的问题意识与历史现实开掘视野,才能使这些知识分子的认同与热情释放出具有积极的成果来? 本文试图在观念与历史的紧张与纠葛中引出问题、产生思考。也即,上面所提诸项问题,都是在先承认“新政”中的诸多观念和措施的积极价值的情况下,通过思考这些观念措施可能遭遇到的困难来提问的。 制度变革为什么走向反面 是以,必需同时面对“中国经济奇迹”与严重贫富分化的急剧发生,既是这两个问题原非不相干,更是因为,当前的和谐社会论在太多人那里实际只成了一个再分配问题,国家对发展成就、国家财政再分配问题。而这样一种状态,其历史的对应便是把“中国奇迹”问题与“贫富急剧分化”问题分开。显然,此种考察追问当代历史的方法,不仅无助于我们进入当代历史、认识把握当代史的复杂,而且直接影响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与感受。 因为把“中国经济奇迹”与严重贫富分化急剧发生分开的再分配思路,无助于消弭、削弱现有和谐社会论中所蕴含的发展与分配、科学发展与已存在的实践的结构性紧张,而且当此结构性紧张在一定条件下变得极其严重时,会因事先缺少认知上的准备,而使现实实践,事实上又回到人们本希望告别的老路上去。 而在已成为知识界焦点并有相当成果的中国奇迹问题和贫富分化问题之外,再提出“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却走向了其反面、何以出现过度实利主义的日常状态和诸种问题,首先在于藉此推动人们去认识、体察国家权力、制度的运作实际和身处于权力位置者的主体精神状况。 因为所谓“新政”的落实既然主要以现有国家权力机体为依托,那么如何设计与努力,才能更富成效地改善并运作此机体,从而使各个层次的国家权力机体都能更富建设成效、更少破坏性,则变成了一个必须被思考与处理的重要问题。要成功思考与处理这一重要问题,当然离不开对国家权力、制度的运作实际和身处权力位置者的主体精神状况的深入认识。 其次,提出这些问题,还在于稍细心省察一下当代史,就可发现,近年大家所忧心的贫富分化,环境、生态、资源危机的形成,不仅仅只是部分观念、制度、措施不当导致的结果,还和中国当代广泛的制度运作、政治权力逻辑、社会运行轨道、多种观念化合成的文化思想状态、日常生活理解与方式、主体精神心理状态等密切相关。而历史性地考察制度改革走向反面的问题,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深度认识、捕捉对中国当代史、中国发展主义具有根本性影响的要素与问题。只有把这些探讨所触碰出来的要素与问题,和通过对“中国奇迹”问题、“贫富急剧分化”问题的探讨触碰出来的问题,一起结合起来思考,我们才可能真正建立出体察当下具体问题的基本认知结构。 而这样一种具坐标性的基本历史认知结构的建立,不仅大大有利于我们更快地进入、把握、定位此历史-现实中发生的各种现象,而且通过把当初对建立起此认知结构做过根本贡献的问题,重新置于此结构所照射的历史场域再观察,可以推动人们去更全面、准确地认知这些已被处理过的问题。这也当然意味着人们有了更好的条件重新认识、体察、评估“中国奇迹”、中国为什么快速贫富分化这些看起来已被广泛关注,但关注路径实已相对固定、相关思考也相对被封闭的重要问题。 第三,提出“以告别家长制、‘一言堂’为出发点的制度变革”为什么走向了反面诸问题,还在于要求我们不把问题探讨视野封闭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而必须把历史视野向前延伸。也就是说: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文革”后中国当代历史的展开,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产生了一些具根本结构性的、关键的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的产生与演变,实和新时期未能更好地接受、转化毛泽东时代某些应该被接受、转化的遗产,却又在另一些本不该再受毛泽东时代遗产左右的地方受制于毛泽东时代遗产高度有关。 两个传统的冲突 审看“文革”后改革开放刚启动时的那段历史,可以清楚看到,邓小平一方面是明确要以毛泽东留下的中国为基盘展开自己的改革的。因此他虽然否定“文革”,却反对“文革”后对毛泽东的过度否定思潮和对毛泽东时代的全面批判与检讨,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新时代的基本口号,且严厉控制了“文革”刚结束时明确挑战乃至否定先前社会主义历史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新时期的后继者们也时时感到毛泽东留下的遗产,特别是制度遗产、观念遗产和他们自己推动的历史展开之间的不协调,而时时进行调整。可惜的是,推动新时期开始使新时期初步展开的这些调整、改革在很多方面未能足够有力地面对好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遗产,而随着新时期的逐步展开,这一新时期兴起时隐伏的问题越来越生长成伤害着后面历史的重要问题。 重点提改革前后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两个传统冲突的问题,当然并非意在换一种方式重复许多人已反复指出的论断:中国大陆现在的问题出在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而意在强调,不在这一历史高度上思考问题,正是我们今天所以陷入困顿的根本原因之一。 也即是说,一方面以先前所遗留的基础为自己的根本展开前提,但在思考如何在新的开展中细致处置、转化、安排此前提的要素和能量上却深为不足;另一方面,在应该告别、超越先前历史的地方却受制于先前的历史。这些问题在历史的演化中所越来越突出对当代造成伤害,因为人们没有历史性地追溯它们的发生与演变,使得这些问题不能得到真正内在于此历史的有力理解。 特别提出毛泽东的传统和邓小平的传统关系问题,意图在于找到可行线索以准确把握我们身处的历史与现实,并在现有条件下探讨遏止与改善此历史中存在的问题对此历史中生命的戕害。而这样一个目标则使问题的关键变成: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大陆其实在不断进行各种制度调整、制度改革,但问题是,这当中为什么只有一部分调整、改革基本达致了预想的结果,而另外一些调整改革则偏离了预想目标甚至走到了预想目标的反面呢? 显然只有不直接以选举制、多党制、议会制来作历史的裁断,并在历史的展开中耐心体察与细究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的认识我们所身处的国家权力的运作实际和所以至此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真的、而非观念幻想地看到改善它的实际可能所在。 即使对那些断定中国的出路在抛弃现有政治权力制度、代以他个人所认定的政治制度的人们而言,此种现实认识亦是有它的意义的。因为任何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社会-精神-心理中由具体人运作的,再精心的制度亦不注定导致理想的结果。因此,在认定一种制度为必须接受的理想之后,便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使此制度真的得到理想运作,而这些都涉及认识历史、社会及人的问题。 在当下中国,由于国家仍为形塑社会、形塑历史、形塑社会心理和人的生活-精神状态的关键力量,因此要研究、认识这一切,都不能不涉及国家权力实际运作,以及既被权力运作塑造,又反过来塑造权力运作的社会问题、精神问题、主体问题。
【发表评论】
不支持Flash
不支持F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