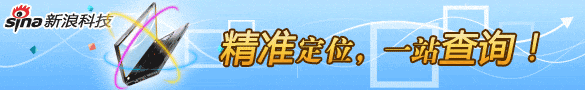药家鑫案涉案3家人三重世界:药母已现抑郁病症
 药庆卫来到儿子药家鑫的床上坐一坐
药庆卫来到儿子药家鑫的床上坐一坐
 案发地长安区学府大街是西安城乡结合部,对面就是大学城和各类房地产项目
案发地长安区学府大街是西安城乡结合部,对面就是大学城和各类房地产项目
 张妙的娘家宫子村,农民们大多已经脱离土地
张妙的娘家宫子村,农民们大多已经脱离土地
 张平选希望等年关前,“没活计可做了,去和药家两口子坐一坐”
张平选希望等年关前,“没活计可做了,去和药家两口子坐一坐”
药案三重世界:阶级、现实与情感
药家鑫已死,张妙入土。从事发至今已有10个月,在法律程序上早已走完的一个简单案件。曾经张家和药家都试图以自己想象中最好的方式和对方沟通,失败了。对于被害者和施害人两方家属,一切的时间、机会、方式、环境、心情完全相反。张家是传统的长安农民,恪守村庄的礼法与人际交往之道;药家是普通市民,以为法律没有要求的事情就是行为的界限。彼此的误读,此后随着公众舆论的加入,变成各种心态交织抗衡的乱仗。双方家人乃至公众,现在越来越深地感受到了伤害。
记者◎葛维樱 摄影◎张雷
受害者:所得非所愿
今年大年初九,张显来到王辉的家。宫子村的土路满是泥泞,张显把宫子村媳妇张妙之死的前因后果听了一遍,又看见王辉要往起诉书上按手印。“我立刻制止了。王辉都不知道那张纸写的是什么。”张显的母亲是过继给宫子村康家的女儿,康家是村里的大姓,张显弟兄不仅都考上了大学,而且在西安当教授、公务员,在村里算是非常光显的门楣。所有宫子村的长辈,都算作张显的“舅家”,因此尽管没有血缘关系,张显也觉得“义不容辞”。
张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妇女,她被害的地方,处在正被大学城和地产项目逐年逼近的村庄。26岁的张妙死亡之前的一个月,都去帮娘家亲戚照顾在附近大学城摆麻辣烫的摊位,这是孩子出生后解决家庭经济窘境的新方法,虽然顶着保守的婆家不愿让她出门的压力,她还是每天很晚回家。在婆家“和婆婆处得有些矛盾,老人爱叨叨几句”,张平选说。出事前一个多月,她才由自家叔伯兄弟做主,搬到宫子村另一处小房子和公婆分开住了一个来月。张妙和王辉的儿子毛蛋只有两岁半,现在由奶奶带着,是家里唯一的宠儿。毛蛋在床上睡得正香,电视机里母亲的葬礼乐声凄哀,这孩子丝毫没有受到干扰。
王辉全家都把张显视为恩人,对于极其务实的王辉一家,这件事随着这张光碟上的葬礼已经结束了。隆重的仪式在村外举行,因为“凶死”,不能进村,火化完了直接去河道边上的公坟埋葬。“听说药庆卫要告张老师?”婆婆非常气愤,“我们又没要他一分钱,他现在还占理了?”王辉作为毛蛋的法定监护人,得到了指定给孩子的网友捐款。而从8月开始,王辉父母开始给打算准备结婚的王辉弟弟盖新房子,对于王家,张显的鼓与呼,带来的是切实走出悲剧的力量。
宫子村大部分人是文盲,农民们只有极少数还在地里做活,大部分人做一些周边服务业的工作倒也容易挣钱。王辉在郭杜村家具城里卖苦力抬家具,从二三层店里到车上,再跟车装卸,一天好的时候一趟有100元收入,没活的情况也有,一个月千把元的收入。张妙有了孩子后总想干点什么填补家用,她上学到初一才停止,王辉却大字不识。“没有文化”是她订婚前对丈夫的担心,但按照王家的习惯,有文化的媳妇并没有优待,婆婆说:“我们从来不让她出去做活,媳妇就应该待在家,穷有穷过法。”
这话让给张妙安排了麻辣烫活计的娘家人陷入了被动。张平选从开始到现在,要的是药家父母来“给个交代”,但这交代随着事件演变,成了张平选心里无法填补的黑洞。“我一开始恨,要把那娃杀了,把他爸他妈也杀了。但是后来我觉得,那个娃,唉,你妈你爸来给我个交代,你赔礼道歉,我给群众给亲戚交代,我也就饶你一命。”张妙的父亲张平选算是北雷村里的先进人物,北雷靠近公路和大学,经济也强。张家的房子几乎几年就翻新一次,瓷砖花样都不俗气。“养不教,父之过,娃的事不是父母的事,但赔理是必须的,饶不饶在我。”
张平选十几岁就出去贩山货、搞小包工,除了80年代孩子们出生那几年,他做过一段时间大队长,其他时间都完全“待不住”。他的勤劳和聪明让三个儿女都念到初中,但近10年郭杜的发展也很快,说是市区,其实长安县改区也只有很短的时间。县里的主要建筑已经和市内相差无几,主要的支柱就是堂皇漂亮的大学城,每个学校的长安校区都极尽设计之能事。大量西安市内的高校在长安圈地,尤以郭杜附近为代表,近两三年修建的小片高层住宅小区,直接矗立在大片麦子和玉米的田地里。
张平选即使把女儿们嫁出去,也还是怀着疼爱,他让娘家兄弟去帮张妙处理婆媳问题,帮小女儿张朗带孩子,这和王辉家把媳妇完全纳入自家系统的想法有些矛盾。王家的房屋简陋,连里带外不过三间小房子,王辉和弟弟都因为太穷,媳妇说得算是村里最晚的了。有大约半年时间,张妙总是回娘家居住,但是经过娘家人调解分房居住之后,她又开始回到丈夫身边。“她也不太会处理矛盾,王辉来哄回去了,过一段又和婆婆闹了。”张平选说,“房子分开住她才算安生了。”
娘家和婆家从思维到诉求上都各有一套想法。“别说是嫁进来的媳妇,就是出去多少年的外甥,回来管每个人都得叫舅。”公公婆婆都很威严,他们把张显看做是“自己人”。“舅家的事,自己人来管是理所应当的。”张平选一开始通过长安县公安局联系了《华商报》,找到的公益律师许涛并不为王辉一家信任。很多人都以为张显是王辉的代理律师,其实张显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副教授,只是王辉的民事代理人。张显的慷慨陈词和对药家的各种看起来言之凿凿的控诉,通过这个有效的表达渠道,王辉和孩子得到了强大的“民意”。
张平选对于张显的加入倒不大在意,他还是坚守父母之道。“我不在乎赔偿多少,但是一切事情都要经过我的同意。”法院一审判定经济赔偿4.5万元,3万元给孩子,1.5万元给父母做丧葬费。他说:“孩子抚养咋弄?老人咋弄?法院说我没到60岁。”张平选决定放弃:“不告了,一切都听国家的。你判到我心里,我不说啥,你判不到我心里,我豁出这条老命。”但他一直留着一块宽容之心:“还是在等,我还有两个孩子,有个依靠,药家老人也50多岁了,就这一个,重生也来不及了,留一条命,有个依靠。从一开始到最后,他们却一直没道歉。”
财富猜想的答案
药庆卫领我们从一楼的空调下面侧身快速走过,低着头丝毫不看二十街坊院子里步道上的人。那些人目不转睛直勾勾地投来目光,一直到我们上楼道还在仰望,好奇心没有丝毫掩饰。如果不是委托北京律师起诉张显,他的日子就一直这样过着。“如果不是网友鼓励我,我也没有勇气打官司。”开了微博之后,药庆卫觉得“骂我的尽管来骂,如果有人愿意听我说,我想絮叨絮叨”。药家来过一个外地网友,夫妻俩做了面条招待。“好多人对我说,他们想错了。我经常碰到有人专门来找我,关心我,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并不是要这样一辈子做活死人的。”
“他死了,为什么我们还在服刑?”药庆卫说自己再忍下去,“一家人也就完了”,药家鑫的母亲已经出现抑郁的病症。家里是三室两厅的屋子,客厅和餐厅较大,三个卧室都小。药家鑫的房间仅容钢琴、床和电脑桌之外一个人转身,墙壁还有浮雕的勾花,吊灯也是过去的花样,看得出来房子刚分下来时的精心装潢。“我家就算这楼里最不好的了。”家里所有的家具、电器都看得出是曾经的好东西,只是用了很多年。冰箱里是一罐罐腌菜熟食,厨房灶台和油烟机后的瓷砖缝隙都是白色的,光亮无尘。
华山机械厂曾经是西安东郊最大的几个国有大企业,所谓“街坊”就是几栋楼围成一个家属院,有自己的院墙和门卫。这个厂子有约30个街坊,几万人的生老病死就在里面,“逃都逃不掉”。上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效益还不错,再加上是军工单位,很是兴盛了一些年。药庆卫1996年回到西安就来到了华山厂工作,此前他一直在外地部队工作,基本上药家鑫都是妻子一个人带着。药庆卫虽然对各种钢琴曲烂熟于心,但真心喜欢的是贺绿汀。“部队里培养起来的喜好,巴赫太难练了,弹好之前是很难听的。”无论年节,家里老人只要来了就让儿子去弹琴,母亲总是在一边忙碌。“他学琴一直是我爱人从小跟着上课,我爱人现在听琴对谱子、节拍、指法算是很内行了,只是不会演奏。”家庭表演没有掌声、表扬,对于一家人,培养一个弹钢琴的儿子,更多的是小环境里的良好感受。“他弹琴让我们觉得幸福。”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