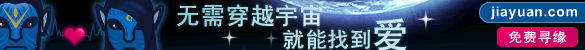枪击案因政府介入转变成政府和百姓的博弈
命案后各路警力迅速赶到现场,已经调任关岭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的罗亚林22点多接到命令,迅速赶回坡贡,当晚就开始介入事件调查,到目击者家中做笔录,李恒学就是在吊井组的家中见到的罗亚林。和他一同被调到坡贡的另两名警察是陈志华和朱学安,罗亚林说,“都是以前在坡贡当过所长的人”。但蹊跷的是,当事者张磊似乎并没有被立刻采取强制措施,1月14日,他的手机依旧可以打得通。打通电话的人用本地话佯称报警,张磊说自己已经调离坡贡,还报出了坡贡派出所的座机,这次对话也被部分记者现场录音作为证据。这则新闻次日见报,张磊的手机也从这一天开始进入关机状态。
1月21日本刊记者见到罗亚林的时候,他正在派出所一楼办公室里。他从2003年底到2008年3月间在这里任职,那时还只有老办公楼。新楼是他选的地址,不过竣工以前他就调离了,如今临危受命回来,居然坐进了新楼,怎么都像命运的玩笑。他在坡贡的口碑很好,陆续到他办公室来询问户籍琐事的几拨村民,疑问大都相似,但罗亚林还是需要分别做答,末了,他们要做同样的感慨,“还是罗所长回来好”,“态度好,耐烦”。这让罗亚林哭笑不得,他对本刊记者的解释也像自己安慰,“这次只是临时过渡,不是正式调任”。
与关岭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的工作比起来,小镇派出所所长的工作显然要枯燥琐碎得多。罗亚林指着大厅里那些排队的人,“都是办新身份证或者上户口的”。这是小镇派出所日常最主要的业务,其他的也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纠纷。村镇里最恶性的案件是偷牛,尤其是年前这段时间,但村民们报案之后,只不过是多了一条记录而已。3名警察的警力配置,能够处理的,其实也只有日常这些琐屑的事情。
罗亚林以前在坡贡任职的同期,张磊在关岭县岗乌镇任副所长。虽然张磊2008年3月接替罗亚林时还是副所长,但罗亚林说,“张磊还是属于升职”,因为“他现在可以主持全所工作”。1997年参警的张磊是贵州平坝县虹湖机械厂子弟,1977年出生,1995年毕业于机械厂的职业中学。参加了原安顺地区公安处人民警察初任培训之后,被分配到关岭县公安局上关镇派出所,2003年10月调至岗乌镇。关岭县公安局政工室主任王湛说,在同批分配到关岭的十几个警察里,张磊是提拔得比较快的。
就在2004年4月4日,张磊任职岗乌不久,就因为和同事梅陆一起,深夜无故闯入小盘江村村民岑金能家中惹出麻烦。当时岑金能还在广东建筑工地上打工,“那时候不像现在,我也没有手机,家里人要打个电话也不方便,这个事3个月以后我回到家里才知道”。岑金能回来后,从妻子和村民那里得知的情况令他愤怒,“那两个警察就无缘无故跑到我家里,把门踢开,乱砸东西,当时只有我老婆和一个小孩子在家,她拼命喊救命,来了很多村民围观,后来所长龙发才把两个警察领走了。第二天,龙发才找驻村干部伍典卫来我家里说和,他和我老婆伍典芬算很远房的亲戚。龙发才提出用60块钱买回那晚警察落在我家里的皮包,但我老婆不肯,后来他们就走了”。这个包至今仍旧保存在岑家。至于张磊和梅陆闯进来的原因,岑金能实在不清楚,他也是辗转听村民说,当晚这两个人是喝了酒,搞错了。
岑金能起初的要求很简单,“我们是布依族,按照我们村的习俗,道歉只要一只鸡、一壶酒、一挂鞭炮就可以了”。但没人理会他的要求。岑金能不识字,他找人帮他写了投诉材料,6名村民自愿按了手印。岑金能把材料分别送到关岭县政府、公安局和法院3家单位,但都是石沉大海。小盘江村很闭塞,岑金能说,2004年他出门打工的时候,“都是走路到江边的铁索桥下游,坐五六个小时的人工船到板江的小铁索桥”,然后再换乘汽车到其他地方。就是现在,从关岭到岗乌的车程仍需1小时40分钟,而从岗乌到小盘江村,需要绕着山路下到谷底,几乎180度的急转弯一个接一个。跑运输的面包车的女司机说,这条路是去年才修整的,“不然就算挂一挡慢慢走,都经常会被卡住,要下来推车,车毁得太厉害了”。可就算道路修整之后,开起来依然颠簸,耗时需一个小时。岗乌汽车站有从岗乌到简江的中巴,途经小盘江,但这趟车“如果人少可能一天都不会开”,果然,当记者返程的时候,一大早就停在车站的中巴车,依旧车门紧闭。
这桩陈年旧案如今能被重新发掘,岑金能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1月22日本刊记者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关岭县医院照顾感冒引发了并发症的小女儿,他感慨说:“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电话、没有网,什么消息都传不出去,我一天打工也就挣二三十块钱,到县上一次,路费都不够用。我是想继续告状的,可实在没有钱,只能放弃了,现在真的很不同了。”
补偿款的逻辑
坡贡镇政府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时代的差别。命案之后,政府人员和警力赶到前,死者亲属已经找摩托车店老板借了电线,拉了临时警戒线保护现场。接下来打电话通知村里和外地的各路亲属。郭永华的弟弟郭涛就是在接到电话后迅速从凯里赶回来,当晚23点多到达现场。
枪击案原本只是警察张磊的个人问题,但当地政府迅速而强势的介入,却将方向奇怪地转变成了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博弈。郭涛和其他几名家属作为代表,参加了由关岭县张县长、胡书记和坡贡镇书记罗兴平主持的谈判。“一开始就是谈钱。”郭涛回忆,“张县长让我们要冷静,说刑事责任公安局会处理,但跟政府的补偿没有关系,这个钱是政府出于人道主义给的。”接下来就是僵持到次日早上6点多种的讨价还价,政府的价码是1人20万元,而家属的要求是1人75万元,郭涛说:“我以前看过一些新闻,出事后找人咨询过得出来的。”到天亮了,双方终于达成一致,“1人35万元”。回忆起这段过程,郭涛的心里并不好受,“说到谈价钱,你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太冷酷了,死的是我们的亲人,我们怎么可能不难过,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啊。我们哪里能拗得过政府,如果不谈,可能什么都没有”。
或许是因为瓮安事件的余波,维稳成为当地政府的首要需求。关于坡贡镇的民情,《安顺日报》2008年一篇文章这样描述,前几年的坡贡因为贫困闭塞,农村闲散劳动力过多,“为鸡毛蒜皮之事打闹的人不少,群众与政府工作人员发生口角之争那是常有的事”,“曾发生过村民冲打政府、集几百人堵水黄高速路等群体性事件”。妥善安置尸体是重中之重,政府和家属签订的协议中写明,死者必须在17日之前下葬,下葬之后,政府才会按约定支付补偿款。而且这70万元的补偿款是以政府救济款的名义发放。镇党委书记罗兴平的解释是:“先用救济金垫付,等最终处理结果出来,会把钱补上,该谁的责任谁出钱。”
谈判完成之后,1月13日中午开始尸检,郭涛回忆,“持续了七八个小时”。但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关注尸检的同时,政府方面已经组织了第一次新闻发布,通报枪击案是因为两名村民酒后闹事,“抢枪、袭警”。家属在1月14日才从新闻中得知这个论断,异常愤怒。他们虽然为了补偿款在15日安葬了两名死者,但只是浅浅地象征性掩埋。他们做好了另一手准备,“袭警的结论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根本不是事实,如果不能还死者一个公道,万不得已,我们就把棺木挖出来上街”。
因为诸多记者的到来,安顺市在1月18日组织召开了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论断依旧是袭警。但这场新闻发布会的主持者们,因为无法招架记者们的提问,只能草草退场,整个发布会的问答记录,非但不能释疑,反而成了一场闹剧,让主持者颜面尽失。于是政府方面拿出了新办法,他们要求来采访的记者不仅要持有记者证,还要有贵州省宣传部门出具的同意采访的证明,如果记者们拒绝配合,相关人员或者以半武力的方式强行“护送”记者离开,或者强势告诫,“如果一意孤行,始终只能拿到单方面的信息”。
通往吊井组郭家的山路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基本上每天都会有政府的工作人员前来蹲守查访,有时候他们并没有事情可做,就只好在半山腰的必经之路守株待兔。看到陌生人或者尾随而上,或者直接就把人堵住,盘查证件并且拒不放行。他们的姿态有些激怒郭家的人,“我们又不是犯人,为什么每天守在我们家门口!”而他们的情绪,反过来,又让政府方面更加把记者视为心怀不轨的不速之客。特地赶到坡贡镇的关岭县宣传部女部长质疑记者们的目的和动机,她觉得“这个新闻已经没有时效性和价值,要做深入分析,也是相关专家和部门的事情”。并语气铿锵地说,“你们这些记者的到来,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当地政府的工作和百姓的生活”,旁边还有人认真地做着记录。
对于死者郭永华和郭永志的家属来说,这种混乱场面,甚至剥夺了他们安静悲伤的机会,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愤怒和无奈中焦灼。33岁的郭永志结婚刚一年多,妻子杨炳珍才24岁。他们的儿子去年4月10日出生,如今刚9个月。他去年刚和两个朋友一起凑了几万块钱搞了个小采石场,生意才刚刚开始。他是个疼惜老婆的人,每天忙完采石场的事情,都会回来给不会做饭的杨炳珍弄吃的。现在,杨炳珍只能抱着孩子到亲戚家搭伙。每个人抱起孩子,都会说上一句“可怜啊”,然后顿住,不敢问杨炳珍以后怎么办。
43岁的郭永华和妻子胡家英结婚已经20多年,他们秉持着最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没有儿子,家里活根本干不下来”,因此屡次超生,育有3女2子。老大和老二跟随亲人都在福建的箱包厂打工,老三郭红敏14岁,初中一年级,算是家里目前学历最高的人,也是成绩最好的一个。两个弟弟虽然彼此相差两岁,但都在读小学三年级。3个人都在坡贡镇上住读,郭永华以半学期200元的价钱,从熟人那里租了一间只能放下两张床的房间给孩子们当宿舍,由依旧还是个孩子的郭红敏负责照顾两个弟弟,放学之后洗衣做饭。
郭红敏16点20分放学,1月12日那天,她正和几个同学在回出租屋的路上,突然看到摩托车店前的混乱情形,突然有同学跑来告诉她,你爸爸死了。她真的认出是爸爸,呆呆地站在那里,都忘记了怎么哭。回到出租屋,两个弟弟已经回来,她开始收拾东西,跟来接他们的长辈回了家,再也没回镇上。其实1月13日就是初中和小学考试的日子,初中考7门,小学2门。考完就正式放寒假了。郭红敏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但她喜欢读书,也渴望重回学校。
胡家英不忙家务的时候,大多数时间都安静地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听着。在我们要借宿的晚上,她把家里唯一体面的房间让出来,铺上新的被褥和毛毯。次日上午离开的时候,本刊记者终于有了一次单独和她谈话的机会。安静的氛围,终于让她忍不住释放了内心的悲痛,但她并不愿意在外人面前流泪,转过身去,独自走到牛棚旁边的角落里,颤抖着擦拭着眼角。再低着头转过脸来,压住嗓子里的颤音,轻声道别,她并没有说自己有多悲痛,她说的只是,“让你们辛苦了”。■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 贵州警察打死村民事件死者家属各获35万补偿 2010-01-18 16:39
- 贵州警察连开五枪打死两名村民遭质疑 2010-01-16 02:29
- 贵州政法委调查安顺警察开枪打死两村民案 2010-01-22 22:09
- 贵州安顺开枪打死村民警察被曝曾带枪打砸民宅 2010-01-21 04:41
- 贵州开枪打死村民警察领枪不足一月 2010-01-19 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