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凶者王宝洺:一场漫长而绝望的诉讼
 王宝洺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朋友称其为“京城草隶第一人”。图为王宝洺家的书房。
王宝洺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朋友称其为“京城草隶第一人”。图为王宝洺家的书房。
 王宝洺
王宝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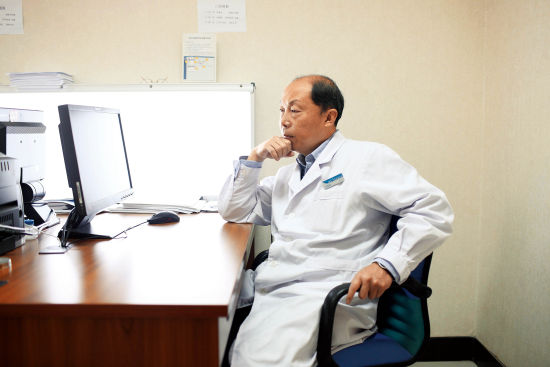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吴雪溪给王宝洺做了全喉切除手术
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吴雪溪给王宝洺做了全喉切除手术
 同仁医院常年法律顾问金晓兵
同仁医院常年法律顾问金晓兵
行凶者王宝洺:一场漫长而绝望的诉讼
医疗纠纷一旦发生,关键要有一条畅通的化解路径。法律诉讼优于协商解决与调解的地方就在于,一旦进入法庭,医患双方就是平等的法律主体,不再有专业知识和医疗信息的不对等。王宝洺选择了诉讼方式来解决他与徐文的矛盾,却终究将刀举向了徐文。导致悲剧的不仅是王宝洺偏执的人格,还有医疗纠纷案件中让人绝望的办案效率。
记者◎丘濂
选择诉讼
2007年9月12日,王宝洺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进行全喉切除手术后基本康复出院,回到家里,他把有关书法的书籍卖掉了大半,也停止了原来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后雷打不动的练字习惯。朋友打电话来,他不能说话,便叫爱人龚美华告诉他们,自己“有事、不在家”。他把自己整日关在地坛附近那栋老式居民楼的家中。
这套建造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两居室,居住起来并不舒适。“王宝洺喜欢散步。也许是靠近地坛公园的缘故,他原来在北京曾有过几处住房,都舍不得搬离那里。”他的一位朋友万永庆对本刊记者说。万永庆还记得,王宝洺最意气风发,是90年代末他刚刚在奥体中心开办英东书法培训中心不久。“有一天,我们一起喝了点小酒,王宝洺的状态很兴奋。在书法教室的大桌子上,他饱蘸浓墨用行书写下了‘精气神’3个大字,一连写了七八张。他挑了最满意的一张给了我,还题上了一排小字:‘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会用三宝天地通。’”万永庆说,当他不顾王宝洺反对到他家中,看到的是出院后另一种面貌的王宝洺。“他的脖子上做了气管造口,喘气不再经过口鼻,时而会看到他从那个口向外咳痰。他的左胸取下了一块皮肤,补到了脖子上,因为颈部皮肤下也长满了肿瘤,需要全部切掉。这让他行动的时候,身体会向左倾斜。”万永庆说,“他见到我,脸上完全没有一丝笑容。”
在王宝洺的家中,本刊记者看到他手术后的照片。那是一组他和龚美华拍的中式婚纱照。“就是想逗他开心才去照的,你看他脸有些胖,那是浮肿还没有消退。他特地选了立领的唐装,为了能遮住他脖子上的洞和伤疤。”龚美华告诉本刊记者。
此时的王宝洺有两件极力认真去做的事情。一件是学习食道发声。龚美华告诉本刊记者,王宝洺报名参加了肿瘤医院的食道发声培训班。“他几乎是班里学习效果最好的,培训完与人交流沟通没什么问题。他待在家里反复练习,最初是学着‘打嗝’,然后又去读阿拉伯数字,还有诗歌。”另一件事情就是去解决他对于第一次在同仁医院做的手术究竟有没有“失败”的疑惑。在他看来,正是在喉癌初期时徐文做的“伪手术”没有将肿瘤切干净,才发展至喉癌晚期他不得不在肿瘤医院进行了全喉切除。
龚美华说,王宝洺最早对徐文的手术产生怀疑是在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拿到核磁共振影像学报告时。2006年10月23日,王宝洺从同仁医院完成“全麻支撑喉镜下CO2激光右声带扩大切除术”后出院。同仁医院的法律顾问金小兵向本刊记者介绍,由于他出院的时候,手术中送病理科检验的标本结果还未出来,所以医院方面的嘱咐是一周后要进行门诊复查,根据病理回报结果来确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如果结果是阳性,就要考虑进一步放疗或者喉部分切除手术。“而当10月25日病理反馈出来时,医院特地打电话通知他来复查,他没来。”金小兵说。龚美华的解释是,虽然没有复查,但他们是严格根据同仁的要求,去一家有放疗设备的医院,也就是肿瘤医院继续治疗。放疗前,肿瘤医院的医生需要核磁检查来判断病情,于是在2006年11月1日的核磁诊断报告单上,就有这样的表述:“右侧声带较对侧略增厚。”王宝洺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徐文没有真正做右声带切除术。之后,由于肿瘤医院放疗科大夫外出,王宝洺在海军总医院放疗,从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一共接受了7000拉德的放射剂量。2007年7月21日,王宝洺因呼吸困难再次到同仁医院就诊,检查后发现是喉癌复发堵塞喉声门区,医院于第二天施行了“气管切开术”。按照龚美华的说法,实际此时他们已经对同仁医院失去了信任感,之所以还在那里就诊,是因为当时王宝洺情况紧急,“从家出发到同仁医院,有公交车就能直达”。在情况稍微好转后,王宝洺便办理了出院手续,经过打听,找到了肿瘤医院擅长治疗喉癌中晚期的吴雪溪主任医师继续治疗,并最终听从他的建议,做了“全喉切除、双颈淋巴结清扫、胸大肌皮瓣修复术”。
在王宝洺家人和朋友的记忆中,在最初“解决疑虑、讨个说法”的阶段,只和同仁医院有过一次不愉快的接触。“那次是我陪着王宝洺夫妇去的,我还拉上了一个北京大学毕业的朋友。去之前我们就商量好,这次去只是让他们把手术过程中存不存在问题讲清楚,不要谈赔偿。”万永庆说,“结果我们到早了,同仁那边主要负责谈话的人还没来,一个小姑娘先接待我们。王宝洺向她抱怨,都是因为自己事先包好的1万元红包没有送到,徐文的手术才没做好。小姑娘就接过话说,实际也不是,徐文当时把喉镜一撑开就后悔了。我们就要追着往下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手术前检查不充分?是不是在病情比预想要糟糕的时候,徐文还坚持原有方案导致了手术失败?但这时主要谈话人就过来把话题岔开了。我们的想法是让他们把手术之前一系列准备工作都做了什么给写出来,这样就可以对照诊疗规范,判断出他们的不足之处。这位谈话人不愿意写,他只是模棱两可地说‘该做的肯定都做了。’”那次谈话后,双方还约定了第二次会面,“但是临时取消了,我估计是上次谈话,让他们感到我们不是那样好打发的”。万永庆说。
在这个阶段,王宝洺很想和徐文见面。“他几次去过医院,想亲自问问她手术的情况,徐文都不在。”龚美华告诉本刊记者。本刊记者了解到,一般医院处理医疗纠纷,都会派医务部有法律背景知识的工作人员和相关科室的其他大夫,共同来向患者及家属解释,涉及纠纷的医生往往不会出面,这是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但对于王宝洺而言,徐文没和他开诚布公地沟通,反而加重了他心头的怨恨。王宝洺的姐姐对本刊记者说,法庭开始审理后,她曾经去医院找过徐文。“我看到她正在看病,走过去说,忙着呢?别再瞧坏几个病人。徐文看上去很冷漠,她不愿意和我说话。她背过身去,打电话给医务部,让他们来接待我。我只是想听听她自己是怎样总结那次手术的,回家好转述给弟弟。也许这样就能互相理解呢?”
与医院直接对话不成,王宝洺经朋友介绍找到了燕园律师事务所的魏崇德律师。魏崇德提议他先去咨询一位在北京市卫生法学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工作的朋友,看能否调解。这是在医院协商解决与法院诉讼解决之间,又一条医疗纠纷的化解路径。“法庭做出判决不能达到息讼的目的,双方怨气还在,并不利于社会和谐。如果通过调解,医患双方达成一致,那就最好不过。”一位经常代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律师对本刊记者说。调解中心在2005年成立,政府没有做大力宣传,也不为人所知。“主要过去我们的运营经费是由保险公司支付。百姓会有一种印象,既然我们的钱来自加入医疗责任保险的医院所缴纳的保费,我们在调解时就会偏向医院。”自成立以来就在那里工作的一位调解员这样告诉本刊记者。在今年5月30日,调解中心更名为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医调委”),运营费用也改为北京市财政局拨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第三方调解机构。
万永庆记得,他陪同王宝洺夫妇当时去调解中心,直接找的就是那位朋友。“因为是熟人介绍,他说得很坦诚。他说,同仁医院在手术上是有问题的,但这是一家副部级的三甲医院,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人原来又都是医生,无法不站在医院的立场上。”本刊记者在医调委查询,并没有看到王宝洺当年在这里进行调解的相关记录。可以查得到的只是一份2010年1月5日的电话记录,家属希望医调委能有人做王宝洺的代理人来出庭。那位调解员告诉本刊记者,如果仅仅是咨询,没有进入之后的调解程序,在医调委是没有留下资料的。而按照调解中心的处理原则,行政部门有结论或已经进入法庭审理的纠纷,他们一般不会受理。调解工作压力大,人员流动性大,那位提供咨询的朋友也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他所说的话也无法核实。但本刊记者了解到的调解工作流程和调解员的工作态度,和万永庆描述的并不相符:“在咨询阶段,我们不可能告诉患者医院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既没有认真看过病历材料,也没有请教过相应的临床专家。在调解过程中,我们和患者交谈,绝不会过多指责医院。即使在最后生成的调解协议书上,医院应该负一定责任,我们也只是用一种中性叙述去谈诊疗过程,不会明确指出院方那些具体的操作失误。这都是调解员的工作技巧,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弥合医患双方的间隙。”
至于医生出身的调解员会不会影响结论的客观,医调委的刘方副主任告诉本刊记者:“现有的46名调解员有13名都获得了副主任医师以上的技术职称。大部分调解员都是二级医院退下来的管理层人员,并都有临床工作经验。我们是替患者找医院过错的。即使是三级医院的知名医师,如果真的犯了错误,调解员也一定会和他据理力争。”刘方认为,那位曾为王宝洺提供咨询的朋友的话绝对只能代表他的个人意见。
王宝洺最终还是选择了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他和徐文之间的矛盾,而对于同仁医院,它不会畏惧走上法庭。曾经担任北京市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的陈志华律师告诉本刊记者:“名誉对私营小医院很重要,它们会力争在法庭之外调解。来大医院看病的病人绝不会因为一起官司而减少。真正在自查过程中认为自身存在错误的大医院,则会在上法庭前主动赔偿。”而认为对患者损伤并不承担责任的大医院,却缺乏调解的动力,“因为进入法庭之后,有法律顾问来做处理,医院方面的负担要小得多。即使最后院方真的要赔偿,也会比调解协商金额要低。”这就是为什么按照程序,面对王宝洺的投诉,参加医责险的同仁医院本可以主动向保险公司报险,再由保险公司通知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出面解决,但实际同仁医院并未这样去做的原因。“同仁直接对我们讲,那就打官司吧。”王宝洺的姐姐说。
对于王宝洺而言,则认为诉讼是一种最公正的纠纷解决方式。“在法庭上,医患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从医疗信息上来说,通过庭上证据交换,患者可以获得全部病历,包括之前并不能得到的主观病历部分。从医学知识上说,很难说医方具有强势。因为对于医院在诊疗中是否存在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需要医学会或司法鉴定机构来判定。曾经在法庭上,被告医院一方指责原告患者一方不懂医。我作为原告代理律师说,正是因为患者不懂医,我们今天才会走上法庭。”陈志华告诉本刊记者。
变换法院
2008年8月12日,王宝洺医疗损害赔偿案在朝阳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在法庭外的楼道里,吴雪溪医生看到了王宝洺。“原来是他啊!”吴雪溪医生说,在开庭前一天,他接到了院方参加出庭的通知,“‘因为一个叫王宝洺的病人把你给告了’,他们这样说。我仍然对不上号谁是王宝洺”。等候开庭的时候,吴雪溪医生还给王宝洺简单检查了一下,看他肿瘤有没有复发。“我对他说,你当时来就诊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了,手术取得这样的效果很不容易,需要定期复查。手术之后的一两年正是你的黄金时光,应该好好享受生活,折腾什么官司啊?”
吴雪溪医生当然也不明白王宝洺为什么要告他。他认为,在肿瘤医院的整个治疗过程,王宝洺和家属都很满意。“王宝洺来到我这里,最主要的疑虑就是,他的喉癌真的复发了么?我为他做了细针穿刺,在一个不太可能长肿瘤的地方刺了一下,检测结果证明有癌。这一针就告诉他,确实复发了。同时我也就确定了手术方案:以喉为中心,打一场肿瘤歼灭战。也就是将肿瘤可能涉及到的组织全部切除,包括全喉、淋巴组织,甚至包括颈部的皮肤和周围的肌肉等等,还要利用胸前的组织转移修复颈部的组织缺损。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没有过度手术。手术后王宝洺一直生活到现在,没有肿瘤复发。”
吴雪溪医生治疗的病人以癌症晚期或是癌症复发居多。“大多数患者都经过了一两次手术,他们经常会有疑问,肿瘤复发是否和以前的手术有关?其实,恶性肿瘤的复发是由于肿瘤的生物学行为导致的。”
吴雪溪医生说:“类似核磁报告的影像学报告下端都会有一行小字‘仅供临床医师参考’,这说明报告只是医师之间互相交流的材料,患者切忌望文生义,做出非医学的错误理解。”
对于徐文手术是否“作伪”,一家三甲医院的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在看完手术记录后,对本刊记者给出了自己的观点:“有一个细节足以说明徐文对待手术的认真态度。术中一共取下了三部分标本去送病理检查,其中‘右声带肿物大体标本’来自切割下来的肿物,‘病变前联合切缘’和‘右声带外切缘’则来自保留下的组织。标本选取充分,为下一阶段的治疗提供了依据。这就好比打扫房间,你可以仅拿大笤帚扫一遍,也可以扫一遍之后,再用小笤帚清扫细小的角落,徐文医生的做法就是后一种。”而对于王宝洺所提到的“右声带”,这位医师说,实际可能只是“右声带部位”。
经过法庭外与王宝洺的交流,吴雪溪医生逐渐明白王宝洺对肿瘤医院的治疗根本没有意见。王宝洺的博客中,明确写着:“在吴雪溪教授的精湛医术下,经过6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清除了残余癌细胞,才挽回了我的生命。”将同仁医院和肿瘤医院同时起诉完全是诉讼策略的考虑。当时的代理律师魏崇德对本刊记者说:“一是想避开同仁医院所在区的东城法院进行审理。东城法院的法官都会去同仁医院看病,我们担心这里会存在偏袒。另外,也是希望肿瘤医院在法庭辩解的过程中,能够从专业的角度,指出同仁医院在治疗过程中的失误。”于是,在王宝洺一方提交的起诉状上,这样陈述同仁医院的过错:在对原告的诊疗过程中,同仁医院违反诊疗常规,对原告未尽充分的注意义务;术前告知不充分;手术操作草率,极端不负责任,未将肿瘤组织全部切除,直接导致手术失败。对肿瘤医院的过错则说得很笼统:检查不充分,盲目手术,加重了原告的身体伤害。起诉状上提出的经济赔偿只是两万元,不是王宝洺一直以来对外宣称的1700余万元。魏崇德说,这同样也是一种策略的考虑:“因为诉讼请求中提起的赔偿越多,一开始给法院交的诉讼费越多,赔偿可以在对医疗过错鉴定结论出来后再做调整。”在王宝洺自己计算的1700多万元中,1500万元是误工费:由于无法继续讲课,他的书法学校在2006年第一次手术之后停办,学校每年平均收入50万元,一共算了30年的时间。
王宝洺案在朝阳法院审理期间,一共经历了两次开庭和三次谈话。在2008年9月25日倒数第二次原被告都到场的谈话中,王宝洺一方还提出了“十一”国庆节之后要补充证据对病历提出新的质证意见,但在9月27日的谈话中,龚美华就代表王宝洺向法官陈晓东表示,“根据案件发展的情况,考虑撤回对肿瘤医院的起诉”。龚美华对本刊记者说,法院一直在动员他们撤诉。“法官说,吴雪溪医生每次开庭都到场,他平时的工作又很忙。既然你们不是真的要告肿瘤医院,就不如把他们撤掉。同时法官许诺我们,撤诉后肯定不会移送给东城法院。”魏崇德说,王宝洺家属征求他的意见,“我的意思是不要撤,就怕审了半截给移送。家属就说,法官都承诺了,肯定不会移送的”。然而,10月13日,朝阳法院就给东城法院发送了移转函,认为应该以同仁医院所在地址作为确立管辖权的依据。陈晓东对本刊记者说,侵权案件要以被告所在地或侵权行为发生地来确定审理法院,既然被告只剩下东城区的同仁医院,朝阳法院肯定不再有管辖权,移送是必然的。“我们递交完撤诉申请,朝阳法院就一直没开庭。我们打了几次电话催促,他们就说现在法院又不止这一个案子,不能着急。结果几个月后,我们再打电话,他们说,早就移送了。”龚美华说,“王宝洺就生气,觉得是律师没有把握好。”移送东城法院审理后,魏崇德还去接受过一次询问,“应该是在2009年初,天气还冷的时候”。但是后来,魏崇德接到了东城法院的电话:“法院问,怎么又增加了一位律师啊?我就明白,王宝洺他们已经把我给换掉了。”对于朝阳法院为什么要移送,龚美华有她的解释:“在朝阳法院审理期间,王宝洺给北京电视台的‘法制进行时’写信,最后该栏目对案子进行了报道。大概觉得媒体关注度太高,朝阳法院感到棘手,才会让我们撤诉。”
王宝洺后来聘请的律师是华鹏律师事务所的杨律师。本刊记者请教了多位擅长代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律师,他们均表示,王宝洺案2008年7月8日在朝阳法院立案,至今审理3年多仍未结案,是十分少见也是不合理的。“变换法院来审理是造成此案在审理时间上拖沓的第一个原因。如果王宝洺能够坚持当初的策略,即使对肿瘤医院的起诉被法院驳回,案件依然可以在朝阳法院审理。”杨律师说。这样,不同法官对案子的驾驭能力就可能导致另外一个结局。
病历纠缠
在朝阳法院第二次开庭交换证据时,王宝洺就对同仁医院拿出的病历提出了质疑。“王宝洺早年曾经在和平里医院的病案室工作过,所以他知道,一旦对医院的治疗产生不满,应该立刻封存病历以保全证据。在2007年,他曾经两次封存和复印病历,包括在同仁医院两次就诊和住院期间的全部材料。”龚美华对本刊记者说。根据卫生部的相关规定,患者只能复印记录他症状、体征、病史、检查结果、医嘱等情况的客观病历,而记录医生对病情观察、分析和讨论的主观病历,双方可以共同封存后保存在病案室,但患者不能复印。在法庭上对病历进行了拆封,王宝洺就看到了双方手中的客观病历有不一致之处。他第一次见到了主观病历,也发现其中的诸多问题。当朝阳法院委托东城区医学会做鉴定后,魏崇德立刻传真给医学会一份详尽的质证意见。东城医学会不能判断出真伪,于9月24日致函法院决定中止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病历是医疗纠纷的处理中,所有其他任何证据不能替代的,是证据中的核心。”陈志华对本刊记者说,“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有: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是考虑到医患双方医学背景知识不对等而设计的‘举证责任倒置’。医院能举证的就是所保存的病历。如果患方能将医方提供病历的真实性打掉,医方无法举证,那就可能输掉官司。真正因为医院提供病历不真实而被判全责的案例极少,却会给患方及代理律师一种希望,即不经过之后的鉴定环节,法院就能直接做出判决。”
由王宝洺和魏崇德一起完成的这份质证意见一共写满了7页A4纸。“提出这些问题,是我们的权利,也是协助法院查清事实的一个步骤。至于这些能否说明病历就是经过篡改和伪造,需要法院做出判断。”魏崇德对本刊记者说。杨律师则将问题归结为两类。“一类是需要法院来判断的有关病历真实性的问题。比如客观病历的住院病案首页中,王宝洺手中那份病理诊断一项是留白的。同仁医院那份却写了‘鳞状细胞癌,前切缘未见肿瘤,后切缘见部分肿瘤’。同仁的意思是王宝洺复印病历的时候,病理回报结果还没有出来,后来要封存,病历就要做完善。那么这两份病历要采用哪份来做鉴定?还有王宝洺提出,在属于主观病历的病程记录中,2006年10月13日、14日、20日的徐文查房记录后,不是徐文本人的签字,是别人代替徐文来签的。同仁的解释是,当时是下级医生和徐文一起来查房,下级医生写记录,之后想找徐文签字时,她可能又去忙别的了,于是经过徐文的授权写了她的名字。王宝洺的逻辑是,因为签字是假的,这几天的病历也是事后伪造的,而且他记得在住院期间,根本没有看见徐文查房。这样法院就应该给出意见,到底这部分病程记录送不送去鉴定?另外一类是需要鉴定机构来判断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王宝洺谈到,病程记录中的术前讨论里,徐文的意见是,‘喉CT及增强显示病变范围基本限于声门水平,喉室及声门旁间隙未见异常信号影,可以考虑单纯行声带部分切除或黏膜剥脱,不做部分喉切除术’。而王宝洺认为,CT报告的结果和徐文得出的结论并不相符,徐文没有采信CT医生的建议。这类问题则需要鉴定机构给出结论。”
在朝阳法院未对病历真实性做出判定的时候,案卷就移交给了东城法院。由杨律师的工作记录可以看出,东城法院仍旧委托东城医学会继续鉴定,但医学会还是在2009年9月因为真实性的问题退回了全部病历并出了终止函。陈晓东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介绍,鉴定有医学会鉴定和司法鉴定两种,也就是所谓的“双轨制”。“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院可以优先申请医学会做医疗事故鉴定来抗辩。但是鉴定完真正构成医疗事故的比例很低,像我们曾对北京市某区医学会做过调查,100例医疗纠纷中,构成医疗事故的只有两例。所以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出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又提供了另一条救济途径,患方还可以提起司法鉴定机构来做医疗过错鉴定。”经过摇号,王宝洺案转给了中天司法鉴定中心。由医学会鉴定又转为司法鉴定,是本案审理时间漫长的另一个原因。
无论哪种鉴定方式,对病历真实性的判断都应该在法院的质证环节中完成。《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16条规定,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鉴定委托。但是,病历真实的标准是什么?是否因为有了一些涂改和添加就能完全否定病历的真实性?法官单独凭借法律知识就能为病历真实性下结论么?北京另一家司法鉴定中心的杜主任告诉本刊记者,由于病历都是人手写的,难免会出现瑕疵。“法律上的不真实,是指有两份不一样的病历同时存在,这种情况很少。大部分患者不认可的病历,都是有一些局部的错误的‘瑕疵病历’。有的法官可以凭常识就判断,比如床号写错了,这对鉴定不会影响。但有些问题,虽然法官可以做出一些初步的内心确认,但这些问题会不会对最终责任判定产生实质影响,还需要有相应资质的人员运用专门知识来做判断。在这个阶段,鉴定机构可以向法院提供专业性的帮助。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3条就规定:经审查,病历资料存在瑕疵的,人民法院应通过咨询专家、委托文件检验、病历评估或由鉴定专家做初步判断来认定瑕疵病历是否对鉴定有实质影响。如果没有,则仍可继续进行鉴定,但瑕疵病历部分不能作为鉴定依据;如果有实质影响,造成鉴定无法客观进行,则应终止鉴定。”
不过在陈志华看来,进入实质鉴定之前,法院和司法鉴定机构来进行这种意见交流的情况在现实中非常少见。“法院来咨询,鉴定机构要把医患双方提供的病历材料全部看一遍,这就要投入时间和精力,但是又不能去收鉴定费。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是,鉴定机构如果告诉法院,瑕疵不影响鉴定,而最终结果又是医院不承担责任,患者就会把怨气转移到鉴定机构。通常鉴定机构是不愿承担这种风险的。你可以去问一下北京市司法局司法鉴定管理处,每年可以收到多少患者的投诉?”
无法知晓东城法院有没有和中天就病历真实性问题展开交流。东城法院以“案件仍在审理中”拒绝了本刊记者的采访。中天司法鉴定中心的谢和平主任则说得很简短:“我们只对双方都认可的材料来做鉴定,材料双方有争议,我们的鉴定只好中止。”自2009年9月医学会出终止函之后,2010年11月4日东城法院才给中天去函要求鉴定。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东城法院一直没有开庭,只有过几次询问。“在我的记忆里,原被告双方都到场只有一次。其他都是单方询问,我们接受询问比较多,同仁去的要少一些。询问过程中,法官只是听取我们对病历的意见,但不会给出判断。”杨律师说。而双方不在场,就无法完成“质证”,也就不能达到质证的目的——帮法院来确定证据。在这段时间里,杨律师也曾多次向主审法官刘宏凯询问案件进度。在杨律师的工作记录上,就有这样的显示。多数情况刘宏凯的答复都是“按照程序,需要请示领导”。2010年3月之后,杨律师就不再写记录,“因为通话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案件没有进展”。同样在这段时间中,杨律师还在做王宝洺的工作。“他的确有一种想法,不愿意去做鉴定,认为病历存在缺陷,法庭就应该直接判了。我就对他说,那第二类技术层面的问题,一定要通过鉴定才能有定论。”
不管是请示领导、自行判断还是与中天交流后再做判断,法院对于病历真实性的认定意见应该体现在2010年11月4日致中天的委托鉴定函中。但是这张不到半页A4纸的委托函只有寥寥几句话。“我摘抄了几个要点,一是‘原告认可被告提交病历的真实性’,二是‘被告认为病历中部分签字非医生本人签字’,三是‘原被告病历对比存在不一致之处’。”杨律师说,“等于法院还是没有做出认定,到底以哪些材料作为鉴定的依据。”
并且对“原告认可被告提交病历的真实性”的表述,杨律师也认为不够确切。“在2010年11月2日的询问中,我们明确表示过同仁医院提交的主观病历中的病程记录,都是事后伪造的,内容不真实。”杨律师今年7月份才接到中天的电话,去那里看到了致函。也许直到那时,中天才要开始着手处理王宝洺的病历鉴定。“每个司法鉴定中心,都有多起案子在排队。在召开医患双方、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和临床专家都在场的听证会之前,排队时间和交齐材料的时间没有严格规定。听证会后,委托人要签订司法鉴定协议书,之后才有要在30至60个工作日完成鉴定的要求。”杜主任向本刊记者介绍。也是在看了那封致函后,杨律师又打电话给刘宏凯,要求“以原告提供的病历材料为准”。王宝洺认可的材料,只有当初从医院复印的客观病历部分。
9月14日,也就是血案发生的前一天,同仁医院的法律顾问金小兵接到了法院的电话,对方询问能不能仅用王宝洺提交的材料来做鉴定依据。“我当时在外面出差,说要回去征求一下同仁的意见。以同仁现在的意思看,仅拿客观病历来鉴定,没有包括病程记录在内的主观病历,鉴定材料是不完整的,因此不能同意。”金小兵对本刊记者说。
绝望袭来
诉讼开始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王宝洺为了能够打赢官司下了很多工夫。在杨律师保存的卷宗材料中,就有王宝洺写的医疗纠纷陈述书,和一份细致的关于各项损失的计算赔偿过程和结果。王宝洺想象医学会鉴定会有一个患者陈述环节,陈述书开篇就是“感谢各位专家百忙之中参加我的医疗事故鉴定”,其实鉴定程序里根本没有这项。在1700万元的索赔中,他算出徐文应该赔给他50万元。但即使徐文在手术中有责任,那也是职务行为,她本人不用做出赔偿。“况且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写这些都不太必要,鉴定结论出来后律师都会帮他仔细核算。”杨律师说。龚美华告诉本刊记者,王宝洺还给北京市卫生局等很多机构写过信,都没有任何回音,“我们不会用电脑,那些材料是他手写的,然后再拿到打印室让别人给敲出来”。
“王宝洺的情绪还是忽好忽坏,我感到他常在希望与绝望中不断摇摆。”王宝洺的姐姐则见过弟弟最阴暗的时刻,“一提起这个官司的停滞不前,他就暴躁、发怒,虽然不能正常说话,但还要声嘶力竭地向我表达。他对我讲,他现在哭都没有声音,他的心一直在流血。”王宝洺曾经自己去过一次东城法院。“他的书包里放了一把菜刀,但是过安检的时候没有通过,书包就存在门口储物柜里。“我提醒过法院,要对他的情况予以重视。”杨律师告诉本刊记者。
血案发生前,杨律师给王宝洺打过一次电话。“我向他复述了一遍我之前和法院通话的内容。”杨律师说。按照之前媒体的报道,法院在电话中回答,律师如果做不通王宝洺的工作就叫他去找法院,法院医疗纠纷案子很多,也正在努力争取开庭。“我安慰王宝洺一切都在按程序走,不要急。电话那端的王宝洺也显得很平静。”杨律师说。王宝洺挂了电话离开家的时候,龚美华正好因为崴脚在卧床休息,否则她绝对不会让王宝洺单独出门。事后回想起来,龚美华后悔那天没有仔细看一眼王宝洺的状态就让他走了。“晚上派出所的人打电话来说天气凉了,叫我们去给他送一双袜子。我才醒悟过来,他是光着脚穿着凉鞋走的。他当时应该十分恍惚。”龚美华当然也没注意到,厨房里的菜刀又不见了。
在那一天,王宝洺没有再选择东城法院,而是去了同仁医院。■
新浪独家稿件声明:该作品(文字、图片、图表及音视频)特供新浪使用,未经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转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