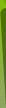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 对话作家王跃文:文学是良心,不是玩具(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01/24 18:24 南方周末 | ||
|
□本报驻京记者 夏榆
1992年,王跃文从湖南溆浦县机关调到怀化行署工作。 怀揣着“学而优则仕”的梦想,王跃文一步一步走上仕途,从一个乡村教师成为一个谙熟官场的小科长,一个敬业勤勉的“机关秀才”。其时,在王跃文的身上,具备了一个政府机关小公务员的全部特征:诚惶诚恐,兢兢业业。使王跃文的仕途发生改变的是1999年他的长篇小说《国画》的出版。这部被称为开创了“反腐小说”先河的小说,因为逼真地描写了“官场”的某种现实情状,成为鲁迅先生命名的那种“谴责小说”,也成为当时最热销也最具争议的小说。《国画》一出,洛阳纸贵,仅盗版就不下10个版本,印数在200万册以上。也因为《国画》的行销,社会上有些人开始和《国画》里的角色对号入座。王跃文被批评“小说可能过于渲染了官员腐败,夸大了官场黑暗”。《国画》出版以后,王跃文从文坛消失。开始是云游,在昆明、建水、大理、丽江漫走,云游之途念念不忘洗心革面,超度新我。云游之后,他关闭手机,在南方某市的一个偏僻角落,租一间三楼的民居埋头写小说。王跃文属于那种在任何环境中都可以创作的作家,不需要挂上黑窗帘,不需要酒精和尼古丁。甚至,也不需要爱情。但那段时间他的写作却异常艰苦,他要努力让自己气定神闲,此前万念,皆若浮云。不停地写,累了就睡,饿了就吃。房间没有暖气,冷得刺骨。只好端着手提电脑,坐在被窝里写。床松松垮垮的,老吱吱地响。 他写出了《亡魂鸟》,似乎是作家的自况写照:一个名叫陆陀的准流亡作家,处在四十岁的边缘,在孤寂中静静地等着自己发疯。他的读者,一个自称残疾而并未残疾,名叫维娜的美丽女人。两人相遇。在小说中有两个声音开始叙述。陆陀叙述他和维娜之间那种扑朔迷离最终却生死相隔的爱情。维娜叙述她铭心刻骨又令她神魂俱碎的初恋。爱情,死亡,金钱,毒品,政治,情欲和变态,畅销书里该有的元素这本书里都有。看上去王跃文再一次重复了作家赚取读者眼泪的烂熟技巧:愈是美女就愈要让她不幸。但是写到最后,王跃文还是忍不住划破了爱情的糖衣,透出他看到的现实的底色:隐在面具之下的地方官员,滥用的权力对人的戗害和掠夺。这一次,王跃文让读者读到的,依然是一本政治寓言。 2004年11月的时候,随着44集电视连续剧《龙票》在央视的播出,王跃文新的长篇小说《龙票》也同时出版发行。那是他枯寂的写作生活结出的硕果。在荧屏古装剧尤其是清朝剧泛滥的时候,《龙票》的严肃风格使习惯了娱乐和戏说的观众感觉冗长和烦闷。虽然《龙票》试图吸引更多的观众,扩大收视率,以收回它的巨额投资。但是晋商们富可敌国的封建庭院和窥视天下的野心,以及隐藏在这类特殊群体心底的人生感悟和他们智慧与财富背后的生动故事,对更多的电视观众是生僻的。最后《龙票》的收视结果还是证明了它的播出依然是一次寂寞的发声。 但是《龙票》还是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学者单世联说:“《龙票》是以严肃的创作态度而不是什么‘戏说’的态度去表现晚清历史的,其中当然包含了对晚清这段充满屈辱苦难的历史,对中国商品经济的悲剧命运,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一再被耽误的根源的深刻认识。《龙票》让我们深切感受到阴冷的政治文化。” 2005年1月6日,在电视剧《龙票》播出的风潮散尽、长篇小说《龙票》被遮蔽在浩瀚的书林中的时候,王跃文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国画》:反述现场的风波 记者:当年《国画》引起读者广泛关注的时候,好像也给你带来了麻烦。那时候你的处境怎么样?能讲一些细节和故事吗? 王跃文:《国画》出版之后,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但在我当时所在的单位,情况却十分微妙。很多退下去的省级领导都说写得好,如果再深刻些就更好了。这些老干部认为欠深刻,其实就是说现实情况比我的小说更严重、更复杂。可我能够怎么样呢?欠“深刻”的小说都横招非议,还能怎么深刻下去?当然,小说毕竟不是报告文学,不能要求小说严格忠于现实素材。当时夸张的说法是我们单位的同事人手一本《国画》,可他们多半是偷偷儿看,有的还把小说包上白色封皮。我立即就成了机关大院里的名人,人们同我见面,几乎都会夸我的小说写得好,但背后他们如何说就拿不准了。有人告诉我,一位处级干部自己掏钱买了《国画》,送给某更高级别的领导看,用意有些阴暗。而这位送书人,至今同我见面,仍像我的朋友,话语间对我关怀备至。 记者:你因为小说而得罪了很多人吗?你怎么化解那些压力,怎么面对那种处境? 王跃文:作为一个读者,他有权利从书中读出任何含义,社会学的、心理学的,等等。如果他不愉快,也许是因为他从作品中,看到了某些一直有意不想让自己看到的东西。作品一旦发表,就不再属于作者。晚清时曾有一位少女,因为读了《红楼梦》,口里呼唤着宝玉的名字而死。你能因此追究曹雪芹的责任吗?或者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方:谁在镜子中看到了使他不愉快的影像,他不能怪罪于镜子而把镜子打碎。镜子碎了,他的嘴脸也不可能好起来。相反,他拿碎镜子去照,那嘴脸更可怖。说到压力,也是有的。但压力只是人的感受,你不把它当回事,就没有压力了。所谓得罪人,我也说不清楚。不会有人公开的说我的小说影射了他。也许有不少人看了我的小说不高兴,那只能是两种人,不开明的和不正派的。 记者:你后来在“官场”的出局跟你的“官场”小说有关吗? 王跃文:应该说有关系。个中细节,往后再说吧。 精英的堕落比群氓的堕落更可怕 记者:你可能不愿意接受“官场作家”这个指称,但实际上你的读者对你的阅读就是因为你表现了“官场生活”,你最初的被关注和你现在在图书市场的走红都和“官场作家”这个指称有关。你不喜欢“官场作家”这个说法,除了它简化了你的文学写作,还有别的原因吗? 王跃文:我的确不承认我是什么“官场作家”。我说过,读者如此关注官场,很大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们民族特有的“官本位”文化,民间对“官”即权力的崇拜与窥视。我的作品以官场为题材,只是因为恰好在某种程度上我熟悉这种生活。我想在官场中观照的是人性,是官场人性的异化与挣扎。其实我并不在意评论界或读者口碑上给我的创作贴上什么标签,因为这对创作本身不是个问题。用写作题材给作家贴标签,本来就是件很无聊的事。托尔斯泰既写过《战争与和平》,又写过《安娜.卡列尼娜》,那么他是军事小说家,还是爱情小说家呢?《红楼梦》中写得最多的少男少女的故事,按时下的聪明划分,曹雪芹应该是青春文学作家?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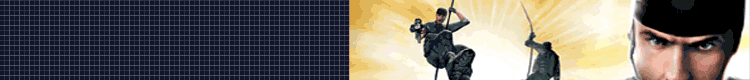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