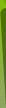| 美女多过三文鱼--20世纪风月史中的小姐(图)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01/24 18:50 新周刊 |
|
过往的中国历史,主要是男人们烩制的一锅浑汤;可是,这中间如果没有当鸡精的女人,味道可就差得很了。当然,三纲五常锁链下的良家妇女是无法充当鸡精的,让历史的浑汤鲜美起来的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游离在一般的社会秩序和特定的夫权之外,享有一般妇女不曾享有的自由。 赛金花本来在当时的中国士大夫中名声很是不好,因为他“老公”洪钧虽是状元,却是个糊涂虫,出使俄国,稀里糊涂地把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送给了人家。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其统帅德国人瓦德西把赛小姐拿过来受用了。赛小姐在天天啤酒、香肠的老瓦手上一过,中国人回过味来了——敢情是块宝哎!为她不知写了多少诗、填了多少词、唱了多少戏、编了多少传说。赛金花作为20世纪中国第一个出名的小姐,其与政治人物的复杂关系、身世的传奇性、无数的绯闻,实在是很具代表性的。 大凡玩弄政治的男人,一般都会热衷于玩弄女人。比普通高级嫖客“档次”更高的是那个时代的“党国要人”,比如立法院长孙科与蓝妮。蓝妮小姐的本来职业就像《日出》中的陈白露,虽然侧身于风月场合,却也是气质非凡。那时,“党国要人”上班在南京,过周末却是流行在上海,蓝妮实际上就成了孙科的周末情人。 不要以为一部20世纪中国风月史,就是小姐给政治强人的经历当点缀的历史。文人们也需要小姐激发他们的灵感、丰富他们的生命。小说家郁达夫是那种不喜欢道学家嘴脸的人,他公开宣称自己喜欢在30多岁40来岁、倚街而卖的“小姐”身上寻找沧桑、悲凉和颓废的感觉。 上海的高级嫖客们把小姐们的营业所叫“长三”、“书寓”,或者就叫什么“斋”——让那些把自己的书房叫什么“斋”的读书人好没劲。入得斋来,是不像周星弛那样立刻眼睛发直的,要有二分的儒雅书生气,二分的艺术细胞,二分的视金钱为粪土,二分的解得风情,外加二分的风流倜傥。 其实,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小姐文化”是“嫖客文化”和西方社交文化的畸形混合物,随一个地方西化程度之高低而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中国的电影电视中,往往让那个时候的小姐一律烫螺丝卷头发,以凸显“风尘感”,其实是大谬不然。 历史在1949年翻过了极其重要的一页。纯洁化的政治取向,连服务业都不承认,遑论流着封建主义脓汁、长着资产阶级大疮的小姐们所依赖生存的产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上海国际饭店门前的鬓香衣影渐成往事,只在阿拉们的回忆中散发着芬芳。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小姐作为一种城市边缘性群体又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开始,她们出现在胡晓阳的密室里和新派作家的小说中;后来,舞厅、咖啡馆、酒吧为她们的生长提供了日益肥沃的土壤。她们或站在当时为数很少的涉外酒店的门口,或在一个城市通常心照不宣的某个准红灯区昏暗的路灯下徘徊,把希望交给老外、港客和崭露头角的大款。因为公安打击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力度很大,因为城市人不可以在本城住旅馆,出租车狭窄的后座曾经作为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发生的场所。 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很多海外研究者的眼中,是中国经济真正起飞的时候。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于是,我们知道北京某女主持人在酒店的被窝中与某著名男人演绎真理(钱钟书先生说,真理是赤裸裸的),事发以后,名声大噪,香港某著名媒体很快请其加盟(这就有点赛金花的意思了)。另一些不怎么出名的小姐们开始让首钢的老总倒了一茬又一茬。王宝森消费小姐时的“吃相”,告诉我们什么叫“阶级异己分子”和“变修”。陈希同大概不会知道孙科和蓝妮,但他让情人把自己的生活也弄得糜烂起来。成克杰跟克林顿一样出身贫寒,可阿克没有为莱温斯基去贪污受贿几千万。胡长清开会间隙千里飞去会小蜜,浪漫谈不上,疯狂倒还是远胜前人。蒋红艳凭色相从仓库管理员一路做到副厅级。和权力同床共枕,是小姐们乐意干的事,但风险从来都很大。 作为客观存在,今天的小姐消费和消费小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已经是个“产业”,温州、合肥等地曾试图收税,说明有关人士早已注意到其中的现金流量;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社会组织的解构与重组,因为它所构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管理这种关系的机制都已经让传统社会茫然失措;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是非主流文化的泛滥,某种文化企图提供让全社会都心服的范本已经被证明是徒劳;从城市学的角度看,是一种城市生态的辐射,它示范的生活方式让很多人砰然心动。当然,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是现代化过程中无法断然剥离于社会肌体的一个侧面。 所以,当城市的高级会馆开张,按金凯瑞的说法,“美女多过三文鱼”。你我的心情用不着骚动。 (责编:幽山)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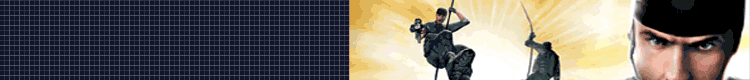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文化 > 人物往事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