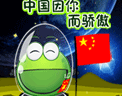巴金:生命艰难地延续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10日21:38 中国网 | |||||||||
|
李辉 1 巴金是长寿的。到2003年11月25日,他将度过99岁生日,按照中国传统,这也是百岁华诞。从1904年走到今年,巴金跨越两个世纪,生命的行程整整走了一百年。在中国作家
长寿是一种幸福,然而,病魔折磨下的长寿却是巴金的痛苦。 生命的延续极为艰难,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巴金幸或不幸,在承受痛苦中走到生命的第一百个年头。 巴金早年身体多病。十四岁时,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刚刚一个月,就因病辍学。1925年,他到北京曾想报考北京大学,却被检查出有肺病,不得不放弃。肺病在当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巴金的亲戚或友人中,就有多位因肺病而英年早逝。这就难怪在巴金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写,并且因患病而发生情绪、思想的变化。《灭亡》中的杜大心、《寒夜》中的汪文宣等都是如此。写《灭亡》时正是巴金治疗肺病与休养的关键时期,主人公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杀军阀以解脱痛苦的念头。 肺病痊愈后,巴金的生理机能却出奇地好。虽然七十几岁时,巴金已经步履蹒跚,言谈乏力,同另外几位老人比他年长或稍小的作家相比,如夏衍、冰心、施蛰存等相比,要明显衰老。但这只是外表,除走路、说话困难之外,他的记忆、思维一直非常出色。而且,我注意到,从1982年第一次见到他,十几年里,他的样子外表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说话声音越来越小,气力越来越弱而已。他一次又一次闯过难关,一次又一次挺过来再次拿起笔,一直到1999年病危时被插气管抢救,他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 生命艰难地延续着。因为有优越的医疗条件,有爱戴他、尊重他的医护人员精心周到的治疗与照顾,同时,更在于巴金有良好的身体机能,有超出常人的承受痛苦的坚韧精神与顽强的生命力。 生命在病房里延续。自年过九十之后,疗养院和病房就渐渐成了巴金最后的家。在新的家里,巴金感受着家人与医护人员对他的爱,也承受着痛苦,在痛苦中继续着回忆、写作与思考。 “把心交给读者。”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这是巴金晚年的心愿。这也是他的自信。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永远与作品同在,与读者同在。 陆正伟先生作为晚年巴金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他一方面为巴金拍摄了大量生活照片,一方面还为巴金读报、读刊物。从他关于病中巴金生活的记叙文章,我们了解到巴金每当听他念文章时,随时会发表评论。他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关注着时事,关注文坛。 病中的巴金还是一团火,用他的真诚用他的爱感染读者、感染周围的人。每当看到有哪个地方受灾,第二天就会吩咐家人到邮局去,化名给受灾地区寄钱。对“希望工程”,资助贫困孩子念书,他也有着同样的热情。1997年夏天,当上海文艺出版社将巴金、柯灵等人的签名本拍卖所得款项资助一所贫困地区的小学时,巴金欣然用颤抖的手为学校题写校名---石关希望小学。几年来,他到底给多少次为受灾地区捐款、为贫困学生伸出援助的手,家人没有统计过。他用的化名,使收款人绝对猜不出汇款人就是这个写出《家》《春》《秋》、写出《随想录》的巴金。 对于巴金,想做的就是献出他对这个世界的全部的爱。不求回报,不求张扬。从热情投入社会革命到勤奋创作一生,从捐款十五万元倡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到不间断地资助贫困学生,他都在奉献着自己。用他半个多世纪前所说的话来说,奉献是人生的最大幸福。三十年代初他曾这样说过:“让我做一块木柴罢、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射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温暖。”在前几年宣布封笔的时候,他说过:他不能再写作的了,但他将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一生追求,来证明自己的心永远与读者在一起。在人们眼里,巴金这样说,也正在这样做。 2 1997年,我到杭州去看望在那里疗养的巴金。我发现,尽管九十三岁已过,巴金思路之敏捷、记忆之清晰仍然让人吃惊。试试他的手劲。左手明显强过写字的右手,用力紧握,居然让人还有一种痛感。不过,他说他气不足,说话困难,很痛苦。他思想,他回忆,苦于气力不足,无法把内心里的话说出来,无法毫无障碍地与人们交流。交谈时,看得出来他的思维走得很快,他能敏锐抓住你所讲述的较为深入的问题,并很想表达出来。可是,只见他嘴唇颤动,想说的那句话却迟迟说不出来。对于一个一辈子愿意将心交给读者的作家来说,这恐怕是最无奈的痛苦。 “气不够,气不够。”巴金反复说。见大夫为他喂参汤。我宽慰他说:“不要着急。你看这不是在给你补气吗?”他微微一笑,却又分明表示他明白我的话是一种安慰。 我是在9月初在苏州大学参加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后,专程来到杭州看望巴金的。苏州大学即过去的东吴大学,巴金的三哥李尧林曾在那里念过书。我告诉他,苏州大学将东吴大学的校园建筑保护得非常好,一个秀美、安静、值得苏州为之骄傲的校园。他马上接过话说:“我去过。”我问住了多久,他说住了两天。我又问:是什么时候?他说是在去法国之前。他去法国是在1927年。1927年到1997,整整七十年,但他却记得这样清楚。 去看望巴金的那天,我和两位朋友刚刚到烟霞洞喝过茶。我告诉他,胡适当年曾在那里住过几个月。他则说:“刘师复的墓……”只有这几个字,但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刘师复的墓也在烟霞洞。巴金曾在文章里写过,当年他第一次到杭州,便到烟霞洞祭扫过他所敬重的刘师复这位中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我又一次问他是什么时候到烟霞洞,是二十年代到法国之前吗?他明确地说:不是,是在1930年,从法国回来之后。 令人高兴的记忆力。一次难忘的交谈。 我将讨论会的情况向巴金做了介绍。自1989年以来,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气氛越来越活跃,宣讲论文、讨论、甚至辩论,真正开始了一种学术与心灵的交流。听了这些介绍,巴金没有说别的,只是说了一句:“要实事求是。”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讲这句话。我理解,正如他这些年反复强调的“讲真话”一样,他也希望对他的研究,立足于实事求是,不切实际的推崇或粗暴的批评,都是不可取的。 谈话中,我们提到了巴金在“文革”所写的交代。巴金的女儿小林说有很厚一摞。我便说,应该整理出来。的确,巴老一直为建立“文革”博物馆而疾呼,他把这作为反思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以后的人们大概会因为他提出这一建议而永远记住他。我想,类似于他的交代这样的历史文献,是应该加以收集与整理的,并且应该尽可能使之出版。我对巴老说:“其实可以将它整理出来,如果出一本书,会有很大价值的。”他马上反应说:“等我死了之后再出。”思维的敏捷顿时表现出来。我又说:等哪天精神好的时候,可以先为这些交代写几句话放在那里。他点点头,表示同意。 一年之后,我又向巴金提到他的”文革”交代。他还是说,等他死之后再发表。我说趁现在身体还好,写一个序,哪怕几句话也行。我和小林都这样试图说服他。他说:“我考虑考虑。”第二天去问他,他还是执意不允。他说我:“你性子怎么这么急?”我笑笑,说:“我哪有你的性子急?有时候你急起来可比我急得多。”他说:下次你来再说吧! 谁料想,随后不久他的病情便加重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件大事一直萦绕巴金心中。自1986年在《随想录》中提出这一构想以来,巴金并不是像有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很快就放弃了这一构想,退缩到只顾编辑个人全集的避风港之中。没有,他从未放弃过个人的努力。 1995年6月23日,巴金在杭州的疗养住所为《十年一梦》增订本新写了一篇简短的序: 十年一梦!我给赶入了梦乡,我给骗入了梦乡。 我受尽了折磨,滴着血挨着不眠的长夜。多么沉的梦,多么难挨的日子,我不断地看见带着血的手掌,我想念我失去的萧珊。梦露出吃人的白牙向我扑来。 在痛苦难熬的时候,我接连听到一些友人的噩耗,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的。梦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我不是战士!我能够活到今天,并非由于我的勇敢,只是我相信一个真理: 任何梦都是会醒的。 这是年过九旬的老人再次发出的声音。这一年,“文革”爆发即将三十周年,多少人沉默着,也有人还在用所谓新的理论来寻找“文革”的好处,但巴金依旧在反思,在呼吁,在提醒人们切勿忘记历史血的教训!难道我们还能要求九十岁的老人做得更多吗? 就在同一年,老朋友、翻译家草婴来看望巴金时,带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他就是编写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的杨克林。杨克林带来他收集的一部分“文革”资料图片,巴金坐在轮椅上认真地浏览。杨克林在这本图录的后记里写到,巴金对他说:“这件事应该做,“文革”博物馆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巴金不仅答应将自己写于1986年的《“文革”博物馆》一文放在书首,还用颤抖的手为画册题词:“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杨克林后来感慨地说:“这是一位伟大的哲人发自心底的声音,是我们民族自信的表现。”草婴担任大型画册《“文革”博物馆》的顾问,他在序中这样写道: 当然,纸上的“文革”博物馆不能代替收藏实物的博物馆,但在正式的博物馆建立之前先有一部这样的大型图录,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也因为这个缘故巴金对这部图录的问世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对编著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深信,编著者所获得的感激决不止是巴金一人,因为,炎黄子孙将由此了解“文革”真相,防止神州大地重演这样的历史悲剧,其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大型图录《“文革”博物馆》分为上、下集于1995年年底出版,收录了数千张历史照片,这是我所看到的迄今为止关于“文革”历史的资料最齐备、叙述最有力度的著作。这无疑是晚年巴金高兴看到的一项重大工程。 1998年10月17日,还是在杭州,又走来专程从美国来探望巴金的方女士。方女士给巴金带来的礼物,是画册《“文革”博物馆》的日文版。方女士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与巴金商讨该画册的英文版的翻译与出版事宜。此时的巴金,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激动地听方女士讲述关于这本画册的一切。他落泪了,他着急地想说些什么,但却难以表达。最后,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一激动就说不出话。” 不必再说。一切巴金都早已表达出来了。几个月后,1999年2月,巴金又一次病危,他被插气管抢救。经抢救,他又一次活了过来,但说话已极其困难。因此,与方女士的见面,或许就是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最后一次交谈。 3 躺在病床上,重温友情,也是支撑巴金生命的另外一种动力。 一个人能够被他人怀念是一种幸福,一个人愿意怀念他人同样也是一种幸福。对于巴金来说,友情从来就是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他说自己很痛苦,但实际上,这种回忆友情的过程,对于他又未必不是一种慰藉。一个老人,能够动情地怀念故人,写出温馨动人的文字,这该是一种难得的快乐。尽管写作过程常常显得艰难而痛苦。他说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文章要写,却力不从心。字越写越大,手也抖得越来越厉害。1998年3月,巴金用了几天时间,给萧乾写了一封信。一百多个字,写了满满四页纸。这是目前所见巴金病重前亲笔所写的最后一封信。萧乾当时住在北京医院,原件意外丢失,幸好小林保留了复印件。病中的萧乾,为信件遗失而耿耿于怀。几个月后,萧乾逝世。 尽管早就说过要封笔,但是,巴金却从来没有做到。像他这样一个把创作视为生命的作家,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是不可能放下手中的笔的。1997年,他完成了译文全集的所有序跋,接着对曹禺的怀念,又占据了他的心。 1998年年初,我去上海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他说他正在写一篇怀念曹禺的文章。说是写,不如说是“说”。他写字很吃力,只得每天口述几句,由女儿小林记下,再念给他听,加以补充。他用了两个星期时间,刚刚完成前面一个部分,大约几百字。他说还要继续写下去。 一个月后,再去看望巴金,他已经完成了这篇《怀念曹禺》。似乎想说的话很多,老人留恋的往事也很多。令人惊奇的是,靠每天一句一句续写而成的文章,仍如他过去的作品一样浑然一体,流淌着动人情感。还是那种真诚,似乎平淡的表述,却又分明有着意犹未尽的深沉。读它,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位九十四岁高龄的老人,思想还依然活跃,还在用笔倾诉着心中的感情。 写完这篇《怀念曹禺》,巴金还想继续写下去。他告诉我,1998年是郑振铎遇难四十年纪念。几年前他曾经开始动笔写怀念郑振铎的文章,可是一直没有完成,他想在这一年继续完成。1922年,巴金生平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是在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旬刊》上,这让他终身难忘。然而,已经动笔的这篇文章,再也没有写完。这样,《怀念曹禺》也就成了从事写作将近八十年的巴金最后完成的作品。 1999年2月,巴金的生命又到了一个转折点。 从事多年文艺报道、与巴金熟悉的新华社记者赵兰英女士,在一篇通讯中详细记叙了巴金这个月的医疗经过: 1999年2月7日,是大年初一,市领导要来给巴金拜年。前两天巴金有点感冒,心内科崔主任不放心,一大早赶来,仔仔细细为巴老检查了一遍。不料2月8日清晨,巴金的体温上去了。医院立即组织抢救小组,经过会诊,认为巴金是因呼吸道感染引发高烧的。当晚20时,巴老的体温达到39度,呼吸衰竭。23时,抢救小组为巴金在气管处插上管子,通过呼吸器将痰吸出来。第二天,巴金被转入重症监护病房。2月14日,医院为巴金在喉管处作了手术,以帮助吸痰。22日,又发现巴金心律失常,心衰……就这样,几度垂危,又几度冲越过去,巴金在抢救室度过了20个令人心焦的昼夜。3月1日,巴金转回病房。这时,久未开口的他突然说道:“谢谢大家!我要为大家活着。”这次抢救后,巴金基本上只能直躺在床上。 生命在无奈中、痛苦中延续。 巴金不愿意这样经受痛苦的折磨。他不止一次要求停止抢救,他一度拒绝为他做喉管手术,甚至请求让他安乐死。然而,他已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躺在病床上的巴金,生命的延续该付出多少代价。不只是个人生理上的痛苦,更有精神上的痛苦。他既然无法辞去一个又一个社会职务,也就得继续由别人以他的名义发表并非属于他自己的声音,也就必然要承受由此而带来的某些误解甚至非议。 每当注目躺在病床上忍受病魔折磨的巴金,我心里真的有一种悲凉。 无法避免的现实。三十年代时,巴金就反复地说自己是一个矛盾的存在:“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七十年后,巴金还在重复着自己的过去。只不过如今他面对的是另外一张网,经受的是另一方式的束缚而已。 且让我们用充分的理解来为病中痛苦的巴金祝福吧! 且让我们以冷静的心态、思索的目光,凝望百年行程中用自己坚毅的步履艰难行走的巴金吧! 在即将迎来巴金百岁华诞时,我们会为他送上鲜花,为他唱一首《祝您生日快乐》。对于巴金,我想,他需要的不是铜像,不是大张旗鼓的庆贺,不是漫无边际的赞颂。更该做的事情是将他放在应有的、恰如其分的历史位置上,用更加客观、更加冷静的态度来分析他,来描述他。 这一个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变化最为迅疾的百年。百年间,晚清、民国、共和国;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思想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朝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在百年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的容颜,他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里,没留下多少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汹涌奔泻,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涌动,听见不息的回响;有的如潺潺溪水,没有引亢高歌,也非恢弘壮观,但它执著,它坚韧,在起伏跌宕中流淌…… 百岁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历史画卷中。 我很难用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如激流;有时又如阴云,如浓雾,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了一百年。他为百年中国创造的一切,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 百岁巴金属于百年中国。百岁巴金也将属于未来。 2003年8月,北京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巴金逝世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