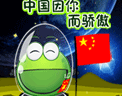关于“巴金迷”的历史回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10日21:48 中国网 | |||||||||
|
丹晨 一九二九年,巴金带着他的中篇小说《灭亡》走进了文坛,由此引发了一场文学“冲击波”。许多读者对着这个陌生的名字,好奇地探问道:“巴金是谁?” 发表连载这篇小说的《小说月报》是当时历史最久、影响最大、销行超过一万多份
到了年终,《小说月报》编者叶圣陶又一次高兴地总结说:一九二九年这个年度里,该刊发表的巴金的《灭亡》,老舍的《二马》是两部“很引起读者的注意,也极博得批评者的好感”的作品,并预言“他们将来当更有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同前,十二月号)这个预言后来得到了应验。许多批评家发表评论,认为是少见的优秀作品,“轰动当时(1929年)文坛的杰作,当首推《小说月报》上登载的巴金的《灭亡》”。(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书局1933年版)“在怠惰和疲惫的状态下支持着的文坛上,近年来只有巴金可以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一个。”(《1932年中国文艺年鉴》,现代书局1933年版,上海)有一位青年读者给《开明》杂志写信说:“这部书(指《灭亡》)实在有激动人心之效”,自己原有的享乐主义被它打消,“情愿去为大众工作”。(《开明》杂志第2卷第20期) 现在人们都已知道,当初巴金写作这部小说时,并没有想到借此走上文坛当作家。他那时正热中于做一个革命家。因为革命跌入低潮,无政府主义运动正趋于分化、衰落,他深感苦闷。因此,他一再说:“横贯全书的悲哀,却是我自己的悲哀,固然我是流了眼泪来写这本书的。”“我是为了自己,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为了倾诉、宣泄自己的苦闷,常常在笔记本里陆陆续续写了些互不连贯的文字,然后整理改写成这部小说。他仍然想像过去写的那些宣传无政府主义译著那样,准备自费出版,仅此而已。他托在国内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周索非,代为将他已译成的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费,用作印刷《灭亡》一书的费用。周索非看到这部书稿后,却自作主张推荐给当时正在主持《小说月报》编务的叶圣陶。叶十分激赏,决定采用发表。就这样一个偶然因素,使巴金的人生道路有了一个转变,从做一个革命家的梦,改为文学之梦,并将执着追求的人生信念和汪洋恣肆的激情,倾注在文学写作之中,从此写作了一辈子。 因此,从《灭亡》这个作品的创作和它后来产生的社会效应来说,最主要的是巴金用自己的真挚感情点燃了当时青年的心。他所倾诉的苦闷,他描写的杜大心的悲剧,恰恰正是表现了时代的苦闷,才会激起如此众多的青年读者强烈的共鸣。 巴金沿着这样一条创作路线,继续写作了《新生》、《海的梦》、《爱情的三部曲》等等大量有影响的富有浪漫激情的中短篇小说;同时又创作了以《家》(1932年)为代表的写实主义长篇小说。后者既保持了原有的酣畅热情的笔触,又更注意人物性格和潜在内心的刻画,细节的真实生动的描写,在更广阔的历史层面上,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家族史、两代人的冲突、礼教、乡绅、官府、学生运动……)作了相当深刻的揭示和剖析。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十多年了,但在文学领域里,较有分量的长篇小说竟仍寥若晨星(在这之前,1929年曾出现了叶圣陶的《倪焕之》,但若用今天眼光来说,他的字数只能算中篇。稍后,茅盾的《子夜》发表于1933年),像《家》这样史诗式的全景式的批判封建专制、张扬个性解放、呼唤自由民主人道精神的长篇小说,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似乎可以说是第一部。像高觉慧那样一些敢于向封建家庭挑战、决裂,投身创造新世界之路、个性鲜明的新青年的艺术形象也是崭新的,成为现代文学画廊中的艺术典型,使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震。 正是因为巴金夹着这样两类不同的艺术风格、但都具有青春激情和生命活力的作品,来到三四十年代的青年读者中间,引发了一股狂飙似的读书热潮,几乎成了鲁迅以外另一位青年精神导师,尽管这并不是巴金所追求和希望的。 现在我们试着列举一些史料事实: 李健吾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专家,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评论家。他用刘西渭的笔名写的评论文章总是文采斐然,情理并茂。他是巴金的好朋友,1932年就对巴金的作品有剀切的剖析和严肃的探讨。他认为,巴金的作品中表现的“爱是为了人类,他的憎是为了制度。”巴金作品所以如此打动青年读者,是因为“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于是,“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还有比这更需要的!更适宜的!更那么说不出来地说出他们的愿望的!”他喟叹:“巴金是幸福的!”“幸福的巴金先生!”(《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第13、3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银川) 著名诗人臧云远,抗战初期,曾在长沙、武汉参与创办民族革命大学。他曾记述了一段招考青年学生时的见闻:“在这之前(指1938年8-9月间),巴金路过武汉,我请他到法租界‘美的’咖啡馆去吃咖啡。我告诉他,这两个月为了给二战区的民族革命大学招生,我负责口试与几千个救亡青年谈话,内中有一千几百人,说是喜欢文艺的,问他们:‘读过谁的作品?’‘巴金。’‘你喜欢谁的作品?’‘巴金。’差不多是异口同声。可见巴金的《家》在当时是风靡一时,在青年心中,变成了反对封建出走家庭,向往光明的艺术力量了。……”(南艺学报1979年第2期) 这样类似的情景,我从另几位文艺界老前辈那里也曾听说过,仅从荒煤同志那里就不止一次听说过。他在文章中也曾多次写到过:那时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很多不是读了马克思主义,而是读了巴金作品以后,参加抗日救亡,投身革命事业的。他说:“但真正认识到巴金作品的影响,还是1938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招考文学系青年学生的时候。……这些同学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们千里迢迢冒着危险奔向延安,爱好文学,投考鲁艺文学系,……要革命,思想上的许多变化,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心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人民日报1982-6-16) 我也听到过黄源同志的介绍:“抗战初期我在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工作,遇到过很多从上海等城市去的青年,是因为受巴金等人作品的启发,才有了反抗旧社会的觉悟,产生了革命的热情。”(与笔者谈话笔录,1979年) 抗战期间,即使在南海偏隅的香港,也有类似的报道。那是刊登在立报上的一篇短文,题为《关于‘巴金’的话》(方野),说:“昨天(24日)在《言林》看到青年读者君的《巴金的新著?》使我想起巴金先生著作的销路来。在重庆,他的新著《秋》每本卖到七八元,尚被争抢一空!在香港,听说作家作品销路最大的,要算巴金和林语堂两位。巴金先生的著作,对于一般现代青年——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男女青年学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确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也正如读者君所说:“现代青年男女谁个不爱读巴金先生的小说?”(立报1940-12-2) 1942年,评论家王易庵在文章中介绍说:他有一次到苏州去,和当地文学青年颇多接触,明显感到他们对巴金作品的爱好,“口有谈,谈巴金,目有视,视巴金的作品,只要两三个青年集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听得他们巴金长,巴金短的谈个不歇,……”在上海,“《家》《春》《秋》,这三部作品。现在真是家弦户诵,男女老幼,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改编成话剧,天天卖满座,改摄成电影,连映七八十天,甚至连专演京剧的舞台,现在都上演起《家》来,借以多多号召观众了。一部作品拥有如许读者和观众,至少这部作品可说是不朽的了。”他接着分析其中主要原因,和李健吾的看法一样,“是在于他具有丰富热烈的感情,贯穿于他文字中间的是对人间的热爱……”因此引起青年读者“内心热烈的共鸣,……深受青年读者的欢迎了。”(《巴金的〈家。春。秋〉及其他》,上海《杂志》月刊第9卷第6期,1942-9-10) 即使在战乱时期,也有类似情况,请看:“要是你生活在学生青年群中,你便可以看到巴金的作品怎样地被喜爱。尽管大热天,尽管是警报,绿荫下,岩洞里,总有人捧着他的作品狼吞虎咽,上课,尽管老师讲得满头青筋,喉头像火,他们却在讲台下尽看他们的《家》《春》《秋》,有时泪水就冒充汗水流下来,夜半巡宿舍,尽管灯光似磷火,也有人开夜车,一晚上吞噬了六七百面的《秋》并非奇怪。而到书店,口袋里有钱,则唯巴金是问,无管那是好是歹,是散文是小说,无钱,则扫着贪婪的眼光,若是稍不自私的书主,肯把书出借,半月一月后,准是没有了封面。”“这是人们经常挂在他们的口上:反抗家庭的,说是《家》的‘觉慧’,‘觉民’,‘作揖哲学’的是‘觉新’……对于妇女群,她们更落落数得出像‘梅’、像‘鸣风’、像‘瑞珏’……总之,他(她)们记得烂熟,他们谈论得唾沫四射,有如书场争辩《三国志》或《封神演义》《水浒传》的人物和事件。”(林萤聪:《论巴金的家、春、秋及其他》,柳州文丛出版社1943年版) 这些评论家、学者一反平日正襟危坐、板着面孔论道的样子,竟都是不约而同地用那么热情、形象、生动的文字描述巴金迷们的如痴似醉,可见其真实、普遍;也说明评论家、学者们也被感动了的事实。 法国传教士明兴礼博士在四十年代后期,与巴金有过多次通讯,讨论巴金与西方文化思想的关系;1946年还曾访见过巴金。他在他的著作《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中认为:“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转变,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无数的中国人所表演的悲剧。作者个人的经历的叙述,在很多青年的心中引起了共鸣。为什么《家》会有这样大的收效呢?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代表了中国大多数青年的自传。” 他还引述了另一位传教士卜相贤在《中国学生》中的一段记事:“我多次问学生们最喜欢读什么书,他们的答复常常是两个名字:鲁迅和巴金。这两位作家无疑地是1944年的青年的导师。让我看来,巴金对学生们的影响好象比鲁迅先生的更大一些,所以他负的责任也比较重。我常听青年人说,巴金认识我们,爱我们,他激起我们的热烈的感情,他是我们的保护者。他了解青年男女被父母遗弃后生活的不幸,他给每个人指示得救的路:脱离父母的照顾和监视,摒弃旧家庭中的家长,自己管自己的生活。对结婚问题,是青年们自己的事,父母不得参与任何意见。……” 卜相贤与巴金并未见过面,只是作为一个当事人的亲见亲闻,提供的这个情况,是一段非常重要而可信的证词。他进一步证实了李健吾的话。可以看出,当时青年读者把巴金看成可以向他倾诉心事的可信任的导师和朋友,看成愿意跟随他所指示的道路前行的先行者。这就远远超越了对于一般作者的所谓喜爱、崇拜之情。更不是现在有些评论者用一些流行的时尚说法,妄加评论,说巴金作品是“煽情感伤”“抽象夸张”的通俗传奇,是那时传媒、商业社会制造出来的“青春偶像”“社会偶像”云云。 从上面所引述的一些历史资料,我想至少可以有这样几点共识: 在三四十年代,巴金的作品曾经风靡一时,拥有广大的青年读者群,以至曾经影响过好几代青年的人生。他是用自己的思想艺术魅力赢得读者喜爱的。他是用发自内心肺腑的真实感情,与时代共鸣的感情,感染读者的。他用对人类真挚的深沉的爱,去点燃青年读者的心,唤醒他们的良知、人性和爱。 他的感情,无论是悲哀的,感伤的,痛苦的、激愤的……都是鼓舞人向上的,进取的,追求光明的,向黑暗势力战斗的;更希望人们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因此是一种正义互助献身之情,美好之情。 因为他爱人类,爱读者,他也就拥有了大家的爱。他是幸福的!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巴金逝世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