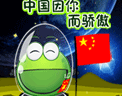我眼中的巴金老人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10日21:56 中国网 | |||||||||
|
李存光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端坐在我对面的高背木椅上,双腿间架放着一根手杖,身着略显臃肿的栗色茄克式棉衣。老人举步维艰,但脸色红润,神态安详。这位老人便是巴金。 坐在老人对面,我真真实实地感到一种宁静,一种镇定,一种充实,一种信任。
这一天是1991年2月4日,农历庚午年腊月二十,节令正当立春。 没有多少热力的阳光,穿过婆娑的树叶,再透过门窗的玻璃,斑斑驳驳地洒进由阳台改成的狭长形房间。房内没有取暖设备。阳光虽未增加多少暖意,却平添了几分明亮。我同巴老便在这样的氛围中谈话。同去的朋友在远处和巴老的九妹琼如老人很有兴致地拉家常。 三天前,我同思和一道去巴老家时,请巴老为我选编的《巴金谈人生》写几句话。巴老应允了,要我再给他一份纲目看看。这天,我专为送纲目而来。老人说:一定写,只是身体不好,可能短一些。我说:哪怕只写一句话也好。说完“正事”,我又同老人谈了些别的事情。老人拿出两件材料给我看。一件是浙江嘉兴县志办公室据1923年手稿打印的《嘉兴杂忆》残稿,另一件是65年前写有《春梦》片断的练习簿。三天前,我同思和在巴老家谈了近3小时,这次,我不愿多占老人的时间,因此,进屋后一直没有取下围巾,脱去大衣。翻看那极其珍贵的稿本时,我显得笨手笨脚。巴老慈祥地看着我,不时轻声说几句话。看着老人双腿间的手杖,身上的棉衣,我突然涌出一个念头:老人那衰老的身躯也需要支持,老人那燃烧的心也需要温暖。我有点走神了。…… 2月5日,我离沪返京。19日,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五,巴老来信。我急切地拆开老人亲笔写的信封,内中是老人一笔一划写成的两页《前言》。文末署“91年2月14日”,这一天是农历的除夕日。《前言》是这样写的: 1928年在巴黎,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只想活到四十。”过了62年,我在回答家乡小学生的信中又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87岁的老人回顾过去,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我老老实实地走过了这一生,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有时走得快,有时走得慢,无论是在生活中,或者在写作上,我都认真地对待自己。我欺骗过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惩罚。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享受。人活着正是为了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将憔悴地死去。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读罢在人生途程中跋涉87个春秋的老人的自白,面对工整而苍劲厚重的手迹,蓦地,我眼前化出一幅景象:在人们忙碌地准备迎接新岁的时候,巴老静静地坐在临窗的小桌前,手中那管显得万分沉重的笔,在纸上艰难地缓缓移动,移动……。我的双眼模糊了。幻象消失了,眼前是实实在在的写着400多字的两页稿纸。放下稿纸,我感奋,我崇敬,只是不知怎地,感奋中含着些许酸楚,崇敬中掺着几分感喟。我默默地对自己说:这就是巴金老人!这就是巴金的精神! 《巴金谈人生》是我为青年朋友选编的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力图通过书中精选的巴老有关人生的方方面面的言论,展现他数十年来所倡导和实践的一贯思想:人应该追求真诚的、充实的、有理想的、有奉献的生活。巴老新写的《前言》所回顾的、所展示的、所渴望的,不也是这样吗?将巴老的手稿复印交出版社以后,我在小书的《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有感而发的话:“最有资格谈人生的人应该是严肃地对待人生的人。巴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怎样说就怎样做,至少是努力这样去做。正因为这样,在80岁的时候,他才能这样说:‘我绝不写文章劝人“公字当头”,而自己“一心为私”。自己不愿做的事我也决不宣传。我的座右铭就是“绝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我们的确见过那种‘论’人生时头头是道,‘过’人生时则背道而驰的人。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与言善行恶、口是心非,其美与丑、高与低,真是泾渭分明。”我向青年读者们建议:“读巴金谈人生的书,还应了解巴金这个人。只有把书和人联系起来‘读’,才能真正认识巴金并理解他对人生所说的话语,受到更大的启迪和教益。对于其他谈人生的书和人,也应如此。” 我同巴老的文字往来始于1963年秋。当时,我刚刚步入大学四年级,准备以巴老的创作道路为题,撰写学年论文和一年后的毕业论文。9月23日,我写信给巴老,一封2000字的信写了一个星期,才交给指导教师林如稷教授,请他转寄给巴老。信写得很稚拙。我说:“为什么我会对您和您的创作感到兴趣呢?凭我有限的知识,我感到,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中,对您的论述和研究还不够充分、全面,有的问题解放前后都在争论,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有的虽然接近一致,但中间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有的呢,似乎还没有怎么触及呢,特别对您的创作道路和经验的研究,显得更加不够。因此,对您的文学活动和创作道路的轮廓,作一个较全面的勾画;对您的作品,作一个合乎事实、较为正确的评价;对您的创作经验和意义,作一个公正的总结,是十分必要、十分迫切的事情。自然,我深知,知识贫乏、能力低下、年仅21岁的我,远远不能胜任这样艰巨的工作,它的完成,有待于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们共同的探索和努力。我愿意在这项工作中,努力尽自己的一点力量。” 我又表示,“读您的作品,我很喜欢您的性格和语言。当然我不是喜欢那些旧时代留下的消极的方面,我指的是由您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家全人的品格。我爱热情、诚挚的人,爱明朗、酣畅的语言,我相信,这会有助于我对您的作品的感受和研究。” 我以十分严肃的态度说:“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才立志研究您的作品及创作道路。我认为,这决不是个人的喜好和事情,对您的研究和评价,实际上关系到正确批判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进步传统,关系到如何掌握评价新文学史上一大批进步作家的标准,涉及到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去对客观事实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我希望通过对您的研究,使自己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刻、具体的认识。” 10月29日,林如稷教授转给我巴老的复信和一本我求借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巴老的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流畅飞动,文句却颇多委婉。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存光同志: 信收到。我最近比较忙,过几天便要离开上海到南方去看看,我抽不出时间写较长的信,请原谅。说实话,我希望您最好不要研究我的作品。我过去写得多,但写得不好,现在社会活动较多,文章写得少,还是写得不好——自己看看,也不满意,何况别人!倘使我将来能写出好作品,我当然不反对人们谈论它。目前我害怕您会白白浪费了您的时间。 您要看的明兴礼的著作,已托林先生转给您了。这本书我这里还有,您不必寄还了。作者是个天主教徒,在他这篇“博士论文”中他也在宣传天主教义。不过他懂中文,我的作品他差不多全看过,引用的地方较多。 我1923年离开成都后曾在上海、南京两处进中学读书。没有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去法国前,翻译过一本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改名《面包与自由》)。 匆覆。此致 敬礼 巴金10月17日 请代问候林如稷先生,我不另给他写信了。我毕竟是一介书生,且悟性甚低,不懂测风察云,见机行事。在1963年秋写信给巴老,表示要研究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并侧面表示对1958年至1959年全国范围内以“巴金作品讨论”为名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的不满,对文学评论和研究中日见抬头的种种“左”的思潮的质疑。这怎么不使心有余悸的巴老感到为难呢?大概是我的书生气令巴老忧虑,因此,他劝我“最好不要研究”他的作品,“害怕”“白白浪费”我的时间。我未能理解巴老的深意,也的确不明白正在发展的形势的严峻,仍然坚持搞自己的选题。以后的事情却为巴老所言中。一年以后,我不得不中止了研究。 风雨雷霆,14年以后,我从西北的一所大学来到北京,得以重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巴老。此后6年间,我只给巴老写过一封信。为了抢回失去的时光,我奔忙于各家图书馆,埋头翻查旧报旧刊,四处寻觅绝版书,整日遨游在书海之中。直到1984年,我出版了一本论述巴老文学道路的小书并编成三卷研究资料后,才下决心去见巴老。12月3日,在巴老度过80岁生日之后,我第一次走进上海武康路巴老寓所。我带去一份复制件,这是上海《大公报》副刊《大公园》1948年12月29日以《巴金的心境》为题刊登的两行手迹:“我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战斗,这是支持宇宙的两根支柱。”手迹中的“一句话”三字有脱笔,看不清是什么字,令我耿耿于怀,因此,趁便先请巴老和小林同志辨认一下。为了节省巴老的时间,赴上海前,我将要请教的问题寄给了巴老;见面后,巴老便针对我的问题逐一作了回答。谈话的主要部分如下: 存光:1979年4月和1980年初,您在同法国《世界报》记者雷米和上海文学所研究生花建的谈话中,都谈到“追随鲁迅的道路”。我正在思考应该怎样理解您所说的“鲁迅的道路”。能否谈谈您在30年代对“鲁迅的道路”的认识,以及今天您对“鲁迅的道路”的看法? 巴金:你的问题我看了。老实说,你的问题我很难回答。作家与批评家、理论家是不同的。有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关于“鲁迅的道路”,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真话集》中《怀念鲁迅先生》写过。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对鲁迅的看法,当然也是这样,不过现在到写这篇文章时,考虑这个问题就考虑得更清楚一点,更明确一点。我认为作家的道路就是这样的,写文章也这样写。我觉得鲁迅的道路首先是这样的。比如讲真话,我是这样写的:写作和生活一致,作家和人一致,人品和文品一致。写这篇文章时虽说是回忆,但鲁迅对我的影响,我对鲁迅的看法就是这样的。30年代、40年代,我不是这样明确,70年代、80年代,更明确了。 存光:现在回过头来看,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对您自觉从事创作是否有什么影响? 巴金:我觉得很难明确地说。当然受到影响,但创作主要是生活。明确的我说不出来。我不是有意的。搞创作,写什么东西,主要是生活里有一些感受。所以我说我不是文学家。……我对青年作家说,你写创作,不要管别的,理论也好,美学也好,什么也好。你写生活中的感受,最熟悉的东西,感受最深的东西。我自己写作也是这样。反正我也不要做作家、文学家。 存光:您认为对于作家的社会理想、政治观点与小说的思想的关系,应该怎样认识才较为确凿? 巴金:这是有关系的。我的作品与我的主张是有关系的。我写作品是宣传我的思想,宣传我的看法。写出作品要打动我,也打动别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我没有话可说就不写东西了。 过去有些东西是别人拉稿写的,现在也有拉稿的。要尽量避免。替别人完成任务,要你写什么稿子你就写什么稿子,是浪费时间。 存光:您认为写一个作家的传记,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巴金:我觉得写一个人的传记,最重要的是你了解他的生活,还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时代最重要,背景、环境最重要。我不想别人替我写传记。我写过去,也需要好些时间来思索,来回忆,才能准确地回忆起来。我写《回忆我的哥哥李尧林》在香港的《大公报》发表后,《一般》杂志也转载了。这篇文章里就有错,时间和事情都有错,查了几篇东西,才搞清楚,收在《病中集》中的是改过了的。 我写东西要有根据。我要写过去哪些事,要考虑哪些问题,也要花好多时间,不能说几十年的事一下就想起来。我的时间不多了,把要要写的东西多写两本,还有,我还要做点事,证明自己的文品、人品,证明文学与生活、与写作的一致。因此,我没有更多精力来写回忆过去的东西。我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事,不能老做别人让我做的事。 存光:有人说,写传记要写出“我眼中(或心目中)的×××”;又有人说,应写出“真实存在着的×××”。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巴金:照我来看,当然应该写真实存在的人。但这不容易,总免不掉我写的东西总有点我自己的看法、印象。比如这个人我讨厌他,写出来总有点反映。他做的有些事你不赞成,你总不可能把他说好。当然,写作时尽可能准确些,忠实一点。过去写传记最困难是材料,我为啥要提出建立文学馆呢?就是为了保存材料。这个馆明年一月一日可以正式建馆。成立文学馆还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成为研究中心。我的意思,先应该是资料中心,收集资料,整理资料,提供资料,主要为全国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服务,还要为海内外研究者服务,为很多人服务。研究中心是为少数人服务。以后发展当然可以办。写传记有了资料也就方便一些。本人谈的只能参考,特别是家属,现在有些回忆录就不大符合事实,家属提供的情况好话说得太多。最困难的是时代怎样创造这个人,能把时代写出来。这个时代出现这个人。 匆匆又5年。1989年11月,我去上海参加“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说来令人感慨,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十分活跃,其中,巴金研究堪称进展最大、收获最丰的领域之一,但召开全国性的巴金研讨会,却困难重重,在上海同仁的努力下,直到1989年尾才得以举行。研究者们从各地赶赴上海市郊青浦宾馆,兴奋和欣喜自不待说。11月21日,会议开幕。许多代表要求探望巴老,会议主持者颇感为难,他们在开会前已与巴老联系过,未得同意,因为巴老不习惯也不愿意搞“接见”式的会见。会议主持人再三解释,但要求仍殷殷不停。于是,23日下午,我同李济生老人、丹晨同志陪与会的几位日本学者去巴老寓所,同时,代大家再向巴老陈情。我对巴老说:有十几位研究者,也是几十年来读您的书的读者,现在来到您的门前,不见您心里实在过不去,50岁的人说起这事都流泪,请巴老见见吧。巴老听后,立即说:“见一见,见一见。”这样便约定第二天上午10点见面。第二天,我随过去已见过巴老的代表参观大观园,十几位从未与巴老谋面的代表,则乘车去武康路巴老寓所。 会议闭幕后,28日下午,我与思和又应约去巴老寓所请教教有关老人的集外佚文等问题。这两次见巴老,我明显地感到,老人的体力不如5年前,行动已很困难,但他那平易的风范、清晰的思路仍然如故,他思维的敏捷和记性的超常,更令我惊叹。 28日我们去巴老寓所前,先到华东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王瑶先生。说到王先生,我不能不多写几句,因为王先生的名字也是同巴金研究连在一起的。早在1957年,王先生就发表了《论巴金的小说》这篇奠定我国巴金研究基础的力作;80年代,王先生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撰写“巴金”辞条,全面而中肯地评介了巴金的剧作道路和文学成就。王先生一直关心支持巴金研究,并为巴金学术研究的收获深感欣慰。 1985年,我和丹晨同志受同仁之托,到北京大学镜春园76号拜访王先生,请他领衔主编《巴金研究论集》(另一位主编是复旦大学的贾植芳先生)。1989年11月9日,我代“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与王先生联系,他在电话中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一定参加。”他还告诉我,即将动身去苏州出席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会毕便赴上海。21日,我因事耽误,下午才从北京飞往上海,同仁告我,王先生上午抱病出席开幕式,但无力讲述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贾植芳先生的劝说下退席休息,已住青浦中医院输液观察。当晚,王先生病情加重,次日转至市内华东医院住院治疗。我和思和去医院时,思和买了一束鲜花,病房的护士小姐找来一个广口瓶权代花瓶,鲜花使洁白的病房增添了一些生气与活力。王先生此时已不能说话,但头脑清楚,面部表情乐观而坚毅。陪伴先生的师母告诉我们:上午,巴老来医院看病,因不能上楼,特让女儿李小林代他到病房向王先生致意。想不到,这一天竟是我同王先生的诀别。12月27日,在八宝山王先生的追悼会上,我默立在人丛中,想到50天前我与王先生的通话,和一个月前在上海的最后一面,想到王先生一生的学风和人品,开拓和成就,不禁黯然泪下。王先生是从巴金研讨会的会场上住进医院的,他是“战死”在现代文学研究阵地上的啊!我蓦然想到巴老1938年在《做一个战士》中写的一段话:“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王先生不正是这样一位“战士”吗?因此,在向王先生的遗体鞠躬时,我心里除了哀痛,还升腾着一种异样的感情。…… 我与巴老接触不多,仅有的几次见面,都在老人80岁之后。尽管每一次见到老人,我都有所获,有所感,有所思,但我却认为实在无需用铺陈的笔去描述每一次见面的情形,这是因为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位诚挚、平易、谦虚的老人,是一位爱憎分明、热情正直的战士,是一位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作家。他不是“首长”,不是“名流”,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仙。读他的作品,我像是在聆听他促膝谈心;坐在他的对面或身旁,我眼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普普通通的老人。我爱我眼前的巴老,我敬我眼前的巴老。 自“五四”以来,可称为“作家”的中国人车载斗量,然而,真正把写作当作事业,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方面卓有建树者,却可以数计。有的作家才华出众,或一度辉煌,或写过力作佳构,但星换斗移,沧海桑田,逐渐失却光泽,有的甚至蒙上尘垢。更有的号称“作家”者,或猎于名,或钓于利,或屈于力,;随时俯仰,见风转篷,文章或有可取,人品几等于零。巴老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他亲历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的全过程,除去头10年和被迫搁笔的“文革”10年外,其余50余年都堪称文学创作的大家和文学运动的中坚。 像巴老这样,长达70余年坚持写作,坚持用作品同读者见面,其作品在几代读者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在现代作家中的确不多见。巴老不想当作家,但生活却把他造就成一个作家。 一个为写作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大作家。巴老写作如同在生活,为使世间更温暖、更幸福,人的心灵更纯洁、更美好,他写作一生,探索一生,思考一生,奋斗一生。他用作品说真话,吐真情,真切反映时代的影象,尽力抒写人民的心声。他有过迷悯,有过坎坷,也有过错误,有过失落,但不论处于何种境地,他始终不忘读者,不忘祖国,始终襟怀坦白,勇于自剖,始终追求真理和光明,坚持理想和信仰。其言以真而传世,其文因德而益彰。在这位写作与生活一致、做人与为文一致的作家面前,諛词和贬斥同样不都是苍白无力的吗? 记叙或评述巴金老人的一生,是一件为许多人关注的工作,已经出版的几部传记和评传,或重在作品的评析,或偏于经历的描绘,或以铺叙言行活动见长,或以揭示人格发展取胜,自成一格,各有特点。我的这本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吗?这不该由我作答。我所能说的是,我力求忠实地、客观地叙说老人不懈奋进的一生,特别是他在思想和创作方面探索、追求的历程;以目前所能掌握的全部材料为根基,不取巧,不自以为是。我爱巴老,我敬巴老,但我避免用一己的感情去择取事实,以个人的好恶去剪裁历史。我的写法也许拘谨,但执著于材料也颇艰苦。我有自知之明:我笨拙的笔,写不好这位世纪老人,时代良知。我这样自慰:我所写的巴老,也是一种认识,一种观照,一种理解,一种表现吧。今年,巴老整整90岁了。在这个时候,我把这册书奉献给读者,也多少卸下了自己心上的重负。于是,我释然了。 末了,对于不断督促和鞭策我的朋友们,对于栽培本书的园丁们,我深深地道一声:谢谢! 作者 1994年中秋夜, 于巴山洞明月下。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巴金逝世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