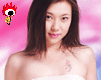香港商人包养二奶 记者探访深圳二奶村(2)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3日21:32 新民周刊 | ||||||||
|
“买卖就要讲个价”
在《苦婚》中,有一位港人司机阿松(化名)的说话—— 在深圳生活,我的几个同事先后在这里包养了二奶。说起夫妻制度,我爸爸就有三个老婆,那是上一辈的遗风了。我想,有伴总比孤独好,何况费用不高,两个人的开销跟一个
涂俏说到激动处,会站起来:这个海湾村,原来的渔民、农民啊,改革开放以来迅速致富,有钱就盖房。一盖就是七、八层楼。海湾村里盖了140多栋楼房,现在有200来户是原住户,其他1000多户,都是住满了的。“村子里的年轻靓妹,多是四川妹、湖南妹、贵州妹、江西妹,等等。我敢说,就这些妹子,就是让她们换上深圳女孩子的衣服,站到街头上去找工作,她们也很难找着。为什么?最根本的,是没有文化。还有,就是从事简单的密集型劳动,时间很长,工资又太低,600元、800元,她们有谁愿意干?” 《苦婚》,这本22万字的著作里,记录的就是诸位外来妹子“怎么从打工到当二奶”的过程和现状。千回百折也好,千头万绪亦罢,说的大都是家乡贫困,特区诱惑,抵达后寻找工作的屈辱,挣钱时岗位上的艰辛,及其最终万般无奈之后的屈服和出卖。有的当过餐厅的“企客”,也就是门童,试工时从下午站到下半夜的2点,先站10 天再说是否要人。也有做企业的“大烫”,服装厂的烫工手提2.5公斤重的熨斗,一拿10个多小时。更有做桑拿女和发廊妹的。再有就是收入太低。有人受欺侮了,有人来表示救助,有人开出价位,于是,就有人“卖”了。从一天一卖,到几个月一卖,比较好的是几年只卖给一个人。“最好的是将来‘转正’。” 于是,处女补膜术诞生了,二奶介绍业也半公开了,人贩子应运活跃…… 年纪轻轻的阿妹已经先后有过两次被包养的“历史”。她家在农村,13岁出门闯世界,1998年春节过后来深圳淘金。她读书读到初中一年级,诸多大字不识,缺乏技能,在城市劳动力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她被淘汰了。 她不得不答应去见见同乡女友介绍的那位香港老头。 ……怎么比自己的父亲还要老?介绍人用身体挡住她的退路,劝她:你不是处女,又没有钱了,回家不也是一样要嫁人?天底下男人都是一样的。下回有年轻的,保证给你介绍。 老头见阿妹点头,很开心,乐颠颠地带介绍人和阿妹去酒楼吃饭。嘴巴一抹,急如星火带着阿妹去租房。租房很神速,半个小时就租了一套二房一厅。再赶到村里的一家超市与家具城,买了沙发、衣橱、床垫、床架、床上用品、梳妆台、茶几、凳子,还有热水器、电饭煲、煤气灶与煤气罐,付了50多张百元大钞。等到商店把货品送到房内,打理完毕,已是凌晨2时。 ……香港老头督促阿妹冲凉。阿妹强作欢颜,“端了人家的碗要服人家的管”,她重重一声叹息,钻进被窝,紧紧闭上了眼睛。……她想离开老头,深更半夜的,她又能到哪里去?身上的钱住宿费都不够。阿妹也觉得,如果不辞而别也对不起老头,人家毕竟是正经跟她过日子的,他为她置办了这么多的家当。 阿妹与香港男人的见面时间在下午,到交易达成,住房家具全部办妥,直至下半夜两点,男人让女人冲凉,也就花了8至10个小时。男人出的价位明确而简单,花去50多张百元大钞。房租另付。此类房租一般价位在1500元至2000元。如此界定,购置一位内地年轻女子阶段性“陪伺”的首期费用,大概为7000元人民币左右。 这段记录,又是没有时间概念的,即没有规定这个香港男人与阿妹的“合同期限”,介绍者也根本不涉及这个问题。所谓的遇上年轻人再介绍,本就是顺口胡说,透露出的就是卖了一次,以后可以再卖第二次、第三次。 第三天,这香港老男人返港“打理业务”,七八天后回来,带来一枚戒指,再给阿妹500元人民币“零用”。而内地女子的心态是:人家也在花钱与自己“认真”。在香港男人和内地女子的心目中,在这段“苦婚”的实际操办中,根本没有“法律文书”的影子。 生活了一年多,我觉得这个港人还不错,每月按时给我3000元,房租也是他出的。我的生活一下子从容起来,安定下来,也算小康了吧?我很满足这种被人包养的生活,真的很满足。我有一位好朋友在沙头角做咨客,冬天穿得极少,每天还冻得鼻涕乱流,“罚站”超过10小时,一个月才600元。我做美容,一个月都不止这个数。 海湾村里有个小花园。一处大理石凳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大体感觉是男长女幼。涂俏说道,又是一对在谈判,人家出钱多呀。我回答:我的感觉复杂,现在我脑子出现的几个字是:“买卖就要讲个价”。 变革的悖论和呼喊 有二奶,就有大婆,有二奶、大婆,就有她们共有公用的“爷”。 中国有句老话: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句话从来就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职场”气息。婚姻之中应有的一切内涵,在这句话当中影踪全无,剩下的只是作为生命生理需求的供给者和受惠人的关系。中国农耕岁月,男人是主要劳动力;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大转型时期,因为经济发展生态的不平衡,因为传统规则泥沙俱下的沉重负荷,二奶现象的出现,成为难以避免的社会故事。 从打工到二奶,年轻的女孩子们走过血和泪的长途。无穷尽的等候,间隔型的会面“睡觉”,定期颁发房屋租金和包养躯体“肉金”。在人类范畴,性是人灵肉合一的故事,正常婚姻中女性都具有的深情、哀怨、愤懑和仇恨,还有故作姿态的平淡、言不由衷的表演,二奶们都不缺乏。自然,男人们也理所当然地“制造”些削价、拖欠、最终“玩失踪”等等故事来应对。 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很多二奶们将“当二奶”作为一种“不错”的职业。 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贫穷家庭的女孩子难道就不能通过一些极端方式来改变命运?我也奋斗过,我也打工呀,可是代价太高了,不是被男人欺骗就是自己无端地生病。我们永远是弱者。 在这个村里,二奶有不少相同之处。家境相同:来自农村贫寒家庭。家庭背景相同:家中有兄弟姊妹多人。你一旦外出打工,往往逼得你去卖血卖身也得搞点钱回家,养活他们,甚至供他们上学、盖房、讨老婆!婚恋悲剧:出来之前或者是被包之前,都经历过失败的婚姻或恋爱。教育背景相同:绝大多数是初中或小学毕业。外出打工经历相同:孤立无援,吃尽苦头,因而常常被人欺负。导致的结局也是一样的:被人包养。 我不是表示做二奶就是这一类女人的唯一出路,但至少对我来说,从我遭受的挫折来说,我不敢再去社会上打拼了,我拼不起,就干脆让人养起来算了。有人叫国家养,有人叫企业养,光拿钱不做事,儿女出国,衣食无忧。我们那里有人5岁造花名册,就是国家干部,就有了国家工资。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叫男人养? 正在六神无主的时候,遇见一位高中同学,她已经做了香港人的二奶。她的“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想找一位老实本分的内地女子做小的。女同学劝了又劝,叫我与其千辛万苦,不如每个月拿几千元“固定工资”算了。我想了一个星期,我咬着牙答应了。 一年多来,我累得很,总要遭受不同男人的欺负。做小姐这样烂下去不是长久的办法,不如找个男人稳定一点,不用成天担心得性病。我想也没想,就跟他来到这个村,租房子住下来。他一个星期过来一次到两次,我慢慢地喜欢上他了。我一个外来妹子,在深圳总算有个家啊!总算有个男人记挂着我啊! 涂俏遇上一个叫阿婷的二奶,她认为自己遇上了好人。她被包养的价格较高,每月5000元家用,还不包括房租。这5000元,就是阿婷的“红利”。逢年过节,“老公”还给红包。有时一个红包就是一万元。她要是“离婚”,家里就断了摇钱树,又要坠入贫困。阿婷认为:“女人有人养,不愁吃不愁穿,这才是天大的福。(家乡)全家人一年到头,从春累到秋,田地里收下的苞米、稻谷、红薯,统统加起来,也卖不到5000元钱!”阿婷父亲还这么说:做二奶有什么怕的,好过在家乡挨苦受累,一月拿5000元钱,不要说下田,连太阳都晒不到一下,要知足! 对于这类特殊女子来说,她们是生活在深圳特区,但她们心中却依旧生活在自己家乡早被确定的行为支持或束缚“系统”中。这个“系统”的成员,就是同乡与亲友。二奶们的大多数都获得了足够的支持,尤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的广泛宽容。 究竟是什么使得那些“支持系统”笑贫不笑娼,认为当二奶不再是一个“火坑”?答案是简单而又极其复杂的:因为支持系统的贫穷,因为血源关系的责任;因为经济条件的差异,因为面对未来的向往。 大变革时代的社会,人潮开始流动,心愿开始更新,外边的世界很精彩,里面的世界很无奈,到处充满着呼喊和悖论,悖论和呼喊。 什么未来不未来的?对我们这些做小的来说,有个男人呵护你,这就足够了。 鬼话,凡是做二奶的都想不开。阿灿喃喃地说:做小,做小,小、小、小……说着说着,她突然嚎啕大哭。这一天,阿灿的哭声使得整个海湾村都显得这般苦涩。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