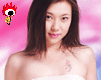香港商人包养二奶 记者探访深圳二奶村(组图)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3日21:32 新民周刊 | ||||||||||||
 海湾村在阳光下,也在迷蒙中  村口道上,停满香港来的货柜车 到今天中国经济的大转型时期,因为经济发展生态的不平衡,因为传统规则泥沙俱下的沉重负荷,二奶现象的出现,成为难以避免的社会故事。 撰稿/陆幸生(记者) 关照小心,绝不是空穴来风
涂俏对我说,把照相机放到风衣里面去,别让警卫看见。我照办。我心里嘀咕,这是什么地方,特区的“特区”? 前天,我在电话里与涂俏联络,我在上海文汇报工作多年,“我跟你是一个单位的”。这句话打动了这位女同行,11月26日,在感恩节这天。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涂俏,特地从香港赶到深圳机场来接我。进入市区,她的捷达车停在距离海湾村远远的道口。我与她下车步行。环顾四周,高楼林立,一派新兴的城市景象;大道通衢,多层立交路上大吨位的卡车在轰鸣。这里没有传统村庄的一点影子。 涂俏告诉我,在附近另一个地方,有记者采访,人被打,照相机也被砸了;我怕你遭受“同等待遇”,我们小心为上。 大道深处,隐约露出与周围大厦不太相符的多层旧楼。一位穿着迷彩服的男性年轻人,坐在“村口”右侧餐饮店门口,见我们走来,他站立起来,眼光对着我们扫来。我观察到,左侧一餐饮店门口同样的一位“迷彩服”也站立起来,看着我们。 距离农历春节(2001年——编者注)还有10天,在深圳打拼的外地人员开始陆续返回内地老家过年。从这天开始,我隐姓埋名实施“卧底”调查,拖着两三件行李,搬进深圳河畔的某某村(为叙述方便,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称之为海湾村)一个小单元居住。稍事休息,已是中午12点。 我这里所说的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青山绿水、田畴围绕的村庄,而是城中村,或者说是城市街道的一部分,只不过在城市规划里被区别对待,还保留着一些农村原生态的建筑群落。深圳市区发展迅猛,原有村落来不及同步建设,就有许多插花地一般的村子。海湾村村内主干道上有一家茶餐厅,我在那里买了一份堡仔饭吃。 堡仔饭香气扑鼻。不期然,一位女仔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她身材娇小,短发齐耳,穿着一身粉白色的棉睡衣,外罩一件艳黄色的太空衫。她走进柜台,对老板娘交代外卖的内容。她的举止使我感到某种不安,时不时警觉地睥一眼门外,眼神有些惊恐。不看门外的时候,她还是低着头,闷闷地想着心事。 (摘录于涂俏《苦婚》,下同) 我和涂俏走在海湾村的路上。路旁有各色小店,小饮食店,小百货店,商品的艳俗在表明着一种原料和审美的最低层面。有一卖家具的旧货店,一位老伯在修理旧沙发。涂俏告诉我,她就在这个店里买过东西。“这个二奶村里,有个二奶散伙了,香港人付清房租撤退,二奶便将家具卖掉。这家具原本是当初香港人买下的,女的并没有掏钱,现在钞票归己,也算一笔额外的收入。然后,后来的另外一些二奶,再来买这些旧的家具,再用。”60元收进一个旧的大衣柜,转手就是110元,七成新的松下电视机收进400元,再卖出去650元。港人包养二奶,带旺了相关的旧家具行业,涂俏说:“匪夷所思吧?!” 家具在反复使用,女人在反复“就业”。买新家具好像也用不着,家具生意便可如此循环地做将下去。 我照相机里留下来去匆匆的照片。第二天早晨6点半,不甘心的我,叫上出租车,再次来到海湾村。我想,这个时候的二奶和她们的男人们,还在睡觉做梦,照相大概会少些干扰。我也在远处停车,拍下在道上停满了的香港货柜车。这条道上有规矩,附近的私家车晚上不能停在道上,全部停进小区,道上“让”给香港货柜车停靠。一辆货柜车每晚交50元人民币停车费。这是一笔固定的收入。 这些货柜车的司机们,就是二奶村里的“爷”。 我提着照相机大步迈进,没想到的是,深圳的早晨,7点钟还没有到,而右侧餐厅门口的那位迷彩服已经上班,他迎着我站起身来。紧接着,左侧餐厅的那一位,也怏怏地站起了身子。这座粗陋的、紧靠边界铁丝网的小小村落,“享受”的是24小时不闭眼的警戒。我转身离去。 五六分钟后,一个电话打到已经在行驶的我的出租车司机手机上。我听懂了他通话的大约意思。待他关上手机,我说,你们的反应速度很厉害啊。司机回答:我在旁边村里住,海湾村有熟悉我车号的人,刚才看这个车号的乘客在照相,电话就打过来了,问这个乘客要干什么;我说,是个记者,就来看看,没别的。这位出租司机是湖南人,与老婆孩子一起住在邻村,这一天他是夜班,已经做了个通宵,早上8点钟才下班。他拉我打的是“夜工”,他说:我就下班了,今夜的钱挣好了,完事了。我多少听出他的话外之音:记者来拍照,“我不扯这个事情了”。 我终于理解,昨天涂俏关照我的“千万小心”,绝不是空穴来风。 支出不增加,“花法”换了 到达住宿的宾馆,涂俏签名送给我一本在今年11月中旬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苦婚——60天隐性采访实录》。内容可简洁地概括为“女记者隐性采访深圳二奶村”。 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一批来往于香港与内地的香港商人、白领人士以及货柜车司机,开始在深圳等地包养“二奶”。随着这个“风流军团”的扩大,一些位于罗湖文锦渡口岸附近的花园住宅,因“二奶”相对集中而闻名。90年代中叶,随着深圳中心区的西移,福田区成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娇”的首选地。沿深圳河北岸,邻近中国最大的内陆口岸皇岗口岸附近的众多村落,因便利出入境货柜车司机的歇脚和进出,日渐成为香港货柜车司机包二奶的首选之地。对那些二奶租住较多的村子,人们习惯上称为二奶村。这种叫法,不科学,但口口相传,仿佛已经约定俗成。 港人在深圳包养二奶竟成为一道独特的景观,由此而在香港与内地造成严重的社会、家庭、道德等问题,早已引起广泛关注。 我向涂俏提出第一个问题:说到二奶,一般人以为,是大陆经济开放后,境外各色资本进入内地,香港、台湾的老板们来做生意,金钱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搞活”,有经济建设方面的,也有社会生活状态的。有一些老板们花钱买色,一夜曰三陪,买房藏娇,期限不一的固定关系就是“包二奶”了。“你这本书很怪,不是写老板包二奶,不是写‘资本’买色。你写的是一些在香港非常普通的货柜车司机们,他们挣的是薪水,也可以说是血汗钱,可他们怎么就包二奶了呢?” 涂俏说道,“这个问题很到位”;我在2001年采访,当时做了若干报道;在充实的基础上,今年出了这本《苦婚》。我当时是记录实例。今天,“你要问的是一个概括的理由”。我说,我的问题当然涉及道德评判,但我更要问的,一是地理理由,因为任何历史首先是地理史,二是金钱理由,是港人司机的“经济分配状况”。 涂俏回答:坐在海湾村的小花园,隔着水泥围墙,就看得见深港两地的出入口岸。几乎可以说,香港的货柜车出了口岸,来道上拐个弯,就进入到海湾村,几分钟的事。港人货柜车司机们来到海湾村,吃饭食宿成为他们最近便的需求。在海湾村这一带,普通宾馆或招待所,100元到150元睡一夜。司机们两头拉货,一般两三天进出一次口岸,一个星期来两三次。一星期的宿费是300至500元,一个月将近1200元到2000元人民币。“货柜车司机还要吃喝,费用就要翻上一倍多。” 香港货柜车司机出车到深圳,属出差,除去工资,是有出勤补助的,大致也就是四五千元钱。货有轻重,路有长短,辛劳的货柜车司机的职业需求,就是吃好睡好,保证第二天的正常出车。“然而,招待所不是为一个人开的。” “于是,有些司机发现,自己每个月在路途上必定要花费出去的四五千元人民币,除去交给食堂和招待所,其实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花法:租间房,‘租’个内地的年轻女人,这个空间、这个女人,从锅到床,从碗到性,就归我这个出资者到来时使用,而且,服务质量还高。” 对于那些包养二奶的港客来说,人届中年一觉醒来,青春早已不再。当深港两地交流愈加便捷顺畅,当他们开车长期往返,目光越来越多地投注在遍地可拾的内地女孩身上的时候,他会忽然发现,他们手中的钱竟然可以给自己带来某种鲜活的东西,那是已经逝去的年轻时代不可能实现的某些东西:男人的尊严、青春的活力以及情欲的刺激。 他们的青春和岁月都消耗在深港两地的公路、马路、高速路上,在不见尽头的路上往来穿梭,“在路上”的两端终点,香港有家,深圳有室,在他们看来,这也许是婚姻的理想状态。如同元代小说作品当中,经常会被提及的“两头大”,就是常年在外地经商的商人,家中一妻,又在外典雇一妾,因为妻妾分住两地,妾亦如同主妇,就变成两头都“大”了。 海湾村中二奶的男人们,80%是货柜车司机,百分之百的港人。在海湾村,涂俏用“被抛弃的二奶”身份,努力与“同命运、心相连”的二奶们厮混,但很少能与二奶背后的男人打上交道。涂俏解释,港人司机们身在“行宫”、“外室”,“走婚”的时间本来就不多,蜻蜓点水,来去匆匆。二是二奶们十分珍惜“老公”回家的短暂时光,二人世界不容打搅。 从二奶们的话中,涂俏得出港人司机对于二奶的“总体要求”,是温顺、贤良、宽容、能干、疼人。我注意到,涂俏的表述中,没有“姿色漂亮、曲线动人”这样形容女性的常用语。涂俏说:她们不漂亮的啊;还有,比起浑身是病的“三陪”,她们比较“安全”。 我接着说: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地理史,将“地理”与金钱结合起来说,就是一个“两地劳动力价格和市场消费差异”问题。从《苦婚》里可以看出,港人货柜车司机的月收入大致在2万元人民币,甚至还有高一些的。这样的薪水收入标准,远高于内地司机的工资。何况,还有补助。薪水交香港大婆,补助“包二奶”, “香港大婆过去能拿到多少养家钱,现在还照样拿多少,一文不少;男人在外边的支出也没有增加。只是,这些大婆的男人用自己的出差补助,在低收入区域换了一种‘花法’”。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社会新闻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