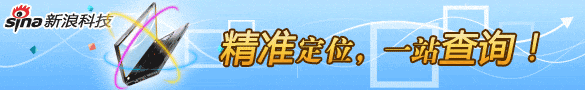男子保外就医刑期顺延12年调查:有关方面不作为
 怀抱儿子的牛玉强脸上写满幸福
怀抱儿子的牛玉强脸上写满幸福
 就在报纸刊登这条消息之前的4月底,牛玉强已被狱警带走
就在报纸刊登这条消息之前的4月底,牛玉强已被狱警带走
中国最后一个“流氓”
“流氓罪”和“严打”是牛玉强的悲情史中抹不去的两个关键词。由于有关方面的推诿和不作为,他的刑期被顺延至2020年2月21日,据此,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记者/应 琛
“流氓”一词,由来已久。按学者朱大可考证,“流氓”原指丧失了土地家园与灵魂家园的人,其涵义随时代的延宕而逐渐狭隘化,最后演变为一种伦理之恶,遭到了国家的厌弃,并作为一种罪名被纳入律法之治。
很多今天看来根本不算犯罪的行为,却在当年“从重从快”的“严打”政策之下获得重判。作为著名的“口袋罪”,流氓罪及其相关案件,更像是一个幽暗年代的黑色幽默。
1997年,新刑法正式实施,流氓罪被永久删除。但这个由时代造成的悲剧,却并未画上休止符。最新登场的主角叫牛玉强,他的青春曾与流氓罪打了个照面,从此青黄不接,命运多舛。按照刑期计算,牛玉强将是全中国最后一个走出监狱大门的“流氓”。
牛玉强到底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行?是谁让他成为了中国最后的“流氓”?在流氓罪被取消多年以后,他又是否仍要为那一段荒诞的历史买单?
从“严打”到保外就医
12月的北京气温虽已接近冰点,但只要不刮风,并不会像南方的湿冷那般令人难受。牛玉强的家就在北京八里庄一幢有着30多年房龄的6层公房内。沿着楼梯来到顶层,楼道内已经囤积了一大堆过冬用的大白菜。敲开牛家大门,一个身高不足一米六、40多岁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她就是牛玉强的妻子朱宝霞(化名)。房间内,牛玉强的老母亲、妹妹和妹夫已早早地等候着记者的到来。
这是一个只有五六十平米的两居室,房间内尽是些简单而破旧的家具,斑驳的墙壁上,随处可见石灰掉落的痕迹。采访在牛玉强母亲的房间内进行,如今已75岁高龄的牛母热情地给每个前来的记者倒了一杯茶。一阵忙活之后,牛母坐在床边,回忆起了那段充满悲伤的往事。
1983年,我国开始第一次“严打”,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公布,6种犯罪行为被大幅提高量刑幅度,其中,流氓罪列于首位。到处都是警察。每天都有人被押往公判大会,每天都有“犯罪团伙”被捣毁。“从重从严从快,绝不放过一个坏人!”广播里那一阵阵高亢的声音犹然在耳。
身为某国有企业模范员工的牛母一度认为这事跟她扯不上关系。但就在当年初秋的一个晚上,两个女儿哭着站在了她的而前,原来哥哥牛玉强出事了。
根据后来送到牛家人手中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描述,1983年5月某一天(判决书连具体日期都未标出,其疏漏程度可见一斑),牛玉强参与了流氓组织“菜刀队”,当时团伙成员共有八人。他所涉及的罪行包括:伙同六人,对刘洪利和孙积春进行殴打,并抢走孙的一把蒙古刀;与两名同伙持械抢劫一名男青年,抢走一顶军帽;参与将刘红家的窗玻璃砸碎;纠集三名同伙,威胁与毒打一名叫许林的青年。至于打架到底造成了对方什么样的伤害,判决书上并没有注明。
最终,团伙内带头的“首要分子”被判了死刑;而对牛玉强的量刑是:死缓。从此,“流氓罪”和“严打”成了牛玉强的悲情史中抹不去的两个关键词。
“做梦也想不到大强敢打人!”牛母含着泪水,仍然忘不了当年的惊讶。牛家人关于牛玉强的一切记忆也都与“流氓”无关:他小时沉默、腼腆,“像个大姑娘一样,就算是在家里的亲戚面前也总是沉默低着头”。
牛玉强特别爱干净,从来不穿脏衣服,比两个妹妹还喜欢照镜子。在牛母看来,毁就毁在“太大姑娘了”。牛母表示,牛玉强的性格是别人说东,他不敢说西的。那会儿,在厂区宿舍大院儿里,没上学的孩子有十几个,他们拉帮结派,没考上高中的牛玉强自然“入了伙”。在那群孩子里头,岁数最大的牛玉强却只是个“小弟”、“跟班”。
1984年,牛玉强和其他流氓犯都被送到石河子监狱劳动改造。1990年,因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牛玉强先后两次减刑,被改判为有期徒刑18年。但长年累月的超强度体力劳动,他患上了严重的空洞性肺结核。
同年,在监狱的审核下,他被老父亲接回北京。当时,一米七十多的他体重不足90斤。回到家中的牛玉强,浑身长满了脓包。据妹夫描述,最大的脓包有核桃那么大,都烂到了肉里,就是一个个坑。而在监狱里,牛玉强的左胳膊还落下了习惯性脱臼的毛病,有时一抬胳膊或睡觉翻身都会脱臼。
牛玉强深知家里全靠父母每月不足百元的工资以及亲戚的接济为生,他坚持没大事不去医院,5元一次抽血、30元一次接胳膊,他都嫌太贵。脱臼的时候,他就让老父亲使劲儿帮他往上推,疼得哇哇叫。
1991年,石河子监狱方面组成的保外就医考察组曾来到牛玉强家中。经过评估,做出续保一年的决定。但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牛玉强等着,考察工作组却再也没来过。
其间,在家休养的牛玉强病情也逐渐好转。他很少出门,只是闷在家里写思想汇报,然后送到派出所,送到居委会,送到街道的司法所。每逢北京发生了大案或举办重大活动,民警会来找他谈话。就连出门几天,牛玉强也必向民警汇报。
意外来客
1996年,有人给牛玉强介绍对象——在北京长大的河北籍姑娘朱宝霞。第一次见面,牛玉强就坦白了自己的情况,说自己还是个囚犯,属于保外就医。朱宝霞觉得这不重要,年轻时打架而已。加上朱宝霞觉得自己年纪也大了,已经相了近10次亲,一次也没有看上的。对白净帅气的牛玉强,她倒是一见钟情,“就图他人老实,不是那种特油的人”。
恋爱一年后,他俩结婚了。也是这一年,修订后的刑法实施,牛玉强所犯的流氓罪被删除。但当时小两口并不知道这个消息。两年后,宝贝儿子的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欢乐的同时,也增加了不少负担。
牛玉强曾琢磨着出去挣钱,但他身体弱加上没有身份证,找工作基本无望。家里的收入全来自朱宝霞在外打零工每月的五六百元。于是,牛玉强揽下了所有家务以及照顾孩子。扛着重担的朱宝霞从不埋怨牛玉强:“我们之间感觉特别好。他不浪漫,也不挣钱,可说不上来哪儿,就是挺好。”
牛玉强从不说脏字,也不会吵架。“他平时就爱看球,喜欢AC米兰。他很少跟人说话,碰见街坊也会刻意低头。就算是别人说了些难听的话,他也总是一笑了之,理由是‘避免吵架’。”好几次朱宝霞都看不过去,责怪丈夫太窝囊。
在牛玉强的观念里,只要在家里等到2008年刑满了,去一趟新疆办手续拿个释放证明,回来就是普通人了。
一家人的日子就这样过得拮据而平淡,偶有甜蜜。朱宝霞曾一度认为,结婚当晚牛玉强贴着耳朵对自己说的“媳妇儿,我们要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是可以兑现一辈子的承诺。
2004年4月的一天,两名“意外来客”打破了这平静的日子。他们自称是新疆来的狱警,看到牛玉强在家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了。当天家里只有牛玉强一个人,他以为就是例行考察而已。过了两天,这两人又来到家里,说要将牛玉强带回去。
牛玉强和朱宝霞顿时傻眼了。朱宝霞一个劲儿追问原因。狱警回答,牛玉强保外就医逾期未归并在逃,已经被网上通缉。之前监狱多次向北京警方发函,要求牛玉强返回,都没有效果。
“网上通缉?他一直好好呆在家里,定期汇报呀!”朱宝霞立刻去找派出所找来民警。在民警的证明下,狱警的态度有所缓和并表示,离2008年4月刑满还有4年,再加上减刑,应该过两三年就出来了。监狱警察回了住宿地,说第二天来带人。
“亲戚朋友们赶来,有人劝牛玉强跑掉。但他不但不跑,一个人已经开始默默地收拾东西了。你说他这人老实不老实?!”朱宝霞说。
当晚,牛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团圆饭。在房间内,牛玉强对妻子长跪不起,没能照顾家里使他愧疚万分,两人抱在一起哭了好久。
2004年4月30日,牛玉强被戴上手铐押回新疆。5岁的儿子在一旁仍跟往常一样玩耍,年幼的他还不知道将和父亲久别。
从牛玉强离家那时起,朱宝霞将房间墙上的AC米兰海报撕下,换上了儿子的照片。她经常为儿子拍照片,说这样牛玉强就能看到孩子如何长大了。老照片中,最大的一张是牛玉强夫妇的新婚照。没有婚纱,没有钻戒,他们只是“破天荒”地在厂里的饭馆摆了两桌喜酒。照片上,朱宝霞穿着烟儿色带花毛衣,牛玉强则新买了一身藏蓝色西装。两个人笑得很甜。
朱宝霞看着照片,掐指算着日子。可仅几个月,又等来一个晴天霹雳。同样是丈夫在石河子监狱的一个女人说,牛玉强好像被顺延了刑期。朱宝霞写信去问,牛玉强才说:“是的,12年,我怕你接受不了就没说。”
监狱疏忽还是警方不作为?
监狱12年来都没个信,怎么说带走就要带走了?这些年来,牛玉强一直呆在家,每个月上派出所报到,怎么就成了逃犯?监狱怎么说刑期顺延就顺延了?
带着这些疑问,朱宝霞辞去了工作,一门心思为牛玉强的事奔波。她辗转于派出所、居委会、街道司法所给牛玉强开书面证明,证明他保外就医14年间一直住在家里,服从管理、表现良好。随后,她又拿着这些材料,骑着自行车找司法部、司法局、高检、高法,领号、填表、排队一遍遍重复。
“司法部说,你凭口就说顺延了,总有个证明吧。可监狱没给我们证明呀。”牛玉强去监狱要刑期顺延证明,监狱不给也不同意复印。最后,牛玉强只能手抄一份《扣除保外就医、请假探亲逾期罪犯执行通知书》,自己画个章,给朱宝霞寄了过去。
尽管得到最多的回答是:“这不属于我们管。”朱宝霞也渐渐有了进展,找齐了监狱提到的法律条文。“司法部终于给监狱打电话,让他们给我作一个回复。”
收到石河子监狱回复已经是2005年9月的事了。可对方回复的结论是:顺延刑期是正确的。这点也得到了监狱上级单位监狱管理局的认同。此后,朱宝霞再去找那些部门已经不接待她了。
朱宝霞是在向监狱申诉的过程中,才得知保外就医最多只有一年期限的规定。她拿出当年《罪犯保外就医证明书》,指给记者看:“上面只印着‘暂予保外就医’,没印期限。我们又不是学法律的,他们不说,我们怎么知道?”
12月8日,记者就此事致电新疆石河子监狱管教科。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告知记者:“我们不接受任何电话采访。”
在早前《法制晚报》的报道中,曾公布一张石河子监狱于1998年11月25日签发的《提请对保外就医罪犯执行监督考察通知书》的存根,上面有牛玉强的名字,这就意味着直至1998年,监狱都承认牛玉强保外就医的合法性。
记者试图求证此事,对方的语气明显有些激动:“这个通知是一式三份,监狱、北京警方、牛玉强都应该有一份。在注联上,我们写得很清楚,希望北京警方能协助我们在某个时间范围内将牛玉强逮捕,如果仍需保外就医也要及时通知牛玉强办理相关手续。只公布存根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另外,我们每年也都给北京警方发协查函,希望对方配合我们对牛玉强的工作,是他们不作为。现在公布个存根,就变成我们监狱不对了。”说到此处,对方停顿了一下,继而谨慎地表示,“就解释到这里。要采访的话,去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开个证明,亲自来一趟。对于这个事情,我们的材料多了。”
在一份石河子监狱每年给北京警方的发函记录中,记者看到监狱确实从1998年起,几乎每年都给北京某公安分局发协查函。为此,记者又致电牛玉强所属派出所以及该公安分局外宣,对方让记者联系他们市局新闻办。但截至发稿前,得到的答复是:暂时不便接受采访。
在另一份文件中,1995年,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曾对一起因狱警失职而引发的超期保外就医案件作过批复:超期期间应计入执行刑期。这让朱宝霞有了一丝期待:“明明不是牛玉强一个人的责任,为什么结果却要他一个人来承担?”
阿奎那有句名言:法律之所以为人所信仰,不仅在于它的苛严与威仪,更在于它的慈悲心。法律的慈悲心,这回是否也应在牛玉强身上闪耀一回?在一个早已没有流氓罪的国家,却还有人因此而服重刑,无论如何,都令“罪刑法定”原则产生摇摆。同样的,事隔十多年后,将一个并无再违法乱纪行为且改造良好的罪犯延期服刑,既是浪费监管资源,也无益于对罪犯的改造。
朱宝霞说,最近半年来,牛玉强寄回家的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短。她猜肯定是因为“大强太累了”。坐在沙发上,朱宝霞捧着一沓子丈夫的来信念给记者听,眼泪终于像开了闸般流了下来:“我不求别的,只求法律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处理方式,大强能早点回家。”▲
| 请选择您看到这篇新闻时的心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