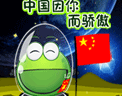巴金:一些说不出的随想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2年06月27日13:44 南方周末 | |||||||||
|
记者张者 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三年多的巴金在为大家活着。他病痛中的生存令人心疼…… 在上海华东医院的高干病房里,巴金老人仰面而卧。5月的鲜花开满了房间,缤纷的
这是巴金老人每天惟一的活动了,从1999年2月8日开始,巴金老人住进医院就再也没有出去。三年多了,他以院为家,整天躺在床上,过上了有口难言的日子。老人的神志是清醒的,而这种清醒对于一个善于思考的智者来说又是痛苦的,是一种折磨。活着不能活动,有思想不能表达,关心着外面的事情无法了解,这位多病、体弱的老人,他的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可是,无论你如何爱戴他、尊敬他,却无法帮助他。 要说真话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巴金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鲁、郭、茅、巴、老、曹……”现代文学史上的6位文学大师人们都耳熟能详。如今,6位中只剩巴金,他成了硕果仅存的国宝。 学术界公认巴金的创作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1949年前,巴金写出了诸如《灭亡》、《家》、《春》、《秋》、《爱情三部曲》等20多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影响了几代青年人,同时也奠定了巴金在现代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1949年至1966年巴金却没有写出让人满意的作品,正如巴金在《作家靠读者养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在17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 巴金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是在“文革”之后,他用了8年时间写了150篇《随想录》,计有42万字。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 巴金在《随想录》(第2集)的后记中说:“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揭露、控诉、讲真话,构成了《随想录》的基本格调。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在“文革”后极左思潮还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之时,巴金率先拿起笔来开始“呐喊”。巴金比较早地提出“文革”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事,每个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是推波助澜者,是有责任的。并且巴金首先拿自己开刀,认为自己在“文革”中也说了假话。所以巴金在《随想录》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的产生是由说假话造成的。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如今当我们读五集《随想录》时,也许有人会说当年巴金所讲的“真话”只不过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常理,在今天看来这些“真话”实在是太普通了。如果把《随想录》和韦君宜《思痛录》相比较,也许《思痛录》更加深刻,更加尖锐。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状况和时代背景,要知道《随想录》写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而《思痛录》却写于90年代,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非常犯忌的话,在90年代已经不算什么了。把《随想录》的第一集和第五集比较起来看,你也会发现,即使是在这八年的跨度中,第五集的文章比第一集的文章也已经深刻得多。在第一集巴金曾写了两篇谈《望乡》的文章,八年后《望乡》简直就不是个事了。最近,我有幸读到由陈思和等人主持编印的《随想录》的手稿本,原来当年出版的《随想录》只是删节本。巴金当年所讲的有些真话,在今天看来也是惊世骇俗的。 巴金说:“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也就是说巴金是真想讲真话的,但是话到嘴边不得不又咽下一点,转换一点,使真话不能痛痛快快地说出。巴金觉得不吐不快却又不敢痛快,如鲠在喉。 后来巴金终于找到了“出气筒”,那就是为巴金开专栏的香港某报。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那是在1981年10月,为了配合鲁迅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巴老为《随想录》专栏寄去了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当时责任编辑正在北京度假,文章刊出后,巴老发现发表在该报上的文章并非原文,而是经过了多处删节。文章中凡是与“文革”有关的词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除了,甚至连鲁迅先生讲过的自己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此“牛”会使人联想起“文革”中的“牛棚”。巴老对此事感到极大的愤慨,为此他一连向责任编辑写了三封信,他在信中说:“……关于《随想录》,请您不必操心,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评判是非吧……。对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当然,对不经作者同意就胡乱删改稿子的报刊来说,作者有理由提出抗议,但是,巴金当时的反应是十分过激的,这在他一生中也是少见的,这和他那温和的性格反差很大。巴金的愤怒针对的恐怕不仅仅是香港某报,一部标榜为讲真话的《随想录》到头来不得不进行多种删除和各种调整以期顺应当时的主流话语,这使巴金无法不愤怒。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要做到完全讲真话,都是十分艰难的。当年巴金虽然不能完全地公开讲真话,却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文学办了几件大事。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如果没有巴金的奔走呼吁现在还不知在哪呢!他亲自创办的《收获》杂志在新世纪的今天也是公认的中国一流的发行量最大的能发表真正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刊物,而这一切和巴金提倡的讲真话是分不开的。巴金以《收获》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不久前张一弓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收获》当年发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曾遇到有关方面的反对,是巴金毅然拍板发表了它。对此,阎钢也曾写了一篇文章,文中披露《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评奖也曾受到了有关方面的反对,评委会不得不向评委主任巴金禀报。巴金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的头一个。《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后来成了“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如今,躺在华东医院的巴金老人无论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了,不但不能讲而且也不能写,只能用点头和摇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巴金曾多次表示过不再当中国作协主席,但是他已身不由己。 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在华东医院的办公室里记者采访了巴金的主治医生崔世贞主任,崔主任已为巴金看了十来年病了,她最了解巴金的病情。崔主任更像一位和善的大姐,一点也没有医生的严厉和凛然。坐在崔主任的对面我问:“你能谈谈巴老的病情吗?”崔主任顿了顿没有吭声。我又问:“是不是要保密?”崔主任笑笑,说:“其实也没啥好保密的,巴老的病情已是公开的秘密了!” 崔主任说:“巴老的第一个病是帕金森氏症,这是1983年确诊的,这个病已20年了,主要症状是面部没什么表情,走起路来不稳,向前冲,手抖,突然身体不协调等。这个病治疗得比较好,病情得到了控制,病情进展较慢。” 巴老的帕金森氏症的主治医生是华东医院神经科的邵殿月主任。1982年确诊后20年来控制得很好,1998年前巴金还可以走路。现在巴金躺在病床上,两只手还可以动。我曾在电话中问邵主任:“巴老的这个病控制得这么好,你用了什么灵丹妙药?”邵主任回答:“我给巴老用的是‘复方多巴’和‘溴隐亭’,其实这两种药并不是最新的产品,在10年前我曾征求过巴老的意见,用不用新药,巴老说这药效果挺好,不用换了。” 崔主任说:“巴老的病都是常见病,比方巴老有慢性气管炎,这个病有几十年了,容易感染,这是巴老年轻时吸烟造成的。1999年2月8日春节期间由于呼吸道感染,突然高热,出现了急性呼吸衰竭。抢救过来以后,病情反复波动。” “是不是从1999年的2月8日开始巴老就没出过院?” “是的。巴老还有高血压和低血压,高血压上去了很高,低血压下来了血压就量不出来了,这样忽高忽低,容易产生晕厥,也就是意识丧失。” “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 “激动、兴奋等情绪波动时。比方某一件事发生了,某老友病故,或者朋友要来看他,在等待中都会使他情绪产生波动。” “所以任何人要见巴老都得特批?” “家里人和巴老身边的工作人员除外。另外,由于感染还引起了一些并发症,比方,甲状腺功能减退、低钠综合征、急性心率衰竭、心率失常、心动过速,有胸水,有贫血,还产生过败血症等。” 我问:“巴老有这么多病,医院是如何治疗的呢?” 崔主任说:“从1999年的2月8日开始,华东医院成立了以院长为组长的医疗小组,我是这个医疗小组的成员。巴老的病情可以分两个阶段,1999年2月8日以前的5年中,巴老一半时间住院治疗一半时间在杭州疗养,春去秋来。1999年的春节期间由于看望他的人过多,疲劳过度抵抗力弱,感冒高烧,引起呼吸道感染,诱发一系列的并发症,痰咳不出来,呼吸不畅,缺氧,脑和一系列的器官功能衰竭,当时情况十分危急。经过抢救性治疗,病情得到了控制。为了吸痰,插管长期插在鼻子里,嘴合不拢,下巴脱了臼。这样我们就做了气管切开,用呼吸机呼吸使呼吸道畅通。巴老最主要的问题是呼吸道,这是一个关键,容易感染。反反复复多次,抵抗差。呼吸道里寄殖菌不容易清除,这就是病因。一感染就引起其他并发症,所以多次病危。” 我问:“巴老是怎样对待疾病的?” 崔主任说:“非常坚强,非常配合。有些治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比方气管插管、胸刺等。特别是打针,他的血管很细很难找,他从来不哼一声。只要他病情好转,他总是表示感谢。在1999年2月8日那次病危抢救过来之后,那时候他还能说话,他说谢谢华东医院,我愿意为大家活着。” 巴金在为别人活着而不是为自己活着。为别人活着,意味着要牺牲自己,是非常痛苦的。这种痛苦巴金又是无法表达的,特别是对他的医务人员。 巴金曾向家人多次提出安乐死。被拒绝后他还向家人发过火,说不尊重他。巴金曾说,长寿对我是一种惩罚。 巴金的痛苦是多方面的,疾病缠身致使他无法工作,友人一个个先他而去。在《随想录》(病中集)中,巴金曾说:“在病中想得太多,什么问题都想到了,而且常常纠缠在一两个问题上摆脱不开,似乎非弄到穷根究底不可……例如生与死的问题,我就想得最多,我非常想知道留给我的还有多少时间,我应当怎样安排它们。而仰卧在病床上动弹不得,眼看时光飞逝,我连一分一秒都抓不住。我越想越急。”《随想录》(病中集)虽然写的是上一次病中的痛苦,但我们从中不难窥探巴金病中的内心。巴金把病中的生活称为“非人的生活”,噩梦和“文革”时的痛苦回忆交织在一起,一次又一次地向巴金袭来,在梦中巴金会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 巴金的这种精神痛苦比病痛带来的肉体之痛强过百倍。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使巴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死。巴金在《病中集》中说:“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巴金曾说:“要是真有一个鬼的世界多好,我在那里可以和我的爱人相会。” 巴金的爱人萧珊曾是巴金的一个读者,当时在上海读中学。1936年巴金和萧珊在上海相识,1944年相恋了八年的恋人在贵阳结婚。萧珊比巴金小13岁。50年代巴金夫妇有了一子一女,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文革”就来了,巴金挨整,萧珊为了保护亲爱的“巴先生”曾挨过红卫兵的铜环皮带。在最困难的时候萧珊总是在巴金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可是,萧珊在“文革”期间身患绝症得不到治疗,后来癌细胞扩散,由肠癌变成了肝癌,早早地离开了人间。巴金后来在《随想录》中写了两篇怀念萧珊的文章,情真意切,读后令人潸然泪下。在病中巴金思念最多的是萧珊,一次次在梦中相见,两人手拉手地痛哭,一直哭醒。醒来是漫漫长夜,巴金会在黑夜中唤着萧珊的名字:“蕴珍、蕴珍你别离开我……”这种思念之苦使巴金恨不能立即到另外一个世界和爱人相见。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 在采访崔主任时我问:“你知道巴老曾向家人提出安乐死吗?”崔主任说:“巴老的病都是常见病,并不是绝症,作为医生我们有责任为他治疗,不到万不得已决不放弃。” 想送巴金一百朵玫瑰 巴金最喜欢玫瑰,因为玫瑰象征着爱,象征着友情。巴金的爱是博大的,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真理,热爱正义,热爱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巴金的爱又是细腻和缠绵的,对爱情忠贞不渝,对友情金坚玉洁,温和,善良,平易近人。 在采访崔主任时,她说:“巴老在华东医院住了这么多年的院,他从来没发过脾气,没埋怨过什么。无论病痛和治疗给他带来多少痛苦,他都是默默地忍受。为巴老护理的护士一批又一批,刚来时心中都是忐忑不安,恐怕护理不好。当她们和巴老接触之后,她们心情一下就放松了,巴老是一个让人亲近的人。护士们换岗时都是满含着热泪的,她们在临别时,默默地为巴老折叠纸鹤,护士们所叠纸鹤已超过千只了。护士们有一个心愿,希望巴老恢复健康、长寿。‘松鹤延年’嘛。”崔主任娓娓道来,她的叙述充满了真情。 巴老的为人是随和也是真诚的,和他交往的人无不被他的真情所打动。由陆正伟先生摄影并撰写的《世纪巴金》大型画册,记录了巴金晚年的病中生活。巴金在病中引起文坛的极大关注,很多著名作家都看望过巴金。在这本大型画册里,除了和家人的照片外,有很多珍贵的照片,具有史料价值。我不妨根据画册的编排顺序列出一个名单。通过这个名单,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坛对巴金的重视。夏衍、王安忆、陈思和、李辉、王蒙、汪浙成、聂华苓、马识途、叶辛、黄源、黄裳、谌容、草婴、周梅森、张光年、周而复、贺绿汀、王元化、舒乙、王西彦、刘白羽、李、李济生、邓友梅、柯灵、赵长天、王辛笛、冯亦代、余秋雨、于光远,来看望巴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朱镕基、李瑞环、黄菊等。 这本画册的第134-135页吸引了我。在这个跨页中冰心女儿吴青正在向巴金诉说着什么,有一个玫瑰花篮,满满一篮的玫瑰花正盛开在巴金身边。上书“巴金生日快乐,冰心敬贺”字样。巴金晚年和冰心交往最为密切,友情十分感人。晚年的巴金是孤独寂寞的,他渴望着人们理解,渴望沟通和抚慰。冰心的友情是巴金最大的安慰,温暖了巴金的心灵。巴金曾给冰心写信说:“……你的友情倒是更好的药物,想到它,我就有巨大的勇气。”冰心回信说:“你有着我的全部友情。”巴金在信中多次表达对冰心的感情。他说:“她的存在就是一种力量。”“我仍然把您看似一盏不灭的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我永远,敬爱您,记着您,想念您。”“我有你这样的一位大姊,是我的幸运。” 巴金和冰心第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当时巴金在北平和郑振铎、靳以创办《文学季刊》,巴金和靳以去向冰心组稿。抗战期间巴金和冰心在重庆再次相见,巴金曾帮助过病中的冰心。“文革”后的1980年,巴金和冰心一起访问日本,当时巴金已76岁,冰心已80高龄,两人曾谈心到午夜12点。 冰心认为巴金是一位最可爱可敬佩的作家。她说:“我爱他就像爱我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他的可佩……就是他为人的‘真诚’。”吴文藻也说过:“巴金真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而且他们还认为巴金“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是“最可佩之处”。 1999年3月冰心去世了,据说巴金至今不知,对他封锁了消息。据巴金的家人说,1999年2月8日巴金病危,通过20天的抢救后刚移到病房,巴金就坚持要给冰心打电话。当时是下午4点。后来才知道那正是冰心的骨灰迎进家的时辰。这种心灵感应恐怕只有相互爱戴的人才有。后来,巴金再没问过冰心,也许他心里已经知道冰心老人走了,他只不过不想去证实,也不愿意去证实,他希望冰心一直活着,活在他的心里。 对巴老“封锁消息”也不是第一次了。当年李健吾去世时,家人也没敢告诉巴金,巴金知道后痛不欲生。在《随想录》(病中集)中,巴金说:“我责备过女儿,也理解她的心情,……相信‘封锁消息’,不说不听,就可以使我得到保护。” 由于巴金病情的特殊性,医生认为对巴老封锁消息是必要的。巴老容易激动,一激动血压就上下波动,会引起昏厥,就巴老的现状来说昏厥是十分危险的。在采访崔主任时,我曾问:“目前巴老的进食情况如何?”崔主任说:“他的进食是通过鼻管,一天分六次打入胃里,特配的流汁。目前巴老的营养状况是好的,每天的热量、蛋白质、脂肪都是根据人体需要配好的。巴老现在不能吞咽,吞咽会反流,会引起感染。如果没有这个管子营养是不能保证的。” 我问:“你觉得巴老还能坚持多久?” 崔主任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对巴老有几个心愿。” “哦?” “第一个心愿就是让巴老能够亲眼看到现代文学馆的建成。” “这个心愿达到了。” “第二个心愿就是希望巴老过千年。” “新千年也过去了。” “第三个心愿就是希望巴金跨进新世纪。” “这个心愿也实现了,那第四个心愿呢?” 崔主任道:“在巴金的一次生日聚会上,我们医生给他送了一个玫瑰花篮,我们对巴老说,希望在你的生日送一百朵玫瑰。” 崔主任说:“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期盼。” 崔主任的话让我很感动,真希望能实现这个愿望,那时候鲜花盛开,人们手捧百朵玫瑰向巴金老人敬献。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巴金逝世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