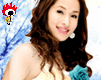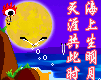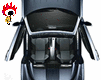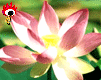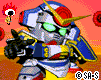今天谁能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被寄厚望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9月22日08:20 中国《新闻周刊》 |
|
一个知识分子的工作如何具有“公共性质”?他能够在别人看不出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来;在别人司空见惯之处,发现隐藏的危险,以及那些未被人觉察的希望 近期《南方人物周刊》选出50名“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毫无疑问,这50个人,都是在某个领域、某个范围、某些特定人群中产生某种影响的人,他们工作及其成果是令人尊敬的。但是“有影响的”人物,并不直接等于“影响中国”。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很简单,以理念作为资本的知识分子要能够“影响中国”,除非他们的思想转化为某项公共决策,或成为制定某项法律条文的依据,使得现有的某些格局发生结构性和调整,从而造成某种不可逆转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比如高耀洁女士长久以来艰苦卓绝的工作,最终推动和导致了中国政府部门正视艾滋病和制定相关政策,这就产生了某些看得见的影响。再比如说去年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为孙志刚事件所作的有力呼吁,最终导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这也是看得见的影响。当然,把一个很长的过程中的很多人的努力,归结于某个人的作用,这又有些不恰当了。 这样说,并不等于知识分子的工作必须导向公共政策,也不等于只有公共政策才是知识分子的归途。我同意关于知识分子是“理念人”的说法,如果他们的工作没有导向公共政策,既不是他们的过错,也丝毫不降低其本来的意义。 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当今中国,谁能影响中国?谁在中国的公共决策中起着主导地位?照这个名单看过去,如果说这些人“影响”了或者正在“影响”中国(注意,说的是“中国”),那么这个中国只能是全世界自由和民主的榜样。 ——显然,并不是把话说得越大,便越好。即使是媒体,它有自己的尺度,也有遵循公共尺度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取决于他的工作的“公共性质”。尽管“公共性”并不是知识分子惟一追求的。 而一个知识分子的工作如何具有“公共性质”?这不仅仅体现在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心或批判。在这一点上,最容易引起人们的误会。当然,这种误会是有理由的,因为有那么多人不关心公共事务,关心是难得的。但别忘了,非知识分子人群中也同样有这种难得的人。 知识分子的关心,更多地体现在他是否能够在现有的公共平台上(不管是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引进某些新的或者不同的维度,发掘那些被忽视和遗忘的视角,以自己新带进来的眼光和尺度,对现有的平台构成一个刺激,产生一个冲击,从而将现有的平台进一步做大,拓展其张力和空间。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人所从事的富有创新、创见的工作。 有一个词汇很好,叫做“洞见”。公共知识分子即是一个“有洞见”的人。他能够在别人看不出问题的地方,看出问题来;在别人司空见惯之处,发现隐藏的危险,以及那些未被人觉察的希望。他和那些被遮蔽、被窒息、被掩盖的东西站在一起。他的预见性、远见也就在此。比如,秦晖先生在“经济大潮”势不可挡的情况下,较早提出“社会公正”,就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 不客气地说,有些喜欢在火灾现场围观并评头论足的人,或者说一看见火灾才兴奋起来的人,他们的公共性是有限的。这些人天天在街上转悠,不是因为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而是不知道怎么在自己的屋子里与自己相处。 而如果人类良心是被遮蔽的、被压抑的,知识分子就和人类良心站在一起,所以有“良心知识分子”的存在。但是,正如汉娜·阿伦特所说,对一个人来说是良心不能忍受的事情,另一个人却熟视无睹,因为他的良心觉得可以忍受。把公共事务交给良心这样一个主观性的东西多少有些危险,良心并不是我们评价和衡量公共事务以及公共生活中他人的惟一尺度。 在这个意义上,“良心知识分子”不等于“公共知识分子”。王怡文章中提到的索尔仁尼琴,便是一个典型的“良心知识分子”而非“公共知识分子”。而那些以“良心的警察”自居的人,动不动就要质问别人良心何在的人,更是与公共知识分子相距十万八千里。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崔卫平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中国《新闻周刊》专题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