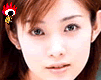最后一棵树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1月08日18:07 安吉生态文化节组委会 | ||||||||
|
郝山终于打定主意,把烟屁股丢到地上踏灭,烟屁股被踏得稀烂,黄的烟丝混着唾沫,像踏死一只 蛄。他披好褂子起身,小路上一层浮土,一脚下去就是一股青烟。那小路很陡,从山上绳似的挂下来,他猴着身子近乎小跑,脚步声在山谷间回荡着,嘭嘭的就像踏在蒲包上,蹚起的烟尘笼罩了背影。
学校座落在一个山顶上,那山顶被削平了,四周光秃秃的,像建在和尚脑瓜上。围墙还没有修起来,红门绿窗的很鲜亮,但贴了白煞煞的封条,像一座被查封的庙宇。它目送远去的郝山,像目送一个下山化缘的僧人。在晴朗的阳光下,郝山的头亮似葫芦,一颠一晃一沉一浮,转眼就消失在了村中。 村子唯一的亮色,是村中一棵茂盛老柳树,蘑菇似的凸现在村子上空,又如女人高高挽起的发髻。村上笼罩着淡淡的烟霭,像深秋坝中散发出的水汽。 郝山形容不来,但心中充满了诗意。这种诗意的感觉,他以往也有过但扯蛋,近日才变得越来越强烈,只要从这老柳树下经过,心情就变得罗罗嗦嗦复杂。但除了诗意更多是别的,说理直气壮也成,说窝窝囊囊也罢,反正他妈的不是滋味儿。 在老柳树下打个定顿,郝山就朝东走去,来到村长刘福家。他一进院,抬头见刘福女人正脱下衣服,站在台阶上啪啪摔打尘土。上身只穿一件衫子,肉滚滚的倒是好膘水,两嘟噜奶子在胸前颤颤的。他心悸了一下,赶紧退出来,重重地咳嗽一声,问福子在家吗?然后又走进院子。 听到咳嗽声,刘福女人一边穿衫子,一边答应在在在。今天是不是长大了,好像他不在就不进来了?说着觉知到了什么,忙把剩下的扣子扣好。她笑道,瞧我这副邋遢相,哪像个妇道人家?便朝屋里吆喝,哎,郝叔来了。 女人的样子确也邋遢,像只坐月子的草鸡。郝山不知平时没注意,还是原来就这副模样?不过蓬鬓厮窝的,加上两嘟噜奶子,倒挺有那么点意思。像城里女人,感觉慵慵的洒洒的,使个眼神儿就勾人。郝山贼一眼,又吭吭两声,一埋头走进屋子。就在他进门的一瞬,背上挨了重重一刮,瞧那球性子气。 那一刮刮得无声,嗔怪也是悄悄的,郝山心里突地一跳,想这娘们啥意思?大白天发烧,还是熟得过头了,随便开一个玩笑?可以往,熟是熟也正经八面,为叔的就是为叔的,做小婶的就是做小婶的。像受了一个甜蜜的捉弄,郝山酥酥的又莫名火气,真想立了眼问你是想咋呀? 郝山装个无动于衷,以同样方式甩了刘福一刮。——哎,你没听见,还是装傻?刘福正头埋在猪食桶上,抱一根棍子拌猪食。他后背猛地一挺,掉头说咋了咋了,你不看我拌猪食?说时,两个人的脸几乎贴到了一块。 刘福两眼冒火,像要干架似的。可一见是支书,眼帘立刻耷拉下来,像电压骤然不足的灯泡,变得眯眯瞪瞪了。他嘿嘿干笑道,我以为她又发啥神经。便解释说,这几天不知咋球了,耳朵老是嗡嗡的响,背得啥都听不见。 郝山也瞪大了眼,这时垂下眼皮说,我还当是夜里耕种,你把镢头子给崴了。刘福被汽腾腾的猪食蒸得一脸汗。他听后又笑了,拿衣襟揩一把汗说,还崴呢崴脚吧,早就抛秃磨光了。 刘福的话郝山相信,瞧那样子像个瘦猴。胡子拉杂的,眼和嘴显得特别大,像电视上的非洲人似的。两个人闲谝时,女人到里屋梳洗打扮了,换一件粉红衫子出来,头发沾了水似的光洁,跟刚才判若两人。她谁也没理会,一脸正正经经的,提上猪食桶出去了。 郝山盘腿坐到炕上,瞟一眼女人的背影笑道,磨秃了到铁匠铺淬淬,地不耕种可是要荒的,荒了就不好收拾了。他掏出两根烟,丢给刘福一支,自己点了一支。说我过来没别的,今天就去找你表哥,依他的意思算了,要不拖到啥时候?再拖下去,雨天就来了,娃们呆那破屋咋行? 刘福当下没有吭声,猛猛地抽口烟吐出来。面前烟雾缭绕,他眯起眼叹道,反正你是老大,你掂量着办吧。娃们倒是一回事,主要是再不决断,村人还以为咱得了好处,跟他纠缠不清。说着把烟灭掉,我这就去…… 两个人相跟出来,刘福骑上破车去了,郝山回家扛上锄头,来到一块山药地里。虽说天旱得很,山药黄兮兮的,可草倒长得挺旺,灰菜有半人高。这些天光顾学校,别的都撂到了脑后,难怪老婆唠叨,再不锄就要荒了。 一锄下去皆是坷垃,遗漏的土烟似的直冒。郝山刚锄了两遭,就再也锄不下去了,心思总投不到地里。他起初不知为啥,是山药长得太蔫气了,还是因刘福女人那一巴掌?慢慢才明白过来,放不下的仍是那老柳树。他打发走刘福,心里终于撇下一块石头,可是撇得一点也不情愿,像赌博赌输了拿房抵债一样。 山药地在半山腰,郝山垫着锄头坐下。远望去,村子栖息在阳光下,像老光棍脱掉衣服,呆在墙根儿捉虱。那情景,跟老柳树很不相宜,甚至是做梦的感觉,而且梦得好像很长久了。对于他来说,老柳树曾经的确是梦,一到春天冒出芽的时候,就会成群结队地爬上树去,猴似的挂在枝头。或悠来荡去地打秋迁,或吱吱呜呜吹柳笛。 等到了夏天,老柳树变得一潭水似的,早晨鸟们从树上飞走,傍晚又一只只飞回来。常是先盘旋一圈,然后翅膀一收扎下,仿佛石子投进静水中,顿时击起一片喧闹。他跟伙伴们也不甘寂寞,不是在地下追逐打闹,就是钻到树上捉迷藏,把村子都给沸了。鸟们顺心就一块闹,不顺心就群起攻击,要么纷纷地用嘴来啄,要么雨点一样屙下白屎。一个个被撵下树来,有的抱头哭叫,有的成了大花脸,非常狼狈。 那一阵子,老柳树像个慈祥的长辈,爱怎么胡闹都不生气,带给了他们无穷的欢乐。郝山遥望着村子,一朵云在悠悠飘浮,飘浮得绵绵絮絮,让人不胜怅然。他回视周围,曾也海似的长满了树,大多是绿苍苍的松树林,一起风就呼啸个不停。最早的时候有狼,夜深人静后出来,蹲在山顶上长嚎,叫声十分瘆人。再后来狼不见了,偶儿还有狍子,现在野兔也难见到了。 树是不知不觉减少的,像人上了年纪的头发,今天掉几根明天脱一缕,一座座山头便瞎顶了光了。村民渐渐发现,哗哗的小河憔悴了,在某个春天终于干枯了,不得不靠打井来吃水。而且风沙也多了,一年四季刮个不停,代替了阵阵松涛。一切变得枯萎起来,包括日头、人脸、畜叫,精神气好像被蒸发掉了。谁也不知为什么,也懒得去追问为什么,似乎从来就这个样子。 这两年上边叫得紧,郝山也多少认识了一点,作支书的总该比别人敏感一些。可再敏感也迟了,况且就那么回事,叫得紧只是叫得紧。老早不过是村民盖房砍几根,或冬天买不起炭劈点柴烧,最近十几年才被急剧砍光了。先是毁林种地,后是偷了运下山去卖,夜半常能听到一种声音。那声音初听闷闷的,像斧头裹起来打人,接着咯嚓嚓似骨头折断,随后轰隆隆震得窗纸发颤…… 一片片林子,成了村民过日的指望,成了村里开支的来源。郝山未当支书时砍过,可当了支书以后,再连一根枝也没往家拿过。这也正是村民服他,把他推上台的原因,但林子又是在他手里最终砍光的。修通村公路要砍,解决人畜饮水要砍,农田基本建设要砍,甚至搞计划生育也要砍。村里穷得叮当响,而样样事情都得钱,不砍树拿啥来支差应酬? 有一度时期,树像旧社会的劳工,挨个儿用红漆标了号,一个号一个价钱。卖树时,木材贩子闻讯而至,沟里停满了大车小车,比城里赶集都热闹。村民有卖茶水鸡蛋的,有专门给人砍树的,还有拉黑牛挣好处费的。贩子们钻进树林,在树下寻来转去,像到了牲口交易市场,只要相准了就拍拍说,这棵我要了。 跟随的人便一涌而上,打手似的把树团团围住。林里到处是斧头挥舞的闪亮,或人拉锯时前扯后仰的身影。斧声远听就像啄木鸟凿啄,锯声就像成群的土蝗进食。郝山听着也曾感触过,也隐隐约约心疼过。卖树期间,乡干部们常下来,说郝山你要小心点,早给你讲过有法了。说着,却拍他一巴掌笑了,谁都清楚村里啥光景。 那几天,郝山最吃香了,吃香得让人眼红。这个找郝支书,那个找郝支书,蜂王一样被围着转。但吃顿饭抽根烟可以,给好处的话一概拒绝,是什么树就卖什么价钱。从当支书之日起,他就给自己立了规矩,干啥都成就不能捞油水。这屁大的官不会当一辈子,这屁大的村却要呆一辈子。 当支书十多年了,他能做到不捞油水,自我感觉也不容易。如今当官的,哪个屁股上不别着笊篱?穷山沟虽没球好捞的,但发个他不成问题。可正因为他没发,才说话硬气做事硬气,站在老柳树下吼一声,老老少少没有不买帐的,早打算不干了却非让干不成…… 郝山坐在地里,像晚上睡不着一样,检点起所做的事来,心里总是坦荡荡的。在他手里,山上的树是砍光了,可通村的路修起来了,吃水井也打起来了,样样差事应酬得都不错。唯一的遗憾是,卖下树的钱有一分花一分,有点像寒号鸟垒窝得过且过,不懂得办个企业什么的,不知往后的日子咋过? 那遗憾,时常像皂泡似的泛起,但远不会影响他的情绪。他更引以自豪的是,自认比哪任支书都重视教育,觉得只有娃们学好了有出息,走出这深山老沟才是根本。于是,把村前村后仅存的一些树,除了老柳树没砍都砍了,硬是东拼西凑地盖起了学校。在全乡不算最好的,可也是屈指可数的,只有两个大村学校比得过。 学校就在对面,郝山一脸骄傲地望去,像将军欣赏一座工事,像老板欣赏一栋别墅。这样的欣赏,他已记不清几次了,把心都熔到了里边。有时在早上,有时在傍晚,有时在近前,有时在远处。村干部会上,包括刘福也在内,都说把学校盖成了庙,是不是有点太铺张了?他说那有啥铺张的,就是要把学校盖成庙,让老师跟方丈一样尊贵,让娃们跟和尚一样修行。人人敬仰,人人烧香。 他给村干部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老话说得一点没错儿。现在你们瞧瞧,从衙门里大小当官的,到社会上这老板那经理,哪个不是读书读出来的?人家之所以吃香的喝辣的,诈你也能诈出个名堂,就是因为肚里有墨水儿。我们却有谁正正经经读过书?开点窍的大字识几个,不开窍的一摸两眼瞎。在这山沟里,我们已经窝得够恓惶了,还再能让娃们窝下去? 盖学校的时候,他院里的两棵大树,自己盖房都舍不得用,可当学校木材不够时,连迟疑都没打就砍了。又亲自把树抬到学校,中途从山上滚下来,差一点儿被摔死。他觉得树砍了会草似的长出来,而人荒了是几辈子的事。要不,咋说十年树木,百年才树人呢? 阳光触摸着郝山的光头,触摸得像瓶胆似的闪亮。无论怎么讲,这学校盖对了也盖好了,是他活了近半辈子,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情。相比之下,其它胡七糟八的事,不干不行干了也扯鸡巴蛋,真正没啥可夸耀的…… 刘福一去两三天,女人几次来找郝山,我家里忙得要死,你把他打发哪去了?郝山起初懒得回答,明明知道干啥去了,偏要不停地来找。被找急了就说,你有完没完?可刘福女人就是要找,又在老柳树下拦住说,他如有个三长两短,你姓郝的顶替呀? 那意思,刘福就像给黑办了,或者上吊跳崖了。郝山正揣抚着老柳树,他不知这女人过去挺腆腼的,现在咋变得越来越歪了?好像猪走花,或吃上性药了。他转过身来说顶呀,你是想咋呢?刘福女人被噎在那里,剜一眼说看那球性气,你想顶老娘还未必呢。说罢一扭头走了,郝山望着那紧绷绷的臀部,像盯着母羊的尾巴一样,琢磨怀羔了没有。 刘福回来时,坐着表哥的小车。破自行车塞在后面,车盖儿大张着嘴巴,像豺狗叼着一只黄羊。同来的自然还有刘福表哥,一下车就抱住郝山的手直摇晃,像久别重逢似的。他说以前没注意,这次来才觉得那路真修好了,干了件行善积德的大好事,要是以前的话这小车的胎早炮了。 刘福的表哥姓许,学校的工程就是他干的。郝山让姓许的来干,一是花多花少刘福清楚,甭以为自己贪污了什么,两颗头尿不到一个夜壶。二是碍着刘福的关系,他不能不把学校建好,真有啥也一根线拴三只蚂蚱。从目前看,学校建得还算满意,可就是姓许的当初揽活时,笑嘻嘻的一口一个好说,到后却啥都不好说了。 碍于刘福的面子,郝山不好砍性子,可也认定无商不奸,自己土包子差了一码。姓许的不让叫老板,也不让叫许经理,让称呼许老弟。什么许老弟,他直呼其名不成,就叫许包工的。说你觉得好走,就多跑上几趟,胶皮轱辘跑不瘦,可封条保不定哪天就撕了。 姓许的听出不满,立刻推上郝山走走走,老哥心里甭有啥过不去。许要去刘福家,郝山拽住脚说,商量事就到队里。这也是他的一条规矩,免得女人们在跟前瞎掺和,再就是那样郑重其事,作支书的像个支书的样子。许只好说,福子那你先回去吧,把车里的东西拿上,让弟媳先去给准备。 队里就是村委会,两间屋子涂满泥巴,蔫得像一顶破帽子。可屋里收拾得干净,正面墙上挂了许多奖状,都是郝山当支书捧回的。有镶玻璃框子的,有光是纸片子的,有县里奖的也有乡里奖的。什么修路建设先进村委,精神文明五好村子,什么尊师重教先进集体,计划生育模范党支部。玲琅满目,看了挺荣耀,像温州人推销产品。 办公桌是两张课桌对起来的,正面摆了一把油漆驳落的太师椅。郝山坐到椅子上说,我叫你来的意思,福子大概也说清楚了,想要老柳树给你。但你得立个字据,不是立抵多少工钱,是立给了你老柳树,就要把封条马上撕了。剩下的营生,围墙和百十级石阶,你得赶秋天修起来,工钱也能缓一时半刻。答应就成,不答应咱就吹,挨下咋办就咋办。 许掏出烟说,近来咱们咋了,一见面就抬杠,不这样好不好?买卖不成仁义在,况且咱哥俩合作得挺好。凭老哥的面子,又有福子的关系,爱啥都好说好办,就是不给老柳树,我也得把工程干好。至于剩下的工钱,老弟不能说不在乎,可也百儿八十万经手过,你几三个钱算得了什么。用时下的话说,干啥都有个游戏规则,那封条不过是贴贴罢了。你老哥真撕了,兄弟又能怎样? 姓许的便把话岔开,盯住郝山放声笑道,老哥肃了脸坐那里,你猜头光蛋蛋的像谁?不等郝山回答,就前仰后合地说,像电影里的蒋光头。郝山被说得也笑了,抚摸着头说你少扯蛋,甭嘻嘻哈哈嘴上一套,又嘻嘻哈哈嘴下一套。咱丁是丁卯是卯,你到底是立不立? 立、立,立还不成?许止住笑,叫郝山找一张纸,掏出笔马上写好。全依你的意思,就看老哥行不行?那字龙飞凤舞的,郝山看着便眼花,还有个别不认得。他挨个儿琢磨半晌,说不亏当老板的,像学校先生写的字,还有点换鹅人的味道。不敢、不敢,许说我跟老哥一样,文昌爷下也没磕过几头。可说着又懵了,先生就先生吧,还什么换鹅人?郝山便激了眼,换鹅人就是王羲之,你连这也不知道?他字写得不错,换了一大群白鹅。说着嗤的一笑,心想以往倒把你抬高了,觉得他妈夹皮包坐小车,牛×烘烘的不得了。 姓许的一拍后脑勺,噢——,知道了知道了,就是那个什么来着?什么来着来,你看我这记性。郝山一脸不屑,说王羲之就是王羲之,还什么来着?许又拍拍后脑勺,赶紧说那是的那是的,不是王羲之还能有谁?他没想到,这土包子还知道个姓王的,就肃然了问您看那字据行不行? 王羲之换白鹅,郝山也是过年时,叫老师写春联听来的。今天居然排上了用场,可也用出了一身冷汗,若再问王是哪个朝代的,什么地方的人就蔫了。他觉得自己也学会了诈,便说那是字据咋不成?说罢了却有些心虚,毕竟有个别字还没认出来…… 两个人斗嘴时,刘福就已经来了。一听屋里有说有笑,左一个“戏子”又一个“戏子”,便悄悄地候在屋外。表哥这几年包工,在外多见了世面,成天泡在饭店里,还风闻养了个小的。相比之下,自己是天壤之别的无能,一个女人都伺候不如意,叫尿的时候咋也不上劲,不叫尿的时候却流了。 这次进城找表哥,刘福想顺便看看。他在几家门诊前转来转去,要么打量着就是不敢进去,要么进去了也支吾不出个究竟,或者一听药价就赶紧逃出来。一位老乡医告诉他,想省钱治病的话,就是每天晚上睡下,用手搓抚睾丸一百次。听了老乡医的话,他回去当晚就搓了,可仍是该来时不来,不该来时却猛地来了…… 刘福还有个隐衷之处,是郝山做事从来干净,这次盖学校更是如此。每次表哥给点好处,都两手一推拒绝了。可钱也好东西也好,表哥又不能再拿回去,说他不要你就留下吧。两个人龄虽差一码,但一直相处得不错,现在又一块搭班子,老这样咋成?于是每次表哥来了,他就尽量回避着,或许背过自己后,给点什么会收下。 刘福听再无要紧的,便进屋说饭做好了,没别的就回去吃吧。许立即说没了没了,拉起郝山走走走,咱俩今天好好喝一盅,看看老哥的酒量到底咋的。郝山一趔脖子笑道,你成天他妈饭店泡,我咋能敌过你? 回到刘福家,一桌饭菜早摆在那里,女人忙得一头水一头汗。她拿上酒水来,叫赶紧吃吃吃,甭客什么套了,谁认不得谁?郝山边入座边笑,说福子己经回来了,再甭天天找我的麻烦了。女人砭一眼,回答那倒不一定,看我乐意不乐意。 姓许的不解其意,郝山便告诉咋回事儿。许立刻笑道,都是我的过,都是我的过。那天恰好出门了,难怪我们福子老实,硬是等到我回来了。刘福用牙掀开瓶盖,说茶无眼淡如水,人无势不如鸡,不老实咋呀? 郝山听得有点懵,啥茶无眼淡如水,人无势不如鸡?他不知有意无意,还是真冲谁来的。见酒倒得要溢出了,就拿手挡住说,得啦、得啦,又不是喝完不喝了?。许也莫名其妙,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三个人像打隐语似的,不知葫芦里卖什么药。他猜不出个究竟,就以为得罪下了表弟,忙端起酒说来来来,为我们福子辛苦一趟,干一杯。 表哥又扯哪去了。刘福举酒抿一抿,问郝山我喝了吧?郝山嗤的一笑,那是你兄弟俩的事,我还知道喝不喝?刘福很是无趣,一仰头自顾闷了。他又倒上酒说,若要喝好先把东家喝倒,我跟你们每人来一杯。 那样子,许更以为得罪了表弟,说罚我两盅罚我两盅。那天我实在有事,要不福子去了咋能找不见?我娘死得早,我是姨拉扯大的,我能有今天全亏姨了。对别人,我都点水之恩涌泉相报,更何况自家人呢? 相关专题:浙江安吉生态文化节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浙江安吉生态文化节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