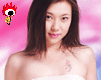新周报:从暧昧到阳光的中国艾滋病政策(2)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01日09:37 新周报 | ||||||||
|
NGO的组织源头 11月26日晚10点,当记者打通艾滋病感染者宋鹏飞的手机时,他喘着粗气说,他一直在地库里忙着搬东西。第二天,他将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推出自己的绘画作品展,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官员、国际非政府组织代表等将参加这次画展。因去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一次拥
2001年那次河南之行之后,宋鹏飞逐渐从万延海的爱知行动项目中脱离出来。作为一个知名的艾滋病感染者,他利用自己在海内外的影响力组建了一个新的NGO“笑看未来”艺术作坊,将一大批艾滋病感染者团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艾滋病民间自救组织。 李丹没完成在北京师范大学天文学的研究生学业,作为早期参与爱知行动项目的成员之一,他于2002年下半年脱离了已合法注册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之后,他与几个志愿者组建了“东珍艾滋孤儿项目”,在河南等地的艾滋病高发区对艾滋孤儿实施帮助。2004年春,“东珍艾滋孤儿项目”在北京工商部门注册,整合为一个健康教育研究所。 爱知行的另外一个成员在离开爱知行后,联合北京、上海等地的志愿者在北京登记了“北京爱源汇健康教育研究所”。 在中国,一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正在形成自己的团体,一部分社会上的有公益之心的人、一些从环保等领域转过来的志愿者亦在组建为艾滋病人群提供帮助、为社会艾滋病干预工作的NGO。 11月24日,另一个艾滋病患者协会“红树林组织”创作的电视纪录片《我们的生活》在北京举行了VCD首发仪式。这个组织的创始人是从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艾滋病感染者小李。2002年,小李获得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发的艾滋病预防宣传奖。在第17个国际艾滋病日来临之际,“红树林组织”出版的《挽留生命——来自艾滋病人的口述实录》在北京的大学校园里进行慈善义卖。 “中国艾滋病防治领域让世界瞩目的最大新闻不再是河南农民因为卖血患上艾滋病,而是一群曾经因惧怕死亡和社会歧视而处于社会边缘的艾滋病病人勇敢地承担起新的社会角色,动员社会力量抑制艾滋病的传播。”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国家协调员雷诺舟博士这样评价。 几乎每一个中国内地省份都有艾滋病感染者自发成立的组织。在河南艾滋病高发区的农村,大部分村庄的农民成立了类似于“互助组”形式的组织,以便于接纳药品援助和经济援助。在上海,一部分因使用血制品感染艾滋病的血友病人成立了“中国血友病人之家”,以法律的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而由健康人群参与的NGO也在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你只要进入一个艾滋病高发区,或者接触到一个艾滋病易感人群,就可以看到有NGO的人在工作。”一位长期从事NGO的工作人员说。
“我们是政府的伙伴” 总部设在比利时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是世界知名的NGO,长期为贫困人群提供健康领域的帮助。2003年开始,无国界医生组织尝试着在中国的艾滋病高发区进行工作。该组织有一个规定,无论是在哪里工作,都以取得当地政府的许可为前提。经过努力,该组织在湖北省襄樊市开设了第一个艾滋病门诊。 2004年春,无国界医生组织北京办事处试图在河南某县联络建立艾滋病治疗机构。开始该县的反馈很积极,无国界医生组织按照惯例提出由该县政府以书面形式确认许可,但县政府和卫生部门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认为,如果允许无国界医生组织开设治疗机构,是否会使当地的艾滋病真实情况公诸于世?无国界医生组织北京办事处最终没能等到该县的邀请函。 “爱知行”和李丹、宋鹏飞等人也都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在得到政府许可的前提下开展工作?2004年7、8月间,李丹和一些志愿者多次前往河南商丘等地,为艾滋病孤儿交纳学费,为一些病人送去免费药品,但每次都会遇到当地的阻拦。 不被认可,不被理解是大多数在艾滋病高发区开展工作的NGO所遭遇的共同难题。 “可这些与注册之难比起来又微不足道了。”万延海之所以后来选择在工商部门注册,是因为他实在无法走通真实意义上的NGO注册,虽然在工商部门注册将为“爱知行”在获取国际支持上带来种种不便。 20世纪80年代末,民政部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照此条例,NGO必须有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的双重管理。1998年,此条例重新修订后出台,仍坚持对社会团体须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要求,同时,对团体的活动场所、资金来源等硬件要求更加明确。然而,很多NGO难以找到可以挂靠的单位,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工商部门以研究所等名义注册,但这样很难获得社会捐赠和减免税待遇。 许多NGO还面临同样一个难题——资金。在北京,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每年能够筹到的款项是4、50万元到7、80万元之间,而在香港,一个乐施会每年筹到的款项就达9000多万港币。 2003年,“爱知行”筹到的款项包括英国大使馆、欧盟和美国一些科研机构的捐赠,总额为十几万美元。宋鹏飞认为,艾滋病民间组织在寻求社会认同和帮助时,经常会遭遇国内各行业的不理解与不合作,相反,倒是国外企业和公益性机构更愿意伸出援手。 一些专家认为,政府之所以对NGO管理一直偏严,主要是担心民间活动失控,公益捐赠立法的滞后则与税务、财政等部门担心税收减少有关。邓国胜认为,目前NGO管理如果放开,确实难免混乱,NGO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很多NGO过多照搬西方的价值观念,过多依赖少数的精英人物,较少利用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 雷诺舟认为,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当务之急是在政府高层推动的基础上,鼓励个人和企业树立公益文化观念,主动参与公益事业。 “中国的艾滋病运动已经进行到了突破瓶颈的阶段。”万延海说,这个瓶颈就是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合作。 “如果要战胜艾滋病,中国必须改变传统偏见和保守态度。在艾滋病面前,人人有受到保护的权利、获得资讯和服务的权利,有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福特基金会是一个美国NGO组织,自称倡导平等和社会公正、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保护多元性的该会高级项目官员高芙曼(Joan-Kaufman)女士说,“保障每个中国人不受艾滋病侵害,需要坦诚的创新的方法。” (《新周报》驻北京记者 喻尘) 1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吴仪在中国职工红丝带健康行动启动仪式上强调,防治艾滋病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局面,共同筑起防治艾滋病的钢铁长城,坚决遏制艾滋病在我国的流行和蔓延。 此前,河南省卫生厅长透露,该省从既往卖血史人群中普查出2.5万HIV携带者和1.1万余名现症病人。 从2002年以来,有关中国艾滋病的信息表明,中国官方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勇气正视艾滋洪流。 握别暧昧和被动 2003年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地坛医院将手与艾滋病人的手握在一起,外电对此的高度评价是:“可以看出,中国握别了一个艾滋病暧昧和被动的时代。” 自1985年中国内地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国际上对艾滋病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舆论,长时间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应对政策。在当时,如果承认艾滋病问题,被视为是给地方政府抹黑,而“泛道德化”则使普通人群认为艾滋病“是和不好的生活方式相关的病”。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无论是在中国官方,还是在民间,艾滋病都是暧昧和不光彩的字眼。 温家宝总理与艾滋病人亲密握手之时表示:中国政府将以负责任和更加开放的态度,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探讨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良策。 政府态度的转变标志 标志着中国政府对艾滋病转变态度的举动是2001年11月13日,中国第一届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的召开。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测算数字:到2010年,中国艾滋病感染人数将达到1000万人。国务院办公厅是年下发的《中国遏止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制定了到2005年度的工作目标,此后,一系列积极的艾滋病治理政策开始出台。 另一个变化是,经费投入逐年增长。1996年,中央财政设立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第一笔为500万元,此后三年每年1500万,而2001年之后,每年的费用猛增到1亿元。国债安排和地方配套的艾滋病资金从2001年以来更是累计投入达40亿元以上。 2003年底,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视察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后,专程在郑州与以防治艾滋病著名的高耀洁医生闭门长谈3小时。直到今天,高耀洁还不愿透露3个小时中究竟谈了什么,但这次长谈被认为是对“艾滋病影响地方经济”的否定,是艾滋病防治领域“政策腐蚀科学精神”的结束。 2003年3月6日,河南、河北、贵州等11个省的卫生厅长齐集北京,与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签下了“建立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项目责任书,中国首批51个县市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正式启动。 国际合作水到渠成 对艾滋病“泛政治化”的放弃使得国际合作水到渠成。2004年4月6日至7日召开的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是自1996年以来最高规格的相关会议。尤为特别的是,会议邀请了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协调员雷诺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副代表倪荣国参加。这是国务院组织召开的、第一次邀请国际组织代表参加的工作会议。 2004年8月25日,全球基金与中国卫生部以及一些NGO组织签署协议,中国将在未来5年内得到近1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在7省58个艾滋病高发贫困县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关怀和预防的综合性活动,以建立可在中国其它地区推广应用的治疗关怀模式。 法律的准备也在紧张地进行。2004年7月11日,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出席第二届亚太艾滋病部长级会议时表示,《传染病防治法》正在修改,社会对艾滋病的高度重视和反歧视的有关条款将被写入,而原有的“对发现的艾滋病病人要进行强制性隔离治疗”条文将被取消。 (《新周报》驻北京记者 喻尘) 相关专题:2004世界艾滋病日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2004世界艾滋病日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