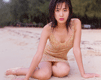台湾美丽政坛女姓陈文茜:希望陈水扁被打败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6月24日16:36 南方人物周刊 | ||||||||||||
|
5月20日,在凤凰卫视录制完节目后,陈文茜一扭一扭地带记者到她入住的酒店,浓妆犹在,蓬乱的火红女巫头,白色的绣花短裙,千娇百媚。窗外是波涛滚滚的维多利亚港。她斜靠在沙发上,美丽、优雅,透着成熟和智慧。 为了接受我们的专访,她在这次的《解码陈文茜》节目中特地选取台湾立法院3位美丽的女性,展现台湾政坛女姓的独特风采。正如英国女作家伍尔芙所说,每个女人都要有一个
我的人生就是办大事 人物周刊:去年12月,你宣布退出政坛,转入文坛,在从政十多年后,为什么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 陈文茜:那太浪费时间、浪费青春了,一群人每天都在搅和。我在政治活动中觉得那样实在太耗费人的生命了,看起来权力很风光,常常什么也没有留下,一片空荡荡。我现在人到中年晚期,快50岁了。一个人的美好时光是中年,不是年轻的时候,青春是美好,但那是感觉,抓不住东西,因为你的智力和地位包括钱都是不够的。其实女人是最晚认识自己的。20岁的时候你觉得在看,30岁的时候你觉得在学习,40岁的时候你定型。女人真的把生命把握住,就在45到50岁。 我在台湾10年了,都是在说话,人人都看着你,好像什么都没有留下。文字还是有它不可超越的地方,我现在花蛮多的时间在写东西。“立法委员”不做了,应该像李敖一样,70岁的时候再去做,那时候进养老院太早,做别的事情又太花力气。 人物周刊:你现在会不会后悔以前从事政治工作? 陈文茜:不会。以前所做的政治工作给了我很大帮助。现在回过头来做一个比较,相对于平凡的男男女女,我发现他们特无聊。我就在想,他们怎么就会被小事所困。政治工作让我和一般人不一样,我的人生就是办大事,不会被小事所绊。我也很庆幸,我是一个成功的女人,所以有时候,遇到事情,哦,小事一桩!你不会觉得恐惧。大多数人都有进取的精神,可是最后消耗他的意志力和进取心的最主要的是恐惧,恐惧改变,恐惧被批评,恐惧人生有很大的变故,你一旦把恐惧消除,就会不一样。我觉得政治训练了我,大风大浪,我看过了,也可能去坐牢,也可能会翻船,每天都生活在新闻焦点里,周围有很多政治风暴,主导很多的事情,改变很多的历史,最后的结果就是:你经过这么多大风大浪,小事情难不了你,你不会为小事所困。 人物周刊:如果去年选举中泛蓝赢了,你是不是可能就不退出政坛? 陈文茜:没有,我当时就想去写作,我说过我想要的角色是辜振甫那个位置。和政治有关不是长远之计,你很难说辜振甫是一个政治人物,但他在政治里头的表现和留下的历史地位,在台湾比谁都高。当时我说,如果连战赢了,我要做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因为辜振甫也老了,我要接他的班,定位很清楚(笑)。既然我身处两岸目前的形势之中,就立刻转身去了凤凰。山不转水转。所以选举结果出来的时候我就说,第一政治的工作我不做,第二我不再把重心放在台湾那个小岛上,要放眼来看问题。 人物周刊:但是最后结局是出人意料的,这对你来说,算不算是一种失败? 陈文茜:(思考)这很难讲。台湾政治基本上已经搞得乱七八糟。以前台湾还没有“大选”,还有希望把陈水扁赶下来,那好吧,我就留下来。但那只是个假象,台独力量那么强,你每天都在消耗。就算赢得政权,也什么都做不来,因为两方势均力敌。我觉得对台湾岛上的民众来讲,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这次选举)是个失败,是个遗憾。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如果那次不输的话,我不会对台湾彻底绝望,我会觉得还可以为它做点什么事。 我对选举结果最失望的不是枪击案,因为枪击案顶多骗100万的票,怎么会有五六百万票投给他?一个人到了这个地步,整个社会被他搞垮,军事也被他搞垮,什么东西都被他搞得一无所成。天天这样骗,还有五六百万的人投票给他,我对这个社会真是太失望了。他们是要把自己的命运放在这个臭水沟里,闹得没完没了。 人物周刊:所以你对台湾的政治失望了? 陈文茜:没有失望,台湾政治走到现在从来都没有移动过。移动的只有连宋来大陆,其他事情都是天天闹,天天一样,陈水扁天天骗你,今天骗你A,明天骗你B,骗来骗去,你发现自己还在原来的位置,根本没有动过。不要说枪击案没有破,选举案没有结果,经济也在原点,两岸关系也在原点,世界贸易也在原点,没有一件事情不在原点。只有我们一天天老去,台湾在这个地方静止不动,毫无进步可言。一个社会消耗起来是很惊人的。 最近我在读清史,最后一个倾向西化的君主是康熙皇帝。中国辩论西化很久,从乾隆拒绝英国公使马嘎尔尼开始,到最后的慈禧,都在讨论一个“西化”的问题。她也知道,要自强运动,要建立新的经济制度,要建设海军等等,但是她面对一个强大的反“西化”的势力,不敢走得太远,害怕失去自己的权力。最终的开放,已经到1979年。从乾隆到邓小平,很久很久(无奈地笑),两百多年。一个社会可以空转这么多年! 人物周刊:选举失败后,民进党说你是压垮连宋的最后一根稻草,还记得当时说了什么?对于这种说法觉得委屈吗? 陈文茜:不觉得委屈,你反对人家,为什么人家骂你还觉得委屈?当时说那个枪击案是假的,那是很严厉的指控。当时我们已经讲好,我做黑脸,马英九做白脸,大家都是在演戏,有什么要生气的。本来说好是我和马英九一起做黑脸,连宋做白脸,但是他明哲保身,改做白脸。泛蓝不能原谅马英九在枪击案中的懦弱表现,到现在为止,我都不跟他做对话。政治里头,一个站在高位置的人,你做决定还是不做决定,你说话还是不说话,都会被评论,除非你不参加重要的会议,站在边缘。我现在是台湾最没有争议的人,因为我不做事啦,不做事就没有争议啊,是不是?你现在在网络上找不到几个月来任何一句对我批评的话,你不重要就没有人骂你了。 我命定要对抗邪恶的势力 人物周刊:你从大学时代就介入政治运动,是受哪方面的影响? 陈文茜:个性。我们现在讲星座,我是牡羊座,成龙也是牡羊座,他说台湾的选举是个天大的笑话,然后被人骂,所以他说4年都不去台湾,他个性就是这样。还有那个拍《星传》的导演,卢卡斯,痛骂布什。我们这种人,就是命定要对抗邪恶的势力(笑),天性如此。我小时候就很有艺术家天分,喜欢写作。我不只是叛逆,比叛逆要多一点。 人物周刊:所以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的发型和穿着也比较特别? 陈文茜:我回去的时候,台湾和大陆是一样的,政坛女性都很传统,穿衣服没有颜色,要么就是深色的,咖啡色,包得紧紧的,像个粽子,她们竞选的时候都拍这样的照片。当时是台湾电视媒体崛起的时候,我本来就是这样子,很难叫我改变,我有很强的女性意识,我的观点就是,如果我帮你们争取权力,你们先把我作为一个女人否定掉,那还谈什么?我的态度就是有点我行我素,可以不用像男人婆一样,可以有很多女性的个人特质,不需要隐藏自己喜欢的东西,把自己变成一个中性的角色,然后说我是一个专业的人。我就把你们这些男人比下去,告诉你们,我还要穿裙子,而且穿浅色的衣服,头发上还要染颜色。台湾的女人有一个成功的范例,而且还特别的成功,因此开始改变她们的风格,现在,“立法院”的女人每个都花枝招展,公众也比较喜欢。 人物周刊:这是你带的头啊。 陈文茜:对对。大陆的女性在这方面其实是被高度束缚的。在政治上不能提拔到很高位置,这叫“天花板”现象,碰到一个天花板,就爬不上去了。再要上来的人,你先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妈妈,一个中性的女人,要把自己全身包起来,而且讲话要非常凶悍,像男人婆一样。李永萍(亲民党“立委”)也说,讲话要骠悍,从头骂到尾,一直拍桌子,大吼大叫,如果不这样,那些男人不听你的,就是要让他怕你。 人物周刊:你在“立法院”是不是也要采取这样的方式? 陈文茜:是啊。我当领导的时候,就打团队战,因为我缺乏跟人家拍桌子吵架的个性,也不太愿意改变自己。我当“立委”的时候,和永萍她们不一样,她们年轻,资浅。我当选的时候,大家已经把我当成一个政治明星,名声很大,所以不用多说话,人家就会怕我。真的要协商要吵架,面对其他的“立法委员”,一大堆人在房间里头时,我常常叫很多“立委”坐我旁边,“9 ·21” 地震的法案我就叫李永萍去跟他们协商,去吼叫,因为她嗓门大,需要骂人就叫周锡玮,现在的台北县长。如果是质询官员,我比较管用,因为他们怕我。我天生嗓门很小,没办法大吼大叫,而且大家觉得你已经不用这样,就和李敖一样,他们觉得得罪你下场不好,所以他们火大是火大,但是还不太敢在你面前翻脸。 人物周刊:这个强势的形象是如何树立起来的?因为你经常在电视上批评别人? 陈文茜:不只电视,电视上的陈文茜给人的印象是,好像这个人什么都不怕。人们怕的就是什么都不怕的人;还有,他觉得你比他聪明,你看穿了他,他从内心里头就觉得比你矮一截,所以那些官员在和我说话的时候,会觉得我每句话里头都有陷阱,如果他随便地和我胡摆,我可能拿出一个资料证明他是假的。他还不能惹我生气,我比较火大,我会抓住他的案子,我有能力拿整个“立法院”来对抗他,而且会在媒体上攻击他,不只是在我的节目上,我有方法让所有的媒体都攻击他,他的下场就会很惨。所以他就明白了,这样的女人,不要惹。 有些事情你也要杀鸡儆猴。我刚进“立法院”的时候,就被他们用一些技巧给耍了,是一个贪污案。我当时开记者会说我要罢免“立法院”院长。当时没有人敢得罪他,都讨好他。我说,指控你跟这个贪污案有关系,我们在表决的时候你在后面和贪污案的那个人的儿子在协商。我讲话比较有公信力,然后就跑到国民党党中央去告状。他是国民党党员,连战就要他去解释,后来他就妥协了,恢复了那个案子。从此以后,凡是我的案子,他们就会说,“哦,让她过,反正最后她还是会把事情搞成。”我们不能打无限战争,一定要抓大放小,二三十个问题,我抓两三个重要的,其他的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不可能每一件事都打无限战争。他逐渐摸清了你,你这样的女人,反对你 ,就会下场很惨,那就顺着你的意思,其他的就会放了。所以你还是要有手腕(笑)。得罪你的人要让他在众人面前付出代价,有仇必报,后面的人就不敢和你纠缠。 人物周刊:你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吗? 陈文茜:不是,其实我的个性有点心软,会想算了,无所谓,后来你知道必须这样,你知道这是政治,不是你的本性,而是人性的问题。人性都是吃硬不吃软,都是欺善怕恶,所以你必须恶,必须硬,否则你怎么能在政治中生存?尤其是女性,当然不能了(笑)。像我,嗓门不大,也不会和人打架,凭什么让人家怕你啊?而你又想维持一种教养,一种形象,让人家对你有一种敬畏,你就要用特殊的手段啊,对不对?其实女性在这方面并没有那么难,你就把头发弄得这么古怪,他就会怕你了。交朋友其实也是一个手段,像我和李敖就是朋友,拿李敖出来,像个门神,把人家吓跑了,省了很多力气。 人物周刊:人们经常拿你和李敖相提并论,李敖也称你是最聪明的女人。 陈文茜:他是这样称赞我,我很谢谢他。我跟他交往有我的目的,他跟我交往也有他的目的啊。他说,他死了以后,要有人传承他的地位,怕有人鞭尸,为了延续他死后的影响力,他必须和我勾结在一起,这是李敖的说法。我也是啊,我不习惯和人打架,一开始放个门神,就把人吓跑了。还有赵绍康,一个很凶悍的广播电台的老板,在台湾也是大名人,他在节目里骂阿扁,阿扁在记者会就说,“人其寥落鬼何多”,他说阿扁骂我是鬼,所以要告。反正台湾不好惹的人都是我的朋友(笑)。你不欺负别人就会被别人欺负,这个逻辑在政治里头非常简单。 和不要脸的人玩政治要有不要脸的玩法 人物周刊:当年你从美国回来,就担任了民进党的文宣部主任,当时你的政治取向和民进党是一致的吗? 陈文茜:我当年在台湾的时候,民进党是比较民主的,讲自由和人权。我不在的那几年,台独运动发展得很快。我回台湾的时候,5月10日担任文宣部主任,12月就已经闹翻了,为了一个大和解。我主张和外省人和解,外省人指1949年后来到台湾的,他们有一个党,叫新党。我主张和新党握手和解。哇,不得了,天天骂,骂我什么“香炉”、“妖姬”,和现在大陆网民骂我一样,全部都是女性字眼。大陆网民是不赞成你的意见,但没有恨,在台湾,那真的是恨你。7个月之内,你为民进党说话,他们觉得你好光荣,但是马上就恨你。我在民进党10多年,7个月就闹翻了。一开始你不会立刻就走,你会认为自己是元老,他们都是小老鼠,都是小瘪三,国民党政权时一个个躲在家里头,现在叫什么叫。 人物周刊:这种冲突导致你离开民进党? 陈文茜:初期你觉得这不能代表民进党,后来的冲突还有政治发展表明,还真的代表(民进党)。我离开民进党那一刻开始,有人说我和陈水扁冲突啦,其实不是,我比许信良都早退出,他们后来受我影响离开。我影响他们的方法是,告诉他们这个党不是我们当初参加的党,它已经变质了,变成一个族群主义和台独主义的政党,没有人可以在这个党里头走出一个两岸和解的路。你看,到今天陈水扁也走不出来,想走也走不出来,因为他做一点点,民进党就会罢免他。当你的权力基础是一群疯子,你只能去演疯子啊,你能演和平天使的角色吗?民进党的基础是族群主义和对大陆的恨意,是一群疯子, 不可理喻。他们拒绝大陆崛起,后来大陆崛起了,他们说抢走了工作,等到后来大陆开放水果市场,又说,哦,是来收买我们的。他们否认事实,是一群神经病。在民进党内,要取得领导权,就必须代表这批人,就必须附和他们,你讲宪法一中,就会被批斗得很厉害。民进党,是换了不同的人在演相同的故事而已。陈水扁是个投机的政客,他利用这个力量崛起,想走出这个力量走不出去,于是再养大这个力量。 以前我们在民进党内的时候,这些人的支持度大概是三分之一,现在大概成长到二分之一。陈水扁把这个势力养大了。原来支持民进党的人口只有百分之十五,现在成长到百分之三十多,变成了很重要的力量,是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造成两岸不能不谈判了。民进党内已经没有任何人物,可以不附和这个力量而在自己的位置上生存。谢长廷讲宪法一中,就意味着他要倒台了。我不相信政治人物可以超越他的权力背景。除非李登辉死了,吕秀莲死了,剩下陈水扁和谢长廷,没有足够的有政治影响的人物可以领导。 人物周刊:2001年,你以无党籍身份参加立委选举,但是只当了一届。 陈文茜:情未了,缘犹在。我如果不当3年立委,现在不会走得这么心安理得。那个地方总像你的家,好像家破人亡啊。2000年台湾经济已经很糟,股票指数从1万点跌到三四千点,缩水了三分之二。我们那时候到大陆来,碰到国台办的人,说浦东也起来了,上海已经好起来了,他们说,你们怎么办?台湾经济怎么这样?好丢脸。以前台湾经济被称为“台湾奇迹”,人们总是问,你们怎么处理金融风暴,为什么你们没有事,好像是大家的模范。 政治这个行业我比别人看得穿,看起来很风光,但一下子就会一无所有。我从小在政治圈子里头,看过太多人的起起伏伏,越是风光的人越凄凉。有一个指导员,施秋镇,当时风光一时,60出头就死掉了,以前门庭若市,落选“立法委员”之后,就坐在办公室里等电话,没有一个人来看他,得了忧郁症,两个月就死掉了。 最怕没落的生涯就是政治和演艺生涯。宋楚瑜也一样啊,以前好风光啊,还不到5年光景,就全变了,直到他来大陆,才有一点昔日的风光。像我现在这样,得个狗屁小病也有那么多人关心!啊啊,所以政治不能当你的职业。你看到那时候的长辈很风光,现在是老头,站在你身边,沾沾你的场面,这样很悲凉。透过外界肯定你才是肯定自己,人家不再肯定你的时候,你能肯定自己吗?我觉得这个行业不是人干的,就像以前大陆有名的明星白光,所有的照相馆都是她的照片,到了台湾以后,风光不再,人家说东山再起吧,第一场,老客人来捧场,两三场之后,就不太有人来了,最后她到日月潭上吊自杀了。 我觉得这个行业做完之后,最适合去当和尚,遁入空门,看破一切,否则你很难自存。我现在看李敖的例子,觉得人应该倒过来,年轻时把时间花在扎扎实实、更有意义的事情上,不要浪费青春,或者年轻的时候从政,中年时候做扎实的事情,老年再回去从政。年轻时候从政好,可以给你历练,使你一开始就有紫禁城的格局,比一般人大气,不是小庙的格局。到了中年,还是要做一些累积型的事情,到了老年,进养老院之前再去从政。李敖现在满好玩的,他每天玩票,游戏,不认真当(立法委员),随便讲话质询,然后走人,大家也觉得很好玩。他每天在后面,拿个望远镜,看前面的官员,东看西看,把人家吓得要死,不知道他要干嘛,哈哈。 人物周刊:你当“立委”时,对自己的期望是什么? 陈文茜:主要跟经济有关,很多时间放在预算上面,很累,把身体都当坏了。开会要做主席,很难像李敖那样。当时我不太想从事这个工作,但感情上又有些歉疚。有个年轻人来找我,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选上。我告诉他,你用什么方法都选不上,你自杀都选不上,没有一个党会提名你,你又没有知名度。可是他觉得台湾经济这么差,如果不做点什么的话,他的下一代也完了,在这里生儿育女,一点意义都没有。还有一个女的,叫雷茜,这次选上了,她就觉得必须救台湾。这两个人对我冲击很大。 我和李敖,都是只要登记,不用竞选都可以选上。就是说你有一个机会帮社会做事,社会给你那么多掌声,对你有那么多期待,所以使你地位很高,使你倍受礼遇,使你赚很多钱,然后你一分都不愿意返还,到老了,拿个算盘算计你的人生,这样精明好吗?还是不太好吧。 后来不选也被选民骂得厉害,怎么就走了?李敖救了我,换他去。民进党的人都是一群小流氓,要让上道的大流氓来修理一群不上道的小流氓,哈哈。 人物周刊:当“立委”期间,你认为最成功的案子是什么? 陈文茜:还是预算案。陈水扁上台后,把“国库”掏空给他的金主,那些捐钱给他竞选的大老板。大的“国有企业”,以民营化为目的,变卖、贱卖,偷偷地卖,偷偷地送给他的金主。所以我一来就彻查,全部绑起来,让他们什么都捞不到。这很重要,当这些企业从陈水扁那里捞不到好处的时候,他们只有在两岸才可以得到正常的发展,就会变成一股力量回去逼陈水扁开放两岸。这群人如果可以从国库里偷到钱,就会默许他在两岸政策里头不开放,不会给他施压。我们在权力中心呆过,其实对政治最有影响力的是金钱。“Money talks”(金钱说了算)。只要是透过选举出来的政治,美国、台湾都是这样。美国可以允许石油公司做决定去打伊拉克,你就知道金钱有多大的影响力。台湾比美国更没有制度,总统简直是金主的买办,好像他们的管家,跑腿的。 我们让陈水扁和他的权力基础开始冲突,那些人对社会的影响力很大,是各个报纸、电视的广告商,当他们和陈水扁冲突的时候,统治就不稳定啊,所以必须撼动那一块。我没有能力给金主好处,那我就让他们没有好处,让台湾的“国有企业”在“国库”里搬不到东西。 我们通过了“公投法”,大陆不想我们通过,但是并不知道,已经没有任何政党可以不通过“公投法”。所以我的方法是,我通过“公投法”,但我要让“公投法”什么都不能投。所以阿扁就骂,我写的这个法是“鸟笼公投”(笑)。“主权”也不让投,“领土”也不让投,“国号”也不让投,什么东西都不能投,而且投的门槛高得不得了:所有公民数的一半。那时候连宋都很担心,我告诉他们,不要怕,他的公投一定会垮的,前面那些公投都是假的,因为我要全体公民数的一半,那你怎么投?投票率都只有8成,所以你只要有3成的人反对,他就输掉了。你蓝军都拿不到3成票,他拿五六成,你输了也应该啊,就认了吧。5成对5成,你只要3成,因为一定有2成的人不投票。这就是“立法”的技巧。 “公投法”大部分是我写的,我们都是念法律系的,陈水扁也是。我表面上给你这个东西,但后面都是假的。陈水扁后来加了一个防御性公投,大家都很紧张,但我说,紧张什么,他一定输掉的,他后来拿那个防御性公投去作弊,是另外一回事情。 人物周刊:你好像对陈水扁非常了解。 陈文茜:不是了解,是看穿他。那个党是超越不了族群主义的。陈水扁是一个恋栈权力的人,是个纸老虎,很多人定位他是台独主张。他没有台独主张,只是一个“Paper Tiger”,你觉得他是个老虎,他假装是个老虎,你觉得他是张纸,一戳就破了。那就要跟他赌,看谁被拆穿。还要认识到,这个人没有面子可言,我们正常人两分钟前讲的话,现在变了总是很丢人的,他的字典里没有丢人两个字,他脸都不要了,所以你和不要脸的人玩政治,要有不要脸的玩法。 人物周刊:你和他私交怎样? 陈文茜:我从以前看着他一路骗。他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大家对他了解不多,或者说对民进党还有期待,有人经过了事情还原谅他。我从美国回来,在民进党处理一些事情,看到他,在楼上说一段话,在楼下就变脸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根深蒂固,核心是个骗子;第二他是个纸老虎,没有任何信仰可言;第三他是代表那个党,他只爱权力,只爱钱,就超越不了。不要和他打交道,不用,也不需要。 人物周刊:去年,你尽力帮助连宋选举,为什么? 陈文茜:我希望阿扁被打败,不希望他赢,他赢了,台湾就完了,两岸的战争就无可避免。你懂我意思吗?去年的选举,是台湾内部最后一次机会用自己的力量去结束陈水扁的命运,所以选举一完,我就跟国民党的一些朋友说,从此,遏制陈水扁的力量就在北京和华盛顿,所以这次连宋访大陆,就等于北京和华盛顿出手。 不期待也不反对爱情 人物周刊:在台湾你有很多争议,有很多人喜欢你,也有很多人恨你,你如何去应对那些反对的声音? 陈文茜:从来都置之不理,又不是什么大事。10年来这种一次一次的攻击很多,他派一些不入流的打手来攻击你,你理他就上当了,不要理他。 人物周刊:你看起来比一般人坚强许多,而且好像不容易受伤害。 陈文茜:我觉得我比平常人更能看穿世界,所以我不会被掌声迷倒,也不会被风雨击倒。我学历史,学哲学,所以我很清楚背后是什么,未来是什么,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迷惑。陈水扁是一个那么有权力的人,你骂他,他会不还手吗?你对抗那么多有权势的人,人家不会回头来修理你吗?你敢站在第一线,你就不敢承担第一线上应该有的伤害吗?人可以选择明哲保身,也可以选择勇敢。勇敢的人不仅仅是敢说话,还要勇敢承担伤害。 人物周刊:你也会有流泪的时候吗? 陈文茜:我不太属于那种人。可能因为我是女性,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就是人们眼光特别盯在你身上,对你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特别在意;好处是很多人攻击你的时候,会有很多人特别心疼。我和马英九被攻击的时候,没有人心疼他。你被攻击的时候,心疼你的人很多,好像你是他们家的女儿或者姐妹,都来照顾你。恨你的人也特别多,好像非消灭你不可。说起攻击陈水扁,你看台湾,有比我骂得更凶的人,但是好像没有什么人恨他,不像我承担了这么多的恨。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承担这么大的关切和掌声。具有煽动性格的人,一站在台上,就有很多人喜欢他;而比较平淡的人,人们对他的爱恨就不会那么强烈。基本上我是一个煽情的人,我的讲话和文字都是,语言模式也是,特别容易引发正反两极的反应,很难活得很平和。 人物周刊:有报道说你在选举中离开台湾的时候哭了? 陈文茜:哪有?台湾的媒体想写剧本!我有什么好哭的?离开的时候,连战已经有20多万票,到韩国,我一看到那个投票,就和李永萍——她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台湾我不要了。如果陈水扁做这样的事情,都可以得到这么多选票,这个地方我不要了。所以,我就来香港,去学校,教书,走就走了。 人物周刊:据说你养了很多狗? 陈文茜:对,5条,都取了很好玩的名字,拟人化的。有一条蒙古狗,叫成吉思汗,像员外一样,很胖,带它出去,它就很害怕,躲在椅子底下,和它的名字完全相反;还有一只狗是李敖送的,李敖以前在台湾有个节目叫《李敖大哥大》,所以狗的名字就叫“李敖大哥大”。李敖竞选的时候,宣布我当他的竞选总干事,大家都来访问我,我说我是总干事的妈,李敖登记的时候我带着“李敖大哥大”去,结果新闻出来都是那只狗,不是李敖。(笑) 人物周刊:你在杨振宁先生结婚时写过一篇关于爱情的文章,你现在还会期待爱情吗? 陈文茜 :不会吧,不期待也不反对。爱情没有重要到你需要去追求它,也没有重要到你需要去反对它,我的人生哲学就是这样。很多女性主义者说,我反对结婚,可是她们花太多时间去谈论感情了,所以感情的得与失对所有女性来说,都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该不该得,该不该失,对我来讲,它比换一个城市居住的影响还要小。我觉得这是人生的一部分,就是一部分。 结婚是一个承诺,而且你和对方结婚,也是要建立比较久的关系,除非你很有把握,否则你不要掉进去。大多数人结婚很简单,离婚就很难。现代人结婚很容易,可是离婚,好像杀了200刀才能做到呢。其实男女关系,或者说爱情通过婚姻取得约束可能是非常大的包袱,如果是爱情的话,合则来,不合则去,事情会简单很多。 人物周刊:我看过报道说你承认自己的感情有3次? 陈文茜:他随便写的,我不会谈论我的感情的。不太可能我活到四十多岁,才只有3次,我16岁就已经完成3次了(笑)。 本刊记者 陈静 相关专题:南方人物周刊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南方人物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