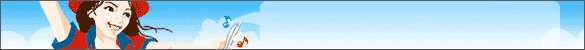南方周末:中国最大的日本战犯改造营揭秘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4日11:16 南方周末 | |
|
6月27日,大河原孝一再一次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想起了自己55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心情。 “刚进来时,我们都很紧张,怀有强烈抵触的情绪在这里生活。我们想,战争的责任是否在我?在谁?为什么把我们关押在这里?我是其中最反抗的一员,”83岁的前日本战犯大河原孝一回忆说,“改变思想就是改变灵魂,这是一项深刻、艰巨的任务。” 如今,他是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副会长的身份重返“再生之地”。被遣送回国后,他在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真正的日中友好,要从向中国人民谢罪开始。”站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台上,大河原孝一的视线飘过台下的听众,声音略显激动,“今天,我被招待到这个地方来,感到非常光荣,并且想,这是不是一个奇迹呢?” 6月27至28日,抚顺战犯管理所举办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与会的中方人士有管理所当年的管教员、看守员、医护人员等;来自日本的访问团共计54人,包括大河原孝一在内的4名前日本战犯、“抚顺奇迹继承会”会员以及一些热心人士,其中几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尤其显眼,访问团成员的年龄跨度超过60岁。 “回日本50年,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什么事情。”另一名前日本战犯岛亚坛发言时说,“我做了版画,举办画展,题目是‘三光’政策。在右翼势力非常嚣张的情况下,我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我想,如果我被杀了,这也是我对中国人民表示认罪的一个行动。这50年,我的心情没有改变。”85岁的岛亚坛缓步走下讲台的时候,听众席上的一个日本女青年在擦眼泪。 谢罪之旅 两天的会议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有14项之多,记者印象最深的是6月28日随“和平之旅”访问团参观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馆内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片焦土,堆积着被烧黑的累累人骨。空气沉重得让人屏息闭嘴。眼前多具遗骨保持着临死前张大嘴巴的样子,3000多人的一个大村子就这样一夜之间消失了。 纪念馆工作人员问访问团是否需要在馆内继续讲解,“继承会”会员、该组织目前惟一的华侨代表李楼摇头说“不需要讲解”。在这里语言是多余的,随团一些人在用自带的摄像机默默记录,他们献上的花篮挽联写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在山东作战时,直接杀害过手无寸铁的农民,我永远也不能忘,”大河原孝一在纪念馆门前开口对记者说,“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一个很好的人,杀他没有理由,就是命令,旁边还有很多比我年轻的士兵,我不能表示软弱。那个人一定有家庭、有孩子,但是我不知道。” 战前是农民的绵贯好男也有终生不能忘却的记忆,他说:“大概是在1945年2月,在中国的南方,我们把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大约3万人集中在一起捆绑起来,每个士兵分配八九个中国人杀死。这是我经历的最残酷的一次,情景惨不忍睹,那是3万人啊。这也是我最后悔的事情。” 同一天,访问团还在战犯管理所参观了《侵略——三光》画展。30幅黑白色调的版画是岛亚坛根据自己亲眼所见创作的,标题有《示众枭首》、《强奸》、《扫荡》、《三光》……他在每一幅作品前为大家讲解。画面上的日本侵略军全是骷髅造型,隐喻他们为战争恶魔。 岛亚坛在讲解他的画作时说:“日本士兵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就是忠于天皇、武士道精神。当时在中国作战,杀中国人、杀八路军,心理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并且我们来中国侵略被说成是帮助中国统一,中国人民会从战争中解脱出来。” 战犯管理所现任所长侯桂花为筹备这次活动刚去过日本,“还能活动的只剩二十几人了。”她说,“80多岁的老头,为呼吁反战做工作,在日本组织南京大屠杀展览、自费建谢罪碑……尽管这次活动他们都积极报名参加,但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来了4个。” 初来时都不认罪 抚顺战犯管理所几乎保留着1950年建所时的原貌。走在长长的走廊里,犹如陷进一座深灰色的迷宫。 其实,这座日式建筑正是日本侵略军建造的,它的前身抚顺典狱1936年竣工后不久即成为残害抗日志士的场所,内设绞人场、停尸房,3000平方米的运动场就是由杀人场改建的,能关押1200人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典狱长本人也被关押至此。 1950年7月,走进这里的969名日本战犯都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从西伯利亚出发前,苏军称送他们回日本,而他们也把回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命运——1945年日本投降后,近60万日本、伪满官兵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收容所,除3000 人被判刑之外,其余大部分人在劳役5年后已经遣返回国。 护士长赵毓英告诉记者,日本战犯刚进所时,普遍患有心血管病、高血压,与当时的情绪有关,认为自己必将受到严惩。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认罪。 据《抚顺市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有的日本战犯撕下贴在墙上的《战犯管理条例》,有的在监号内大喊“天皇万岁” ,还有人故意浪费粮食,甚至为不听教导用筷子捅聋自己的耳朵。 抚顺战犯管理所1964年总结的《对日本战犯中将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经过》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出场:“身穿将校服,头戴战斗帽,撅着仁丹胡,佩戴中将军衔领章,威严傲慢地走进战犯管理所,并公开向我们表示:‘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日本军人的天职。’” 藤田茂,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是35名将级日本战犯之一,他命令部下以活人作“刺杀活靶”进行“试胆训练” ,理由是“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 969名日本战犯中,属第59师团的将近300人,大河原孝一等4人昔日都是该师团的“鬼子兵”。 超常的优待 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前日本战犯绵贯好男只有48公斤重。他告诉记者,从西伯利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短短半年时间,他的体重由53公斤猛增到63公斤。 “我们含着泪工作,瞅着他们吃的饭菜心里很气愤。”齐亨隆老人在采访中几度落泪。他当时负责战犯伙食的采购。 公安部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分别供应尉级以下、尉级、将校级战犯。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吃“瓜菜代”,战犯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1960年左右,管理所为操作方便,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25元。 “每月20多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管教员崔仁杰对记者说,“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困难时期我一个月肉票只有几两的定量,饿得脚都浮肿了,下班时路过厨房闻着香味扑鼻,肚子咕咕真受不了。” 厨房最多时有十几个炊事员,工作人员大都不理解为何如此优待日本战犯,对于将来如何处理他们也都心里没数,有人一边做饭一边猜测“喂得胖胖的将来枪毙的时候才够劲”。 2005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录片《战俘回忆录》,齐亨隆每天必看。“那主要是讲日本人怎样对待战俘的,押在沈阳、东南亚的美国、苏联、中国的战俘。”他禁不住老泪纵横地说,那些美苏中战俘“骨瘦如柴不像人样,天地之差啊。我再想想我们怎么对待战犯的,越看越生气”。 认罪教育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从1950年接收日本战犯到1964年最后一批遣送回日本,又是14年,按侯桂花的比喻,战场转移到没有硝烟的思想领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有5座战犯管理所,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知名度最高,它以对日本战犯、伪满战犯成功进行思想改造著称。 “日本战犯为什么能改造过来?我的理解是,首先要他认罪。”张仁寿对记者说,“认罪是直观的。你杀了人烧了房子强奸妇女,不能不认,不需要更多道理。” “需要道理的是,这种行为是作战行为还是战犯行为,用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的尺度量罪定性,他就没话说了。”他说,“再辅之以人道教化,不认罪也把他当人看,不折其尊严,这对日本人是有用的。 最早对日本战犯进行思想教育,与两个人创造性的工作分不开。他们是吴浩然和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同事张梦实。” 据《抚顺市志》记载,周恩来指示“对这些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的时间是在1952年2月,而此前吴浩然他们就已经组织了战犯学习小组。 未能如愿上大学的大河原孝一把战犯管理所比作大学,他求知欲很强,还当了学习小组的组长,组织全组25人一起讨论。 吴浩然在生前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进行硬性灌输。而是先通过调查研究,首先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学习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学习组长……学习方法是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自己开展讨论。” 当时的学习材料主要是日文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以这部著作为思想突破口,是张梦实的提议。 张梦实,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曾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受中共地下党启蒙,产生反满抗日思想。他担任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员时,他的父亲则戴上了战犯编号牌。“儿子管教父亲”成为美谈,而他本人并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 与众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他不仅有理论素养,而且非常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帝国主义论》在日本国内是禁书,讲给战犯确实抓住了要害。 “这部著作没有什么党派色彩,写的是社会发展史,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它的本质是侵略。”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写“ 改造日本战犯工作总结”的主笔张仁寿说。 战犯痛说家史 4名前日本战犯在战前都从事着普通、正常的职业——大河原孝一是一名铁路工人;“小市民”出身的岛亚坛是一个画工;公司职员高桥哲郎毕业于“专门学校”,在4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绵贯好男是一个农民,在家以种地瓜等农作物为生。 他们的个人情况在日本兵中是有代表性的。吴浩然在生前留下的一篇回忆录中记录道:“这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为高小水平,被俘时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发现日本兵中有不少是工人出身,吴浩然冒出一个点子——他们同样受过剥削压迫,何不开个诉苦会呢。 吴浩然给大河原孝一等学习组长布置了两道思考题:对比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比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监狱。组织战犯讨论第一题时,挑选出身贫寒的战犯作重点发言,讲自己的家史。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翻阅各学习小组长报上来的‘学习情况汇报表’,突然看守员师国荣跑进屋来,大声说‘老吴,不知为什么,各监舍里都有人在哭,你快去看看’。”吴浩然在1980年代口述回忆录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成就感:“我听了却很高兴,不慌不忙地对师国荣说,‘你不必担心,战犯们的学习已经进入理论联系实际阶段,这对他们悔罪认罪有好处 ’。” 第一个痛哭的是宪兵军曹东一兵。他是佃农出身,他的家史听起来类似中国的“白毛女”。东一兵说,为给父亲治病,大姐辍学到火柴厂打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直到中了磷毒,牙床溃烂活活饿死了,厂方说大姐5年期合同未满,硬逼二姐顶替做工,父亲在病床上看到女儿被抓走,晕了过去再未醒来……讲到父亲的丧事,东一兵放声大哭,其他战犯也跟着哭起来。出身贫寒的人争着讲述自己的家史,都是边讲边哭。 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尉级以下战犯感觉,受剥削阶级才是同一个战壕的。”崔仁杰说。 吴浩然后来在在回忆录中说:“这些校级以下战犯普遍认识到,人的贫穷不是天命所致,而是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造成的;天皇也不是最仁慈的神,他是日本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为天皇效忠,就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卖命。所以,自己犯罪,应该感到惭愧!”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出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抚顺市志》引用了这组数字。 暴风骤雨式的认罪 “如果说悔罪教育是和风细雨,认罪运动就是暴风骤雨。”崔仁杰形容。 1954年,最高检察院东北工作团500余人的审讯队伍进驻战犯管理所,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开展“认罪运动”,对将校级战犯则采取“过筛子”式的个别审讯,一个个过关。 为打开僵局,在认罪运动中采取了“典型引路”的方式。第一个典型是第39师团中队长宫崎弘,他在全体战犯大会上坦白了扫荡湖北白羊寺村,如何亲手残杀几十人的罪行,当时全场听得目瞪口呆。属于积极分子的学习小组组长大河原孝一从未做过典型发言,尽管他也亲手杀害过无辜百姓,其罪当诛,但就残暴程度而言,相比之下怎么也轮不到他当典型。 崔仁杰说,认罪运动的场面很有感染力,“大家在运动场上席地而坐,典型发言时,听众有同感就会突然站起来鼓动性地说几句,也不长篇大论,比如‘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真不假,我们确实是恶魔’,经常有人喊一句‘ 多岗(日语:同感)’,然后全场齐声高呼‘多岗’,右臂高举起一片”。 “这么个会后,分组开会气氛就不一样了。”崔仁杰分析,听众心理是“他的罪比我严重得多都坦白了,我还怕啥呢,何必自己背包袱”。 认罪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很多战犯思想压力大,吃不下饭,说“认罪运动是生死斗争啊”。“彻底否定旧我、产生新我,由一个战犯到一个善良的人,转变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崔仁杰说。 “认罪运动后,一提到自己的罪行和中国宽大待遇,战犯都爱哭鼻子了。”他说。 认罪之后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大河原孝一等89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遣送回国;对45名罪行十分严重的日本战犯,分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但最终全部提前释放,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于1964年回国。 回国之后,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前日本战犯全部参加。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即使获得自由也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大河原孝一就是这样一个。 他回国后回到战前工作的铁路局继续当铁路工人,同时在“中归联”兼任副会长,从事反战、友好工作,例如护送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刘连仁回国。回国10年,他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他说:“因为我感到很对不起中国人民。” 目前,近千名日本战犯仅百余人在世。大河原孝一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50多年来在为中日友好尽一点微薄的力量,现在更感到对未来负有责任。但时间不多了,感到非常着急,非常想把反战的观念传达给下一代。” “今天参观了惨案纪念馆,想到日本国内还不承认发生过侵略战争,我由衷感到气愤。日本政府应该正视历史,特别是应该反省战争责任,对这个事情有个了断。” 本报记者 寿蓓蓓 相关报道:南方周末:日本战犯回国后的遭遇相关专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专题 > 正文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