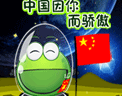巴金传:我是诚实的人吗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7日23:53 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 | |
|
《巴金全集》是巴金从1986年开始编辑的。本来,巴金是不打算编印全集的,他一直认为,自己的作品中有不少“失败之作”,甚至“废品”,没有必要收集起来重印一遍。1985年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仰晨(树基)的再三动员下,巴金基本同意编印全集,当年11月,商定了全书的框架和编目(此后不断有所调整),年底,他在给王仰晨的信中说:“说实话,我又不想搞《全集》了,我真希望被大家忘记,让我安静地再活几年,再写两三本小书留给后人。可是我知道我不让你搞,别人也会搞,我活着的时候我还可以指指点点,出主意 经过整整八年的艰辛劳动,1993年底,二十六卷《巴金全集》全部面世。这部全集是迄今为止收文最丰的一部巴金作品总汇,也是显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发展历程和巨大成就的一项宏阔建筑。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设,是巴金最为关注的另一件大事。三年前,1990年4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5周年的时候,巴金曾写信给文学馆馆长,信中说:“我说过文学馆是我最后一件工作,我应当把全部力量献给它。其实你们为它出的力,为它花费的心血比我多得多,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但是只要我的心还在燃烧,我就要为文学馆出力。”“让我们大家为文学馆出力吧。文学馆会发展下去。中国作家的美好心灵会通过文学馆的发展而开花结果!我坚决地相信,事业一定会大发展。”他向文学馆继续赠送图书、手稿,继续捐赠稿酬,继续呼吁海内外人士关注她,帮助她,支持她。在海内外文学界和关注中国文学事业的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下,文学馆在艰苦的条件下逐步发展,截至1990年,已收藏各种书刊资料近20万件,其中,图书10万余册,期刊2000余种6万余册,此外还有作家的手稿、照片、书信、文物以及录音、录像和其它文献资料1万余件。文学馆的藏书中,作家赠书约占三分之一,仅作家亲笔签名的著作就有近6000册。文学馆为除了自己的著作外还大量捐赠自己藏书的作家,设立了专门的文库,其中最早设立的作家文库就有“巴金文库”。 然而,文学馆还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临时馆址借用的万寿寺西院,将在1994年到期。由于万寿寺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再继续借用,将实行有偿租借,而租金却是文学馆无力承担的。为了使文学馆摆脱困难,找到永久性的馆址,1993年初,巴金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信中说:“我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目前遇到的困境感到不安。归结起来最迫切的是建馆舍的问题,希望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获得批准。在新馆未落成之前,希望仍在万寿寺西院内安身,不实行有偿借用。文学馆将是我一生最后一个工作,绝不是为我自己。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我不愿意看见它夭折。前面有不少困难,需要大家的支持;也希望得到您的帮助,请您过问一下。一切拜托了!”2月下旬,冰心也致函国务院副总理,恳请国家支持和帮助建立新馆。在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的关切下,国家正式决定投资9600万元,在北京建设面积为24000平方米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作为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者、支持者和催生者,巴金感到欣慰。 1993年,巴金又获得两项荣誉。4月,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授予他“资深作家敬慰奖”,奖牌上写道:“巴金先生著作等身,作品广受读者喜爱,历久不替,堪称文坛瑰宝。”年底,欧洲举办的颇具影响的文学评奖之一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评委会授予巴金和以他为主席的中国作家协会特别奖,“以表彰其在促进中意文学交流中作出的重要贡献”。巴金没有出席这两项奖的授奖仪式。前者由他的女儿李小林在上海代领,后者委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赴西西里岛巴莱莫市领奖。巴金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书桌前,不时用颤抖的手,握起沉重的笔写着,他写信,也写些短文,他要留下更多的肺腑之言。 按农历计算,1993年(癸酉年)11月是巴金90华诞。全国政协和上海市政协在巴金寓所举行了庆贺寿辰的活动。深情的祝福从中国和世界各地飞往上海。这个时候,巴金对众人说的是这样一段话: 我的一生是靠读者养活的,只要读者不抛弃我,我还要活下去。 我明白一个道理,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我是不是做到这一点,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等将来看,要盖棺论定。 (选自李存光《巴金传》,题目为编者加)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征,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选自《巴金自传》(标题编者加,有删节)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巴金逝世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