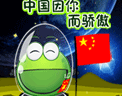精神觇标:巴金的意义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16:45 成都晚报 | |||||||||
|
一、信仰 从我第一次见到巴金先生说起。那是在1980年的时候,他应该是76岁,身体看上去还没有显出过分的老态,只 是一头银发,从楼上走下来时脚步有些滞重。他还有些感冒,稍坐了一会,就有医生上门来给他打针。但他兴致很好,打完针 又聊了一个小时左右。那天是我和同学李辉一起去武康路的巴金府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带花园的洋房,也是我第一
巴金先生的态度给我带来过一丝疑问:他现在到底还信仰不信仰无政府主义?这也是巴金研究领域里一个常常被提起 讨论的问题。我曾有缘拜访过几位与巴金同时代的老人,他们几乎都不忌讳自己的信仰。比如翻译家毕修勺先生,我第一次去 拜访他的时候,他坦率地说:“我到死也信仰无政府主义。”出版家吴朗西先生并没有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运动,但是他说到 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社精神时,容光焕发地告诉我:“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主义啊,所以搞得好。”我没有见过四川的教育 家卢剑波先生,但听访问过他的朋友说,卢先生也说过,你只要信仰过安那其,就不大可能再忘记它。我总觉得“信仰”这个 词对“五四”过来的一代知识分子而言,远比我们今天的人重要,他们的献身信仰往往是极其真诚的,不像今天的中国,到处 钻营着做戏和看戏的虚无党。那么,巴金对自己过去的信仰持什么态度呢? 我对这个问题是犹疑的。虽然我曾多次与巴金先生谈到无政府主义,他始终没有说过他现在还信仰它,或者不信仰它 。但有两件事我印象深刻,一次是我协助巴金先生编辑他的全集,我是竭力主张他把1930年写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 安那其主义》和几篇与郭沫若论战的文章收入全集,因为前者不仅是巴金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而且也是中国最系统的一本宣传 无政府主义的书,而后者,主要是批评郭沫若关于“马克思进文庙”的谬论,郭在1958年编文集时把他的辩论文章《卖淫 妇的饶舌》收入了,还特意加了注,说明当年与他论战的李芾甘就是巴金,这在当时显然是有构对方于罪的意图,但巴金却从 未再提过这件公案。当我这样建议后,巴金先生略加考虑就同意了,但他表示有些担心别人会说他还在宣传无政府主义。果然 ,最后出版社审稿时,还是将这些稿子删去了,那天巴金先生特意对我说了这事,他脸上略有笑意,有点挪揄地说:“还是他 (指全集的责编)比我们有经验,我们太书生气了。”这使我感到,巴金先生还是有许多顾忌,没有把他心中埋藏的话说出来 。还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观察到的,巴金先生晚年写过许多创作回忆录,惟独闭口不提他最喜欢的《爱情的三部曲》,这部作品 是根据他当年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事迹来创作的,他有意回避了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对此我一直觉得奇怪。直到他写《随想 录》的最后几篇文章时,才涉及到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叶非英等朋友,并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赞扬他们,那就是“理想 主义者”。我马上意识到巴金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被现在接受的语言来介绍他当年的信仰,才保持了那么久的沉默。果然,继 《随想录》以后,他连续写了怀念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朋友吴克刚、卫惠林等人的短文,收在《再思录》里。如果不是后来健康 恶化阻止了他的写作的话,我想巴金先生会进一步写出他对自己信仰的许多真实看法。 但是我还是无法断定巴金晚年是否有自己的信仰。我起先理解是巴金先生的地位比较特殊,他不可能像其他一些朋友 那样对自己的信仰有感情。因为像毕修勺等人50年代都遭受过极大的政治迫害,不仅受到社会的歧视,日常生活也很拮据, 被压制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因此他们一般都能够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惟一的精神支柱。而巴金先生50年代起就有较高 的社会地位,境遇也较好,可以战战兢兢地出入于庙堂,因而无政府主义不仅不会是他的信仰,而且还会成为他的思想包袱。 他在1958年以后删改自己文集中关于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就是其表现之一,而且,即使在写作《随想录》时他仍然心存犹 疑。我接触过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朋友,其中比较激进的朋友对此都有微词。 但我后来想,大约人们所忽略与所隔阂的,正是在这里。在一种理论学说还被认定是这个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敌人的 时候,如果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在私下里表达对它的信仰当然风险要小得多,但你无法想象,环境会允许像巴金这样地位 的知识分子公然表达他的异端信仰。就像30年代的鲁迅尽管尖锐地批判国民党政权,但他似乎也从未宣布过自己信仰共产主 义(如后来研究鲁迅的学者所认定的那样),而且鲁迅不止一次地痛斥那些暗示他拿卢布津贴的人,骂他们为乏走狗。鲁迅还 拒绝李立三要他公开发表反蒋政权、拥护共产党的声明,宁可用各种笔名在各种灰色报刊杂志上发表曲折的杂文,这是为什么 ?当年左翼激进青年不理解鲁迅,连斯沫特莱也批评鲁迅不积极参加左联的具体活动,但富有经验的冯雪峰当场就驳斥说,鲁 迅的地位不是别的作家可比的,他的存在(于左联),就是(左联的)一个伟大的力量。冯雪峰显然比那些青年人和外国人更 懂得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保护文化名人的重要。在鲁迅死后,他曾一度想去主动接近知堂,争取知堂,这些成功的和没成功的计 划,都显示出冯作为一个政工人员的卓越眼光。我想鲁迅当年与周扬那样一批热血青年之间的隔阂肯定会发生的,而巴金所面 对的是比当年鲁迅、蔡元培更加无奈的环境,他只能选择自己最有利也有效的工作方式来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 二、岗位 我在上一节本来是要讨论巴金先生的信仰,因为这涉及到巴金先生是否保持人格的一贯性以及关于“说真话”的问题 ,结果似乎仍然没有能得到肯定性的结论。但这并不离题,因为看一个人有没有自己的信仰主要不是看他的言论,而是看他的 行动。无政府主义在长期被镇压的过程中逐渐蜕变为一种日常的伦理行为,即强调自我道德完善。所以,像毕修勺先生自觉把 无政府主义精神解释为“只知耕耘,不问收获”的人格力量,并贯穿到他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中去。吴朗西先生把只讲奉献、助 人为乐都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原则,贯穿到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具体工作中去。这样的转变不是从1949年开始的,早在30 年代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已经在中国消失,无政府主义者发生分化,比较上层的人士都参与了国民党政权的建立,如 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等,而处于社会下层的青年无政府主义者都分散到边缘地区,积极从事理想主义的教育、出 版等工作,在社会上确立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岗位。 关于这些想法,我过去在巴金传记与其他一些文章里都已经说过,不必再重复。本节要讨论的是,巴金作为一名作家 ,他的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如何被体现出来?在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里,一直有两种价值取向交替着发挥影响,我把这两 种价值取向归纳为广场意识与岗位意识。前者常常作为传统士大夫的庙堂意识的补充,它企图将现代社会中的庙堂权力与民间 权利相沟通,来推动社会的改进和发展。“五四”以来,陈独秀、瞿秋白、鲁迅等激进的知识分子和30年代流浪型左翼知识 分子基本上是走广场意识的道路,巴金早期作为一个自觉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也是广场上的一员,启蒙与西化是他们的主要思 想武器;而另外有一批知识分子,或是作家或是学者,他们自觉地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理想的“岗位”决不是用强调专业 来掩盖对现实的怯懦,而应该是既包括职业又超越职业,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也往往通过自己岗位上的工作来体现。这两种意 识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两翼,当民主空间比较大的时候,广场意识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如果民主空间比 较小的环境下,岗位意识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更加大些。作为一名中国作家,他的岗位意识当然不仅仅体现在文体上创造美轮美 奂的境界,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美的创造中寄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精神作用。巴金走上写作道路之初,对文学如何结合这两种功 能显然是认识不足,这也给他带来了深刻的痛苦,他常常抱怨自己无法从事实际的社会运动,他希望到广场上去呼风唤雨,实 现“安那其”的理想。这些煽动性的作品虽然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也暴露了他内心的浮躁和偏执。到30年代中期, 他的朋友吴朗西等人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请他回国当总编辑,切实的岗位才使他有了把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与具体的文化工作 结合起来的可能,由此恢复了知识分子的自信。他的自信不但体现在从事出版工作的热情,也逐渐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憩园 》《寒夜》等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较高的结合。 应该说明的是,这样一种由广场向岗位转化的道路并不是巴金独特的道路,而是中国社会民主空间越来越小的产物。 鲁迅就是在切实的知识分子的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特有的道路。他弃小说而重杂文的写作,正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广场上的战斗 作用,同时又把自己的工作范围严格设定在文化批判领域,这就是他与郭沫若的不同之处,也是他先拒绝李立三,后又拒绝周 扬的根本立场。鲁迅晚年自觉团结了一批严肃认真从事文化事业的青年作家和编辑,其中主要就形成了以巴金和胡风为代表的 两个知识分子群体。很显然,如果鲁迅不是因病早逝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将会在汇聚了各种风气的上海发挥极为重要的战斗作 用,而且其生存与斗争方式将明显区别于《新青年》开创的广场的传统,也区别于因怯懦于现实环境而躲入书斋的传统文人的 方式,形成一种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价值取向。不幸的是鲁迅去世了,随着抗战的爆发,巴金与胡风两个群体,一个以文化生 活出版社为阵地,一个以《七月》《希望》为旗帜,各自开拓着鲁迅的道路,即在具体的知识分子岗位上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但并没有可能在鲁迅的传统基础上更前进一步。更不幸的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存与工作方式后来也被残酷地中断了, 巴金、胡风在后来的历史中各有不同的表现,也有不同的遭遇,直到80年代他们以不同的面目重新出现在千疮百孔的中国文 坛上。这时候的巴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惟一能继承鲁迅而做的工作,就是写作《随想录》。 三、《随想录》 巴金先生晚年对文化的主要贡献就是写作《随想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先生内心深处的信仰与力量。当然我也 感到惋惜,由于巴金先生的高龄和重病,以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已经无法使他在80年代的思想基础上有更进一层的突破。事 实上这也不仅仅是巴金先生个人的悲哀,总的来说,80年代思想界起过重要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力量到了90年代几乎是广 陵散绝,自有另一批新的偶像与战士来领风骚,这是时代风气的变迁所致。我们不可能要求一个九十多岁重病在身的老人永远 与青年人一样冲锋陷阵,何况,在90年代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压力下,以思想界领袖或青年斗士自居的人们是否真的在冲锋 陷阵,退一步说,是否都能像巴金先生那样真诚地对待历史和自己,也是值得怀疑的。《随想录》当然会有局限,正如任何前 人创造的精神成果在急剧变化中的现实中国环境里,都会有其局限一样。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前辈的创造。我总以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是靠一代代知识分子有意识的培养和积累得以发展的,即使从本世纪初的严复章炳麟算起,也 不过是百年光景四五代人,所谓百年积德,真正的“德”,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是极其薄弱的。我们现在无法创造什么,惟一能 做的,就是把前辈们的精神遗产继承过来,加以清理,他们做到了的我们有责任发扬广大,继往开来;他们没有做到的,我们 有责任勉力做去,点点滴滴,都是在前辈知识分子的努力、苦难和教训的历史阴影里走过来的。而由于忽略与隔阂,就用狂妄 的审父甚至弑父的态度来对待前辈的精神遗产,虽也能称快一时或不失为一种后生可畏的进步,但是自斩其根自断其流,这样 的“进步”也终将会成为昙花一现的现象。近两年有学者提倡“鲁迅精神谱系”,我不很赞同这样的片面说法,但我是理解倡 导者心态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很难离开鲁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战斗传统来思考问题,但是我又想,鲁迅的精神传统不 应该成为几座孤立的独秀峰,而是一道源远流长的精神河流,它既泾渭分明,又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即使流淌到今天,也不能 成为少数精英的专利,它还应该能够化解怨毒暴戾之气,淹没无聊闲碎之音,使每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都可能融化为其中的一 点一滴,而贡献自己的所有。也只有在这样的立场上,我们来讨论巴金的意义才是有益的。 理想并不能够被现实征服。希望的火花永远在黑暗的天空闪耀。甚至在压迫最厉害的时候,也有人站出来勇敢地叫道 :“我反抗!” ——巴金《给一个敬爱的友人》(陈思和)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巴金逝世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