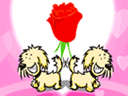林怀民:我是一个保护社会公器的人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2月10日10:54 南方周末 | |||||||||
|
□本报记者 王寅 舞者林怀民认为,一个地方想要久长,总要有点牢靠的东西。所以他希望自己退休以后,云门还要继续,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公器” 2月15日至19日,林怀民将带领云门舞集在香港艺术节上演“行草三部曲”,这也是
去年,林怀民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年底推出了《狂草》。二是《红楼梦》在上海大剧院的封箱上演,舞蹈以春夏秋冬四季的更迭串联起了《红楼梦》的故事情节,漫天飘飞、密如珠帘的灿烂花雨和穿着绿色三角裤舞蹈的贾宝玉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怀民把演了25年的《红楼梦》作封箱演出,是为了对自己的早期创作有一个了断。“用3个月的时间来重排《红楼梦》,可以编两个新舞。我年近60,来日不多,还想翻两个山头,封箱算是一个交代。” 《时代》杂志亚洲版评选2005年度“亚洲英雄人物”,中国共有六人上榜,名列第三的林怀民,同时也是台湾地区唯一入榜者。时代亚洲版称“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是不断创新求变的艺术家,同时更盛赞他是舞蹈天才。从1973年春天创办“云门舞集”至今,林怀民把云门打造成了亚洲顶尖、世界一流的舞团,台北市因此把云门所在的街道正式命名为云门巷,以表彰云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艺术探索求新求变的同时,林怀民的身上依然保留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云门将台湾作家陈映真的小说搬上舞台就是一例。林怀民的理由很简单:“对于那个时代,有我们青春的眷恋,在那个时代里面,陈映真的声音是重要的声音。而今天作为一个文学家,陈映真是非常孤单的。”在为这部戏作宣传的时候,林怀民亲自上阵,他做得最多的是在公众面前朗读陈映真的小说,读的是《山路》里女孩子的信,在朗读过程中,每每看到听众的眼泪慢慢地流下来。尽管这部戏票房不佳、亏损严重,但是林怀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我仍然很高兴很骄傲,快60了,还要当愤青。可是‘愤青’这个词现在没有人用,现在大家都在讲‘花男’。因为愤怒青年没有市场,无法与商品挂钩,所以无法流行。” 王寅 摄 林怀民期待云门以后到内地的演出,他希望演得更多,而不是现在这样一次只演一部,他从云门的作品中精选出最值得演出的几部:《九歌》、《流浪者之歌》、《水月》、《竹梦》、《烟》、《行草1、2》、《家族合唱》、《薪传》,在林怀民的节目单上,这些都是云门的精华之作。 今年12月,云门将在台北和台中的秋季巡演中,分别举行“林怀民六十回顾”的纪念演出。林怀民还是像以前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观众习惯了每年看云门推出新的作品,也习惯了林怀民每场演出之前在剧院大厅的即席讲解和在谢幕时向演员们深深鞠躬的姿态,大概没有人会想到林怀民也会退休。在采访中,林怀民向记者透露了离开云门后的各项安排,他早就盘算好了云门以后的人事安排和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但是,林怀民肯定地说:“退休不是一个计划。” 没有了林怀民的云门,还叫云门吗? 看书道,悟舞道 南方周末:《狂草》和《行草1、2》有什么区别吗?我看《行草1》里面已经有怀素了。 林怀民:《行草》那个时候只是要做一个形式,没想到要做三部曲,所以我就把书法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放进了《行草》。讲《行草》的时候,并不是在讲某种字体,而是以行草这个名字概括了书法,所以用了很多名家行草之外的手迹。演完之后,我觉得我贡献很大,因为我们到故宫博物院看字的时候,王羲之的字,其实就是拇指大的一个字,可是拜电脑之赐,我帮它洗了澡,把它放大起来,在舞台上黑白分明,吓死人,好像王羲之刚搁下笔来走人,那真是震撼。 《行草1》在华人世界上演的时候,观众难免要去辨认这个字:是谁写的?哪里的字?实际上这些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跟舞蹈没有关系。 但《行草1》在西方受到惊人的欢迎,西方观众只需要去感觉书法的美,没有发出研究性疑问的可能。在华人世界,《行草1》第二次演出时,观众才会很喜欢这个舞蹈,“看图说话”这个阶段才过去。 南方周末:对于书法,是不是《行草1、2》里面还没有说完,意犹未尽? 林怀民:一定!一定!意犹未尽,我们不是在说书法,这是一条很大很长的路,就像人家写书法写了一辈子还没有写完,我们做这个事情一样没有做完。书法这个事情,和练习武术完全一样,讲虚实,讲走势,讲手法,讲墨分五色,全部是一样的思维。这5年来,云门的舞者每个礼拜四下午都练习书法,刚开始有一两个人嘀咕,觉得自己又不是书法家,但现在每个人都期待练习书法的时刻。 南方周末:《狂草》演完之后,他们还会写吗? 林怀民:写!写!写!这是他们的娱乐行为。好几位云门舞者一到欧洲,进了旅馆,一有空儿就摊开纸来,在窗前写他的字。我很喜欢他们写字,因为这里面你要体会到运气。 实际上他们有些人写得很好,老师和我商量说,是不是明年开一个小小的书法展,鼓励大家。老师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很放得开,实际上书法不是手臂的运作,而是全身的,这跟舞蹈很神似。他们当了一辈子舞者,上两堂课,书法的感觉就来了。他有这样的体会,心里有了这个意,自然就会体现出来。 这几年在做《行草》三部曲,我看到了美丽,就像看到一个字帖,开心啊。对于书法,我是外行,我字也写不好,可是书法对我而言始终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和提升,对于舞者们也是。排练的时候,我们经常一两个小时就读讲书法的书,什么书都好,我们每个人都有小册子,台湾石头出版社出的,台湾和大陆的学者写的一些东西。读怀素的两页长的简传,我们会耗上两三个小时,舞者们都很开心。有些文章是文言的,有些事情需要讲些背景资料,我们就在一起讨论。比如怀素和尚到了京城,住在有钱人家,出入坐有钱人的马和轿子,京城所有的大户人家、权势之家,都准备了白壁屏风请他去写字。我就问大家,你们认为这说明了什么?有舞者说,作者在嘲讽怀素和尚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我们就聊这些,然后再看怀素的字。 再比如说张旭的《肚痛帖》,舞者们都喜欢读,凑在一起就兴致盎然。张旭的字对我来说,是一个惊人的交响乐的雏形,从粗犷到秀丽,那么极端的东西集中在那么小的一个篇幅里头,在空间的呼应上,在气韵的流动上,在动机的变化上,简直让人目瞪口呆。 这些东西与《行草》系列舞蹈无关,但那些书法是对一个艺术工作者的当头一棒。我把张旭的字贴在墙上天天看,就看自己哪天能够得了那个规格。 南方周末:现在还在看张旭的字吗? 林怀民:我家里的厕所,床头,都可以看到张旭的字。这个字和下午的排练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只是一种开心! 我们中国建筑的整个装饰,从休息厅的天庭再到房间的摆设,就是字。一个牌楼起来,两个小狮子旁边一站,就是字。我们的房间里全是字,因为我们的汉字本来就都是图画嘛。 我也不是讲“复兴文化”,但一头栽到传统文化中去,真是柳暗花明,所以我觉得开心。这里边可以找到编舞的由头或者方向,甚至是限制,但是也可能找不到任何关系,因为也许本来就没什么关系———谁说你一定会找到(书法和舞蹈的关系)?你以为你是谁?你只能埋头苦干,当然别人会说,你这样埋头苦干不行,不潇洒,顾了这个没那个。 让墨水长流10米 南方周末:这次排《狂草》在舞台上和前两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林怀民:我们云门很多的事情是有趣的,像这回在做《狂草》的布景,我就决定要用纸墨来做,这是唯一的要求,我要求在舞台上顶天立地挂10米宣纸,在观众眼前水墨漫泛,技术人员于是就疯了。 南方周末:他们为什么觉得难呢? 林怀民:地心引力问题。我要求,一滴墨汁从10米高的宣纸上,从头流到尾,十几秒到二十秒走完。要直线进行完成极限运动,要匀速运动。我们和纸厂合作做这个布景,这个纸厂很厉害,常年接受日本皇室的订单。 南方周末:这个宣纸是台湾出的,还是内地出的? 林怀民:其实那不是宣纸,而是修补用的特种纸。所以我找他们做液体在表面流不动的、充满障碍的纸。做完了,我们试验,墨水下降的时间二十几秒,三十几秒,我们在控制,多少水多少墨都得算。我们想让墨水慢慢流,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控制,但这事儿我们控制不了。墨水流过的地方,就像水墨画,漂亮得不得了。因为是墨水又是自然流动,流动的过程中又有很多化学反应,墨水流动的路线上又有很多障碍,墨水到了障碍上,水会一直累积,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崩了,接着就会流出另外一个走势。我们也可以给很多的水,让它先走一点点,然后再加水,还可以玩稀释。 南方周末:我上次采访您,问到《竹梦》里面,从天上掉下来的雪花由于材料不同,飘落的速度也不一样的时候,您非常得意。这次玩墨可以和那一次媲美。 林怀民:这其实是非常严肃的。看起来,说出来觉得非常简单,完了就走了。但为了达到那种效果,我还跟台湾工业研究院的化学家们专门请教过,他们给墨水加入不同的化学成分,使墨水有不同程度的蓝,非常美,在舞台上背光一打,墨分五色、历历在目,而且透明。 南方周末:《行草1、2》还没有这样的尝试? 林怀民:《行草1》是用那些大家的字来呈现的。《行草2》是我这辈子最美的东西,因为我从故宫的字画看到,那些黄黄的斑驳的字迹,我就在想斑驳这个事情,我一下子想到宋瓷,所以我就把很大的一个瓷器的造型放到舞台上,再配上约翰·凯奇的音乐,你几乎可以感觉到空气里飘荡着什么东西,安安静静,所以《行草2》是一个非常冷静、安静、祥和的东西,和宋瓷一样的感觉。 《狂草》回到纸墨,我的体会是你管他怎么草,到最后书法它就是一个纸(草本的东西做的)、松烟、水,还有人的呼吸,这个就是走自然路线。舞蹈现场,看到的是水、纸、墨,听到的全部是自然界的声音,水声鸟鸣……非常干净,跟大家想象中的狂草不一样。 林怀民可以退,云门不能退 南方周末:您刚才讲到退休,应该说退休是早晚的事。 林怀民:是的,不管有没有计划,退休是早晚的。 南方周末:有没有想过找一个接班人? 林怀民:这个事情是人算不如天算。即使我找到了接班人,只要我退休了,大概三五年内,所有我比较好的作品,就会统统变成空气消失。 理由?我的假设是这样的:董事会以及我自己都在找一个有个性、有创意的人来做总监,因为他够聪明,那么他就不会愿意在林怀民的阴影下工作,我们也会赞成他走出自己的路子来。然后第一个从训练课程上削掉的,很可能就是我的这些传统的积累。 南方周末:那观众会不会不买账呢?他们觉得没有林怀民,他们就不看云门了。 林怀民:应该会有一段时间适应。我觉得一个舞团最重要的功效是提供好的作品,所以,我也期待年轻的创作家用他的语言与新时代对话,而不是创造一个必须常常清理灰尘的博物馆。 南方周末:您退休以后干什么? 林怀民:其实我很好打发,只要我有一杯茶,有烟……我不担心,我想读的书还有一堆。 南方周末:从特别繁忙的创作当中退出来,会不会觉得寂寞? 林怀民:这是大家的想象。我也想过过不繁忙的日子,我会做一些我能力可以做的事情,像云门停掉的那年,1988年,我搬回我的故乡新港,住了1个月,当时我把新港文教基金会的整个行政体系初步建立起来。我基本上是一个孤僻的人,人多的时候我会不自在,超过3个人就不自在。 南方周末:但是事实上,您在云门做的工作面对的人经常要超过3个人。 林怀民:有人说你这么有名,忽然什么事都不做,你会不会觉得很空虚?我说报纸上登的那个人不是我,你在我家,看不到一张我的照片,你甚至看不到一张舞蹈的照片,关起门来那个人才是我自己。我也知道有再大的名气,都没有办法帮你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帮你解决父亲母亲生病的问题。名气和我的生活关系不大,但跟云门的业务有密切的关系,我是这样看待这个事情,不然我也可以摇摇摆摆起来,可是摇摆给谁看呢?(笑) 南方周末:我两年前采访您的时候,您说过云门是您生活的全部。您付出这么大的心力,能够轻易地舍弃它吗? 林怀民:对我来讲,这是很现实的事情。 首先,云门100多个人要发薪水,所以不是说你要下车就可以下车。 其次,对我来讲,云门造就了我,我原来是一个写小说的孤单的年轻人。云门成了我和社会沟通的通道,在其中我不只学习到了舞蹈这个事情,我通过云门中的舞者认识社会和人生,我的成熟都在云门。 再者,从文化来讲,台湾是个非常贫瘠的地方,云门至少是一个文化的东西在那里摆着,多好多坏,见仁见智,我们就在那里存在着,我们这样的存在,以前没有发生过,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发生。 最重要的是,云门不是我林怀民一个人组成的,云门也不是只由这些舞者们组成的——云门是这个社会的雨露培养出来的。确实,社会给我们的东西永远不够,永远露多于雨,但是我很珍惜。台湾是一个改变非常快、非常多的地方,而且在每一个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消耗都很大;但因为台湾地方小,所以成功也来得比较快。 我看到大陆传统的东西,即使经过10年浩劫,好像真的有某种东西的“底儿”还在,这与台湾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在西安,你穷疯了,还可以在你们家卧室里往下打洞,好歹可以掏出几个唐俑来。台湾往下挖,还是泥土。我觉得,一个地方想要久长,总要有点牢靠的东西。我个人希望我不做了以后,云门还要继续,它是一个社会公器,我是一个保护社会公器的人。 林怀民: “云门舞集”创办人兼艺术总监,1947年出生于台湾嘉义,14岁开始发表小说,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文坛瞩目的作家。 留美期间,一面攻读学位,一面研习现代舞。 1973年创办“云门舞集”,推动了台湾现代表演艺术的发展。曾获世界十大杰出青年、纽约市政府文化局“终身成就奖”、香港演艺学院荣誉院士。 王寅 摄 云门舞集: “云门”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相传存在于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但早已失传。1973年春,林怀民以“云门”作为名称,创立华人社会第一个当代舞蹈团体。 30多年来,云门舞集排演了150多出舞蹈作品,成为台湾社会两三代人的共同记忆。云门也经常应邀赴海外演出,是国际重要艺术节的常客。近年来,每年在大都市举行的户外公演,平均每场观众多达6万。 迄今为止,云门已经在全球的200多个舞台上演出了1500多场,享有世界范围的崇高声誉。 相关专题:南方周末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南方周末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