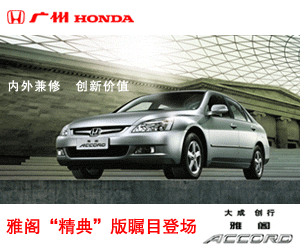|
|
|
|
|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文人:以笔为枪摇旗呐喊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30日14:08 新世纪周刊
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笔部队”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内阁情报部向中国战场派出了一批文学家。他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被当时的日本媒体大肆宣传为远征中国内地的“笔部队”。 “笔部队”的成员们制作了大量“战争文学”,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美化日军暴行、丑化中国军民。“笔部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作用不可小觑,但在中国,却鲜为人知。 战后,日本右翼文人又大肆撰文,蓄意歪曲历史、任意抹杀史实,将战前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文人对华的文化侵略继续推进。其中最重要的“作业”,就是否定、抹杀南京大屠杀。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历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经过中国军民八年的艰苦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署投降书,日本侵华战争以失败而告终。 以笔杀人:不能被忽略的侵略 拿破仑曾说:一支鹅毛笔能抵三千毛瑟枪。日本侵华期间,也曾派出一只“笔部队”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着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作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战线》,1938年12月,朝日新闻社出版) 这是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1903-1951)笔下的日本侵华战争,屠杀的场面充满了英武的美感,令她难以忘怀。 1938年,林芙美子从军出征,时值日军攻占武汉,她把亲眼目睹的战争场面写成了两本从军记:《战线》和《北岸部队》。因为对美化日本侵华战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林芙美子被当时的日本媒体誉为陆军部的“头号功臣”。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向中国派出了一批像林芙美子这样的“笔杆子”,他们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部队,被称为“笔部队”。“‘笔部队’的成员们以笔为枪,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向远称:“他们或把战争责任强加给中国,或为侵华战争强词争辩,或把日军的残暴行径加以诗化和美化,或胡说中国老百姓如何‘亲善’,或炫耀自己的战争体验。” 协力侵华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近卫首相召集各新闻通讯社和几家著名杂志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战争。紧接着,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又把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报刊、广播等舆论工具也向国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侵华战争的宣传。 为了满足日本民众对战场通讯的需求,早在1937年8月初,《东京日日新闻》便接连派出大众文学巨匠吉川英治氏和小说家木村毅分赴天津和上海,及时发回战事报道。8月底,杂志社也开始向中国战场派出作家。“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一年里,日本媒体派出了几十名文学家来到中国内地“从军”。他们写的“从军记”和“现地报告”一时充斥杂志报端。 “这时,日本军国政府还没有直接插手组织所谓‘笔部队’。这些初期的‘从军作家’都是由非官方的民间机构派出的,但其性质和后来的所谓‘笔部队’并无不同。可以说他们是初期的‘笔部队’。”王向远说。 在初期特派作家的作品中,尾崎士郎的长篇从军记《悲风千里》一直获得日本读者和学者的较高评价。书中描写的是日军侵占下的华北地区的情形,没有战争的恐怖,只有温情的和平。在其中的《支那的孩子》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小孩!小孩!来!来!” 孩子们起初不敢接近,随着逐渐熟悉,慢慢地靠了过来。于是东洋鬼子给他们牛奶糖,抚摸他们的头。 孩子们已经知道了,原来东洋鬼子不是鬼。于是跑回家中,从家里拿来了梨、柿子等,献给“东洋鬼”。 “东洋鬼”乐得笑逐颜开。他们接受了水果,同时付了钱。 孩子们再次跑回家里,然后把他们的父母兄弟带来了。 “尾崎士郎在这里刻意描绘的颇有‘人情味’的场面,绝不是有的日本学者所说的什么‘人道主义’,而是刺刀和枪口下的‘和平’,也就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搞的所谓的‘宣抚’。”王向远说。 1938年3月,日本作家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发表。因作品描写了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场景,石川达三遭当局逮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士兵兼作家火野苇平1938年8月创作的小说《麦与士兵》,站在军国主义立场,美化歌颂侵华日军,却在当时发行了120万册,成为最畅销书。王向远认为,正反两个事例,显然给日本军部和政府以明确的启发,导致了他们对作家从军及其创作活动的干预与管制,并成为由军部和政府直接出面组织从军作家的所谓“笔部队”的一个契机。 1938年8月23日,日本内阁情报部召集文艺家开会。会议提出:希望派20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国前线看看,不对作家做硬性要求,相信作家们自有正确判断。 8月26日下午,内阁情报部公布了确定派遣的从军作家名单。此后,日本新闻媒体对这批从军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内地的“笔部队”。 第一批“笔部队”回国后,军部和政府又组织了第二批“笔部队”。1938年11月,他们作为海军的从军“笔部队”被派往“南支”,即中国南方地区。 “‘笔部队’的组成以及开往中国的过程,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开始已经通过国家权力,把日本文学拖入了侵华战争的轨道。此后,无论是否到过中国前线,日本的绝大多数作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支持和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写下大量侵华的所谓‘战争文学’的文字。”王向远说。 日本当代学者高崎隆治评论“笔部队”中的文学家,“不必说抵抗,连不合作也没有,竟趋炎附势,溜须拍马。文学家们应该从这种可耻的堕落中,充分地汲取历史的教训。” 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 1938年底,“笔部队”的大部分作家都已回国,日本许多报纸杂志纷纷刊登“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报告文学、小说等,形成了侵华战争期间所谓“战争文学”的一次高潮。 “‘笔部队’成员的这些文学作品,尽管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完成了军部要求他们完成的使命。”王向远说,尽管军部在劝诱作家从军时,曾表示不对作家做硬性要求,但事实上,作家一旦来到前线,就必须按军部的要求去做,前车之鉴便是石川达三。 石川达三的纪实小说《活着的士兵》描写的是几个日本士兵在南下进攻南京的途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种种野蛮罪行:他们仅仅怀疑一个中国年轻女子是“间谍”,就当众剥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平尾一等兵因为一个中国小女孩儿趴在被日军杀死的母亲身边哭泣而影响了他们休息,便扑上去,用刺刀一阵乱捅;随军僧片山玄澄,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他们占领上海后,强迫中国妇女作“慰安妇”,成群结队到“慰安所”发泄兽欲。 “比较地看,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是日本‘战争文学’中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作品。”王向远说。然而,正是由于作品揭示了侵华士兵人性的畸变,石川达三被日本法庭以“记述皇军士兵掠夺、杀戮非战斗人员,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定秩序”罪名,判处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这是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发生的第一起、也是仅有的一起作家“笔祸事件”。 被判有罪,石川达三感到了一种“成为罪人的屈辱”,于是他“幡然悔悟”,并很快找到了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判决十几天后,他再次被派往武汉战场从军。一个多月后,返回日本,发表了“思想革新”作品《武汉作战》。 “《武汉作战》与《活着的士兵》大为不同。在《活着的士兵》中,作者描写了日军的凶残行径,而在《武汉作战》中,他努力表现日军的‘文明’之举,显然是在试图抵消、抹杀上一部作品中有关描写及其造成的影响。”王向远说,“但由于露骨地‘戴罪立功’,无条件地歌颂侵略战争,其结果是毫无‘真实’可言,而是黑白颠倒,谎话连篇。” 与前后判若两人的石川达三不同,火野苇平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坚定日本军国主义战士。他和他的《士兵三部曲》(《麦与士兵》、《土与士兵》、《花与士兵》),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 在火野苇平笔下,侵华日军是一支伟大的军队,士兵们具有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然而对于中国人,火野苇平却道出了“强烈的憎恶”—— 我对于那些给我们的同胞造成如此艰难困苦,并威胁到我的生命的支那兵,充满着强烈的憎恶。我想和士兵一起突击,我想亲手消灭、杀死他们。(《麦与士兵》) 火野苇平的侵华文学作品,被军部宣传机构大力推广传播,他本人也被捧为“国民英雄”。 “整体看,‘笔部队’制作的侵华文学,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国策’的产物。”王向远指出,一方面,侵华“国策”造就了“笔部队”,另一方面,“笔部队”制作的文学作品又在相当程度上为日本的武力侵华推波助澜,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双管齐下的侵华战争局面。 半途而废的侵华文学反思 鉴于“笔部队”的从军作家对日本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战败后,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在1946年1月发布文件,决定追究在侵略战争中负有责任的人,其中规定:“通过文笔、言论,积极地鼓吹好战的国家主义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指的主要是文学者——也在追究之列。” 在占领军最高司令部文件的支持下,日本文学界内部开始了对文学者的战争责任揭发和追究。1946年1月,评论家小田切秀雄等创办《文学时标》杂志,设专栏渐次点了战争协力者的名字,包括火野苇平、石川达三等40多人。1946年6月,日本左翼杂志《新日本文学》发表了小田切秀雄《追问文学上的战争责任》一文,点出了包括火野苇平、尾崎士郎在内的25个作家的名字。 然而,这样痛快又合情合理的揭发和声讨,却没有能够持续下去,不久便走调了。一个重要原因是文艺评论家本多秋五等人,在战后初期的重要杂志《近代文学》组织召开的座谈会上犀利地指出:“要追究文学工作者在战争中的责任,首先应讨论追究者的主体资格问题。可以说,在战争中完全没有责任的文学工作者是绝无仅有的。”这样,既然谁都没有资格追究,就等于谁也不会受到追究了。 王向远说:“这反映了日本战后初期文学界对战争责任问题的主流态度,在这种论调下,文学界关于文学者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和追究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被《文学时标》和《新日本文学》点名的几十个文学家,除了小部分人后来陆续被占领军最高司令部定为战争责任者并给予开除公职等处分之外,大部分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直到1948年3月,占领军最高司令部才分两批公布了作为文学家受处分的12人名单,其中包括石川达三和火野苇平。石川达三等3人被提出异议,准予不受处分。而那些受了处分的文学家几年后又全部恢复了“名誉”。王向远由此总结说:“无论从行政手段上,还是思想上,对侵略战争负有重要责任的文学家都没有受到根本的触动,没有做过真正的反省。”
【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