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龙:我就是一堂吉诃德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23日11:00 南方人物周刊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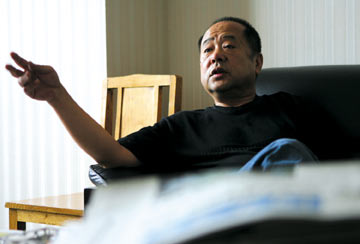 马云龙 -本刊记者 李玉霄 1963年,他是河北省的高考文科状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却成了豫东平原某农场的杀猪匠。 “文革”初期,他是北京大学名噪一时的红人,位列聂元梓之后,号称“北大第一嘴
1974年,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背着85条“反动言论”,被投进看守所,本以为必死无疑,却在1979年安全释放。 15年后,他成为主办河南大河报的四大元老之一,是这份中原地区第一都市报的灵魂人物,却在其鼎盛期无奈离开,在同仁看来,这“标志着一份报纸一个时代的终结”。 此后,他也像那些理想满怀的年轻人一样,为了寻找一个可以做新闻的地方,东奔西走,最极端的例子是居然在一年之内连跳3家媒体。 去年8月,这位61岁的老先生,就任河南商报顾问。他当“顾问”,既顾且问,亲自采访、亲自写稿,然后亲自编版,依然是带着一帮年轻记者,继去年10月捅出“巨能钙含双氧水事件”,今年3月又率先报道河北“聂树斌冤杀案”,以至于有人评论“河南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大新闻,全让老马给做了”。 老马,就是马云龙。这位以非党人士身份一直主管新闻的大河报原副总编,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向有“狂人”、“怪人”之称,但私下里,年轻的记者编辑们,却因其狂和怪,亲切地称之为“马老爷子”。 从造反派领袖到青年农民 所谓命运,不过是人生中诸多偶然的累积。 马云龙之所以来到河南,并且成为今天河南新闻界的扛鼎人物,和4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直接相关。 1966年初夏,“文革”狂飙席卷全国,北京大学成为全国运动的风暴眼,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马云龙脱颖而出。这位曾经的河北省高考状元,博览群书,兼具口才,大小集会频频露面,登台一呼,应者云集,“北大第一嘴”不胫而走;进而作为北京大学惟一学生代表,进入首都红代会常委会,成为14名常委之一。虽然不久之后,这段经历让他终生懊悔,但当时,年轻气盛的马云龙一时领风气之先,饱尝灵魂革命、思想斗争之快感。 但是,随之而来的一场武斗,将他从“斗出一个新天地”的梦幻之境拉回残酷的现实。1968年3月28日深夜,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率先向“井冈山兵团”发起攻击,大打出手,是为全国高校“文革”武斗之始。“3·28武斗”暴露了所谓“革命”的另外一副真实面目,马云龙大梦方醒,第二天早上即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声明:即日起辞去红代会所有职务,彻底退出红卫兵组织。 自此,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目变成彻头彻尾的逍遥派。上午泡在寂静冷清的图书馆,啃读列宁全集;下午去颐和园游泳;晚上则和来自各系的逍遥派们辩论政治、议论时局、交流读书心得。这种“神仙”般的日子持续到1968年底的毕业大分配。 军宣队控制下的毕业分配,一切变得非常简单,军代表手中名单一念,数千名学生踏上行程,分赴祖国各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马云龙卷起铺盖,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河南省太康县解放军第一军的部队农场,打土坯,烧砖瓦,盖房子。然后,他被分配在炊事班,顺理成章地学会了杀猪。 两年之后,“学军”结束,按照全国统一政策,这批大学生理应分配工作,但患有“意识形态过敏症”的河南却执行了更左的政策:“学军”之后再“学农”。 农场里的七百多名大学生就像“老三届”中学生一样,进村入户,插队农村。马云龙这次被“分配”在长葛县南席公社古城村,开始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又是两年过去,1972年“学农”结束,这批早就离开学校的大学生就地找工作。有门路的去了郑州和许昌,马云龙举目无亲,他的去处是长葛县教师进修学校。 从首善之区北京到豫东平原农场,继而是不为人知的古城村;从红卫兵领袖到被改造的大学生,到农场炊事员,继而荷锄而作的青年农民,最后是县进修学校教员——虽然依旧关心时事,虽然坚持晴耕雨读,马云龙还是深深感受到了政治风潮对于个人命运的无情播弄。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对于昔日革命的狂热追随者、如今散落各地厂矿村寨的马云龙们,不啻一记当头棒喝。 当副统帅林彪命殒蒙古的消息传到河南,正在学农的大学生们惊诧莫名。马云龙说,“我们当时先是震惊,然后就是愤怒和屈辱,是发现自己被愚弄之后的愤怒和屈辱。” 同时,农场就业、农田耕作的最底层经历,则促使马云龙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开始用怀疑、审视甚至质疑的眼光打量他所厕身的这个世界。但是,也正是这种独立的姿态,给他带来了一场牢狱之灾。 牢狱之灾 1974年底,马云龙在大小场合的言论被好事者收集起来,计85条,随即被上边定性为“反党、反毛主席、反中央文革”。他旋即被隔离审查,然后确认为“现行反革命”,1975年1月10日,他被关进看守所。 先是在长葛县,后又转到许昌专区,一关将近两年,就是不判刑。看守所的“待遇”不如监狱,吃不饱饭,见不到家人,马云龙忍受着“火烧火燎一样”难以抑制的饥饿,忍受着独居囚室的煎熬。更糟的是,铁窗外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传来的全是坏消息: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他渐渐地绝望了,感觉自己出不去了。 “那几年经常夜不能寐,只是在琢磨怎么死才能体面一点,才能有人的尊严。甚至动过念头,宁可一头撞死,也不能让他们五花大绑勒着脖子押赴刑场。此外,就想如果有机会,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怎么说,说什么内容。” 事态仿佛如他所料,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马云龙在里面的感觉是“形势急转直下”。10月1日深夜,他忽然被叫起连夜提审,主审员换成了法院院长,而且是连轴转不间断的审讯。他意识到“凶多吉少,可能要杀人,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于是,马云龙拿出当年的辩论本领,以法院院长为听众,将那些“罪状”挨个反驳,直将每次提审变成了辩论会。连续6天下来,85条“罪状”还没过一遍。 10月6日,也是在一夜之间,审讯突然结束。“三天之后,站岗的卫兵悄悄打手势告诉我,中央抓了4个人,他问我知不知道哪4个,我明白了,告诉他是王张江姚,他很惊讶。从那天开始,只要他站岗,他就从食堂偷偷给我带馒头,从窗口扔进来。” “四人帮”虽然打倒,但马云龙尚有12条“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因此,他又在号子中度过了两年“不杀也不放”的日子。 1979年初,马云龙被告知“免于刑事起诉”,1月19日,他走出许昌地区看守所,两个月后平反。 他将恢复自由的1月19日当作自己的第二个生日。有关方面曾打算把他树成“张志新式的与‘四人帮’斗争的典型”,他三言两语就回绝掉了,原因很简单,他不愿意再被左右,只想要自由。 他又回到了长葛县,这让当时的县领导甚感为难:“你虽然平反了,但我们县这些年大会小会批马云龙,1974年批林批孔、1975年批邓反右倾、1976年批四人帮,都要把你马云龙捎上。现在你又回来了,我们怎么向群众解释呢?你还是走吧。” 马云龙去了郑州,当年一位农场同学介绍他到省图书馆工作。5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还是由同学的推荐,他调进河南日报,当上了一名记者。 这一年,马云龙整整40岁。 “苍蝇老虎一起打” 自1968年兴冲冲来河南,已经16年过去,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年届不惑。但是,失去的只是懵懂,得到的却是彻悟;变化的亦只是容颜,不变的仍然是激情。 他自告奋勇去老山前线采访;他报道了当年轰动一时的长沙漂流,并且策划组织了黄河漂流队,和那些血性男儿一起出生入死,被他们尊为“政委”。更为难得的是,进入河南日报不久,在党报体制内,他屡有“出格”之举,有一次竟将考试舞弊的副厅级干部拉下马。 因为强烈的道义担当,底层生存所赋予的民间立场,以及对新闻的挚爱与执著,马云龙很快赢得同行的敬重。 1995年2月,在领衔创办洛阳晚报之后,马云龙重回河南日报社,与王继兴、庞新智、马国强3位昔日同僚一起,共同筹办大河报。当时的郑州报业市场上,郑州晚报一家独大,年广告收入8000万元,而偌大的河南日报只有3000万元。4位主办人抱成一团,豪气干云,决心夺回市场霸主地位。 马云龙的职务是副总编辑,直接分管采编业务。他带领着同样理想满怀的编辑记者,以这张新报纸为阵地,东拼西杀,“既打苍蝇,也打老虎”。 大河报之所以会有爆发式的发展,两年之后全面超过郑州晚报、奠定中原老大地位,马云龙等4人及其麾下的那批年轻的新闻信徒们,功不可没。 直到现在,初创期弥漫整张报纸的那种冲动与激情,仍令后来者怀恋不已,有人甚至直接将其称为“马氏风格”。 “马氏风格”的最大特点就是“苍蝇老虎一起打”。 那是在一次全国都市报总编辑会议上,一位颇具声名的报社老总说,现在舆论监督环境不甚理想,我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马云龙当场反驳:“错了!既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也许有时候打不了老虎,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 他是这么说了,他更是这么做了。 1997年夏,河南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个“学三讲”读书夏令营活动,组织全省“学三讲”中的青少年积极分子到香港、澳门游玩。可是大河报记者采访中却发现,30名营员中,居然有28人是省市县各级宣传部的官员,真正符合青少年身份的只有两人。这稿子发不发?编前会上,主导意见是“这是直接批评我们的直接上级,算了吧,不发了。”马云龙坐不住了:“这是好新闻,当然要发。”两下争执之际,马云龙当场操起电话,按了免提键,给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林炎志家里打电话。他在电话里将稿子读完,林炎志静默片刻说,“宣传部也要接受舆论监督。我的意见是发出来。” 第二天,这条破天荒的新闻在头版头条刊出。 类似的事情多了,“马云龙一见好新闻就兴奋”、“马云龙做新闻,六亲不认”之类的说法开始传开。甚至有部下在办公室当着马云龙的面,半是玩笑半是感慨地脱口而出:“你就是一堂吉诃德!”马云龙闻听此言,哈哈大笑。 回想起来,马云龙带领众弟兄打掉的最大一只老虎可能是张金柱,以至于直至今天,“张金柱”仍然是驾车撞人逃逸者的代名词。 1997年8月24日晚上,郑州市开发区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醉酒驾车,将苏氏父子撞翻,11岁的苏磊当场死亡,父亲苏东海卷入车底,被张金柱的座驾拖着狂奔,留下一条1500米的血路。 从这天晚上直到第二年2月26日张金柱被执行死刑,马云龙贴身指挥记者江华等人,对此案做了4个月的连续报道。张金柱臭名远扬,大河报也因此名动全国,4个月下来,发行量一路飙升3倍。 但是,成也在兹,败也在兹。就在马云龙心无旁骛、带领部下步步向前之时,他的路也越走越窄。 2000年12月25日,洛阳东都商厦一场大火,305人亡于火海。马云龙坐阵指挥,以《悲惨圣诞夜 横祸降洛阳》为题,当夜将这一重大新闻独家发出,受到有关方面批评; 2001年2月27日,刊发《靓女包围医改会》,捅出中国医药界痼疾,某部门大为光火; 2001年3月26日,转载新华社稿件《周口外商气得直哭》,被斥为“损害河南形象”; 之后,他再也没有迈进大河报办公室的那个门。 再返江湖 大凡受过牢狱之灾、半生困顿的知识分子,无外乎三种归宿:一是被整怕了,从此闭嘴,安度余生,甚至开始风花雪月;二是矫枉过正,要以今天之左来掩盖当年之右;第三类就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反而更加义无反顾。 屡挫屡奋的马云龙当属第三类。 离开大河报之后,他回到河北老家,侍奉年迈卧床的父亲,略尽孝心。之后,他重返江湖。 但是,他无处可去,于是流浪和跳槽成了这位老报人的无奈选择。 他担任过香港文汇报河南办事处主任,独家报道了柘城县农村艾滋病;他甚至还南下珠海,为珠海晚报出谋划策;直到去年8月,他才在河南商报稍微安身。 接下来就是“巨能钙含双氧水”、“聂树斌被冤杀”、“任文辉冤狱”等一个个重大新闻,从这个不甚为人所知的报社连珠炮般地捅出。 河南新闻界的人都知道,站在这些报道后面的,就是马云龙。 2004年11月16日下午,在记者初稿的基础上,马云龙亲手编写、五易其稿的调查报道《消费者当心:巨能钙有毒》确定第二天见报。巨能公司河南分公司经理来到马云龙办公室,开口承诺只要稿子不发,给他个人100万元,至于报社要多少可以自己开价。马云龙不露声色,沉着应对。一小时后,来自某要害部门的说情电话打了进来。 马云龙决定编版印刷流程提前3个小时,晚上11点之前报社所有人员下班回家,同时安排网络编辑迅速向全国100多家报社传送稿件,争取第二天全面开花。 当天深夜,商报的主管单位负责人接到指令,指派5个激光照排人员赶来强行改版。但是,整个商报社人去楼空,3层办公楼漆黑一片。有马云龙坐阵,他们来晚了。 与此同时,编辑记者们下班之后并没回家,而是兴冲冲赶往印刷厂,运送报纸。 第二天清早,当看到费尽周折的报道终于重磅推出,有的编辑记者激动得哭了。 此后,巨能公司声称河南商报诬蔑中伤,要动用法律手段。马云龙有理有据,毫不退让,随即写出7点声明;同时,他带着大河报和郑州晚报的记者,千里迢迢,赶往天津和河北沧州,一路调查,从生产车间追到供货基地,不仅掌握了巨能钙含有双氧水的铁证,更调查出使用工业级双氧水的确凿事实。 不过,巨能公司却偃旗息鼓了,马云龙策划的第二轮报道才未发出。据说,为了打官司,巨能公司请了多位专家仔细研读稿件,结果专家的结论是“这官司没法打。” 今年1月19日,郑州多家媒体报道了河北在逃嫌疑犯王书金在河南荥阳落网的消息。2月底,河南商报记者从警方得知,王书金主动交待自己曾在河北省广平县犯下一起强奸杀人案,但广平县警方却称此案已破,“凶手”聂树斌早已于10年前被执行死刑。 闻听此信,马云龙当机立断,带领记者赶往河北广平,前后去了4次,遍访聂家父母、办案律师和河北警方。3月17日,河南商报头版头条《一案两凶 谁是真凶》将这一沉年冤案兜底托出,舆论一片哗然,3天之内,新浪网的网友评论高达7万多条。 碍于种种限制,重归江湖的马云龙无法全力出击。 很多时候,他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新闻,而是如何才能继续在新闻一线安全地呆下去,如何不失去现在的机会,不致再次“流浪”。 因此,他把自己的目标压得很低,“巨能钙调查、聂树斌冤杀案,这样的新闻,两个月做出1个,一年能做6个,就是我的理想”。 至于亲自采访、写稿、编版、写评论,马云龙认为是“为了自己良心上的平衡,同时也让后人知道,我们这一代人不是没有努力过。” 性情硬汉 还是在大河报时,马云龙有一张“工作照”,背景不是办公室,而是郑州街头。光头墨镜、T恤衫牛仔裤,腰间配一腰包,身后是麾下几位手持长枪短炮的摄影记者;他本人双手叉腰,站在马路中间,面目冷峻,威风凛凛,势不可敌。 他的昔日部下都知道,这只是“六亲不认”的马云龙,并不是“让人喜欢”的“马老爷子”。 首先,马老爷子一有好新闻就兴奋,一兴奋就要和大家喝个痛快。马云龙自己也承认,“总编不过是个记者头儿,活干完了,干高兴了,弟兄们一块喝酒去!” 1995年10月15日,1岁半的小女孩李恒掉进建筑工地深达8米的地桩洞里,300名民警展开了几个小时的大营救,大河报摄影记者陈更生拍回了独家照片。照片冲洗出来之后,陈更生很兴奋,但是,马云龙比他还要兴奋,连声叫好。当整整3个版的现场图片报道全部编妥,马云龙从家中拿来两样东西,一手拎着的是剑南春,另一手是一条三五烟。 其次,老爷子雷厉风行,作风硬朗,有时急了还会骂人。 1998年1月12日上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张金柱死刑,马云龙离开法院时已是9点多,这时当天的大河报还没上报摊,就在等这条消息。在回报社的车里,马云龙用手机给编辑部口授稿件,有一个词说了几次,编辑都没听清,马云龙那个急啊。同车的刘书志说,“云龙急眼了,那个词重复一遍就骂一句‘傻B’,他连骂了6个‘傻B’!” 2002年底,大河报举行春节团拜会,邀请马云龙参加。马云龙在河北老家侍候重病的老父亲一年了,几乎没在郑州呆着,也就答应了。他没想到的是,编辑记者们一见推门进来的是一年半没见面的老马,全体起立,鼓掌10分钟! 和马云龙共事近20年的刘书志深知,新闻硬汉马云龙也有温情的一面。 2001年5月马云龙离开大河报之后,陷入长时间的苦闷,于是和报社的几个哥们在一起,关起门来喝酒。刘书志亲眼看到黯然神伤的马云龙无法自持,两度落泪,“突然地痛哭,涕泪长流,然后又突然地收住眼泪”。 马云龙自称,在郑州他有3个生活圈子:一是同事和部下;二是因为特殊经历结识的民间思想者;第三就是“报社看大门的、司机班的司机、印刷厂的师傅”。在第三个圈子里,他们都叫他“马哥”,一见面,“马哥,喝酒去”,“马哥,最近有事没有?有没有谁欺负咱?有的话咱打他去!” 因为采访聂树斌案,他去了4次聂家,并和“可怜的”聂父聂母结下感情。他告诉两位年迈的老人,等到聂树斌平反那一天,他会专程到他们儿子的坟前,为他扫墓献花。 在报道周口二级警督袁文龙被山西临汾关进冤狱一案时,他再次承诺,只要袁文龙获释,他就要亲自开车把他从临汾接回周口老家。 还是在河南商报,在编写一篇无良中介将无辜农民骗到海外做苦役的稿件时,看到这些中原农民沦为“现代农奴”,他潸然泪下。 但在另外一些场合,马云龙则被视为“狂人”和“怪人”。 多年以前,马云龙就有了副高职称,此后,他一直拒绝参评。2000年,社长和总编强令他参加。谁也没想到,评审会上,轮到马云龙个人自述时,他开口就说:“这评职称在我眼里就像大街上耍猴的一样,敲一声锣,猴子就得翻一跟头。现在你也别敲锣,我也不翻跟头。它对我什么也不是,评上了我不高兴,评不上我也不会难过。” 15分钟的个人自述,马云龙三下五除二把这些意思讲完了,又是扬长而去。 采访结束时,记者和马云龙有一段对话: “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非常不满意。” “在河南这么多年,你孤独吗?” “非常孤独。” “我们永远不能声明放弃打老虎的权利!” 图/受访者提供 相关专题:南方人物周刊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南方人物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