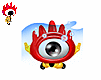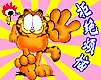| 舒芜:走出“胡风事件”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18日13:18 时代人物周报 | |
|
舒芜老人早已走出“胡风事件”,现在心平如水,他说:“我对女性一直有很好的感觉”,所以有了《哀妇人》这样的新作 本报记者 赵倩 舒芜引起我们的关注,应该是从“胡风事件”开始,他是当年“胡风事件”的关键 我对女性一直有很美好的感觉 时代人物周报:最近您又有两本书面市:《红楼说梦》和《哀妇人》,这些年您还在不断地写作吗? 舒芜:打倒四人帮之后,《红楼说梦》曾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那时的书名是《说梦录》。但后来感觉不太像是一部关于《红楼梦》的作品,所以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推出新版本的时候改名为《红楼说梦》。内容是一样的,只是有些小的细节上的改动,比如加了清人改琦的插图等等。 《哀妇人》里的文章都是以前我写的关于女性问题的随笔。复旦一个研究女性问题的学生,看了大量我写的关于女性问题的作品,鼓励我把稿子结集出版,于是就有了《哀妇人》这本书。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写那么多关注女性的文章,回头来看觉得也很有趣。 时代人物周报:您为什么会这么关注女性问题? 舒芜:我想这主要和我的母亲有关。我们一家原来生活在北京,后来父亲另续一房妻室,我和母亲就搬回安徽老家生活,父亲在全国各地辗转教书。虽然有父亲,实际上就像一个单亲家庭。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说过父亲一句坏话,对父亲也从来没有怨言。还总是跟我说父亲怎么读书,怎么有学问。“我不能因为我离间他们父子的感情,”这是母亲曾经说过的话。但母亲对她和父亲不多几年的共同生活很是怀念,常和我聊他们生活中琐碎的小事,连他们吵架都谈得很有趣。我读书后母亲还不断督促我每个月要给父亲写封信。我从母亲那里感觉到女性的伟大,觉得女性很值得敬佩。 由于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和女性亲戚的来往就比较多,她们都很漂亮,所以我对女性一直有很美好的感觉。 还有一点就是,我很早就接触了新文学。我的堂哥方玮德是当时新月派的诗人,他有很多书,书中有鲁迅、周作人等提出的“要尊重女性”的观点,尤其是周作人,对我影响很大。 时代人物周报:您对周作人也很有研究? 舒芜:还没上中学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周作人的作品。关于他对女性问题的研究,我曾经编过一本书《女性的发现》专门来谈。尽管我们对周作人抗战时期政治上的问题比较愤慨,但他的功劳不可抹杀,尤其是关于女性思想解放,不仅仅是一种朴素的感情,甚至可以说是博大精深。 我想和“红学家”划清界限 时代人物周报:《红楼说梦》里是不是也有大量关于女性问题的观点? 舒芜:曹雪芹是最了解女性悲剧的,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这个悲剧是从曹雪芹眼中看到的悲剧,也就是贾宝玉看到的悲剧,这比女性自己看到的悲剧更深刻。价值各有不同的标准,贾母、贾政还有平儿、香菱等看起来可能都不是悲剧,只有贾宝玉才真正了解女性的价值。所以说,女性的价值要看是谁的标准。如果女性解放运动由女性自己发动,也许并没有什么;但另一方面,从那些有觉悟的男性的视角出发,“哀妇人为其代言”(周作人语),有时候会比女性本身更具代表性。 时代人物周报:您对《红楼梦》是非常有研究的,但您一直强调您是一位普通读者,为什么? 舒芜:我主要是想和有些所谓的“红学家”划清界限。现在的“红学家”有两种,一种确实是在踏踏实实地做“红学”方面的研究,帮助读者多掌握一些资料。还有一种把《红楼梦》看成是莫名其妙的东西,里面有多么了不起的文化意义、政治意义,甚至越讲越玄。其实《红楼梦》就是一部小说,和别的小说没有什么不同。我对红学没有兴趣,我就是一个普通读者。曹雪芹也是写给普通读者看,而不是专给“红学家”看。“ 时代人物周报:在当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中,您是怎样的观点? 舒芜:当时我主要是批判俞平伯的“钗黛合一”论。其实“钗黛合一”并不是俞平伯的发明,脂砚斋早就强调过这样的观点,而且《红楼梦》的前四十回在曹雪芹的笔下也有这样的倾向。但我认为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最大的贡献就是悲剧结局,强调了钗黛的矛盾。鲁迅的观点也是这样,认为它冲破了以前小说对人的蒙骗。 1954年批判俞平伯时,我曾经写文章表达“批判钗黛合一,强调钗黛矛盾”的观点。当时我为了强调钗黛矛盾,把宝钗写得像个特务似的,其实那是不对的,主要是我当年的幼稚造成的。宝钗其实还是一个好姑娘,仅仅是因为她把自己纳入封建的规范中去了,是一个情商比较低的人。现在看来当时批判俞平伯是小题大做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学术观点,却把它纳入了“政治公式”中。但现在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后四十回从文笔上讲比前八十回相差很远,但它的悲剧结局非常成功,而且把前八十回“钗黛合一”的思想挽救回来,确实是它的功劳。 “胡风事件”有出入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人们提起您,总是把您和当年的“胡风事件”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颇多争议,您怎么看? 舒芜:“胡风事件”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交信不交信”的问题。其实当时并不存在“交信”的问题。那件事情可以这样说,甲有一件东西,乙借去了,丙在甲乙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给了丁看。甲就是我,乙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丙是当时《人民日报》文学组组长袁水拍,丁就是林默涵。当时《人民日报》命题叫我写一篇《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文中引用了胡风给我的信中的部分内容,叶遥借去这些信核对。那时候胡风已经被上升到反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了,所以这篇文章在当时批判胡风的时候是一个很次要的内容。叶遥拿到信之后也没有意识到什么,但袁水拍看后觉得很重要,就送到林默涵那里去了。这件事我和叶遥都不知道。 林默涵后来找到我,我才知道信已经到他手里。林默涵说,你的文章不用发表了,人家已经不想看你说什么,人家要看胡风说什么。当时林默涵作为中宣部文艺局长是非常有权威的,我也不敢反对。但林还留有余地地说:“当然不是说胡风是反革命,但这一次胡风真的很反动。你就把这个写出来,再加上简单的注解。”所谓第一批材料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说,在那种情况下,我确实没有交信。叶遥向我借,她也不知道要送上去。袁水拍拿去也没有告诉叶遥就送到林默涵那里。 时代人物周报:当时您真的认为胡风所做的事情是在“反党反人民”吗? 舒芜:这个事情说起来就复杂了。我从抗战初期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走错门了。事实上,我是从斯大林主义入门的。我看的第一个领袖传记就是《斯大林传》,那时候对斯大林崇拜得不得了。后来大家公认的观点就是斯大林把“哲学政治化”,每一条哲学是非都落实到政治是非,这也是斯大林的特点。 解放后,我的处境和其他所谓“胡风分子”有一点不一样。那时候我在广西南宁,是全国最晚解放的地方。当时把我安排到“知识分子改造”领导层的地位,主持教师学习班等。对于所有胡风的问题,我觉得,我和胡风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不过是其中比较次的一派,我是诚心诚意希望把胡风改造起来,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我和胡风不断交换意见,后来发现和他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于是就发表文章,表达我自己想改造的意见,希望别人也改造。当时就是这样的出发点,确确实实相信思想改造,认为改造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后来批判的浪潮越来越高,到展开胡风大批判的时候,感觉就不同了,胡风事件的性质就成了反马克思主义。 “胡风事件”之前,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中,许多著名知识分子都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的检查。回头看这些,要说是逼迫,好像又不是那么简单。人的思想有时离不开大环境的影响,当时国家是这样,就要这么跟着国家走。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相信革命会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胡风这件事也是这样,要说我当时是趋炎附势、贪生怕死,也不是那么回事,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就是会那样做。 时代人物周报:50多年过去了,您对当年的“胡风事件”是不是有了自己新的看法? 舒芜:当然有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所谓“思想改造的公式”就是“不革命=反革命”。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想,胡风的案件是个焦点,冲出焦点,回想知识分子所走的路,可以说,20世纪的经验需要整个21世纪来消化。上世纪30年代,全世界知识分子左倾,鲁迅、罗曼·罗兰等世界知名作家都是这样。当年曾经有一个记者从苏联归来,写了一篇关于“苏联真相”的文章,遭到全世界的攻击。现在想起来,这里面其实问题很大。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面对别人对您或褒或贬的两种不同的评价时,您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舒芜:那无所谓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评价。过去很多人对我的印象不好,这我可以理解,换上我,我也不会有什么好感觉的。但事实是,包括交信等问题,都是有出入的。 相关专题:新浪人物 |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浪人物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