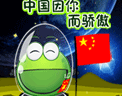巴金:百年行程中的文化创造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0月18日12:28 新浪文化 | ||
|
作者:李 辉 走在巴黎,便走进了历史长河。不经意间走进一条小巷,一幢老房子,或者一个咖啡馆,也许就能飞溅起几朵浪花,将怀古幽情敲打,行囊和衣衫顿时湿成一片,伴着脚步缓行。
如此这般走在巴黎,我走进了巴金的历史。 说不完的故事,看不厌的景致,浓得化不开的历史情结。 沿着塞纳河缓行,注目河水流淌。抬起头,巴黎圣母院无言高耸,听不见雨果描写过的钟声。攀上钟楼,俯瞰四周。河南岸,是拉丁区和卢森堡区,小巷弯弯曲曲,网一样蔓延着。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时光就是在下面的一个个网眼里闪过。巴金1927年来到巴黎时,就在河对岸的一座小旅店里寄寓。拿着地图,望着对岸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建筑,我试图辨认早就通过巴金的叙述而熟悉了的一切:先贤祠(国葬院)、卢森堡公园、河边的旧书摊…… 当我在巴黎感受巴金时,随身还带了一本书,是诗人梁宗岱的《诗与真》。我一直喜欢这本书,欣赏梁宗岱用诗人的语言对诗与艺术所作的阐释。来到巴黎,只带这一本书,在于梁宗岱用了不少篇幅描述他在巴黎留学时与巴黎诗人的接触,以及历史上诸多法国文学家在巴黎的生活。我把它当作另外一种别有天地的旅游手册。 一个有意思的对照。梁宗岱与巴金差不多同时都在巴黎,让他陶醉的是诗,是美术。不仅仅是他,在此前后,到过巴黎并且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理论家的还有朱光潜、冯至、傅雷等,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在巴黎这座文化之都感受艺术的熏陶,探索艺术的奥妙。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同时期的巴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巴黎让巴金迷恋的不是艺术,而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是血与火的恐怖画面中高扬的英雄主义,是强大的政府权力下个体生命的反抗、呼喊。三十年代,巴金曾就《蒙娜丽莎》到底是否为油画与朱光潜进行过争论,由此可见,当他徘徊卢梭雕像前的那些日子里,他也曾走进卢浮宫参观。但是,这座城市所含蕴的伟大、悠久的文化传统,一个个博物馆里展示的文物、绘画等等人类艺术的精华,在他关于巴黎生活的回忆中,并没有什么叙述。相反,在1932年他写的《灵魂的呼号》中,我们看到的是他用相当激烈的言辞贬斥卢浮宫,贬斥艺术: 我不是个艺术家。人说生命是短促的,艺术是长久的,我却认为还有一个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那个东西迷住了我。为了它我甘愿舍弃艺术,没有一点顾惜。艺术算得什么?假若它不能够给多数人带来一点光明,假若它不能够对黑暗给一个打击。整个庞贝城都会埋在地下,难道将来不会有一把火烧毁了艺术的宝藏,巴黎的鲁佛尔宫?假若人们把艺术永远和多数人隔离,像现在遗老遗少们鉴赏古画那样,谁又能保得住大愤怒爆发的时候,一切艺术的宝藏还会保存着它们的骄傲的地位?老实说,我最近在北平游过故宫和三殿,我看过了那令人惊叹的所谓不朽的宝藏,我就有一个思想,就是没有它们,中国决不会变得更坏一点,然而另一些艺术家却诚惶诚恐地说失掉它们中国就不会存在。大多数民众的痛苦和希望在他们看来是极小极小的事情。 巴金正是从特殊的政治标准出发,强调文学的功利作用,从现实革命的角度而反对纯艺术,反对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巴金在1935年和吴朗西、伍禅等人一起创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并担任出版社的总编辑。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巴金同时也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出版家。 如同走向文学之路是政治生活的延续一样,热衷于出版对于巴金来说,同样是他的政治生活的延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更多的寄寓理想与信仰的成分。与现代出版史上其他一些著名出版社有很大不同,文化生活出版社是典型的同人出版社,主要参与者,如巴金、吴朗西、伍禅、丽尼、陆蠡、朱洗等,赢利不是他们的目的,有的工作人员甚至分文不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鼎盛时期,那是一个和谐、友好、无私的集体,就如同巴金过去梦想过的境界一样。 似乎是矛盾的现象。在以偏激的言辞批判传统文化的同时,成为作家和出版家的巴金,又实际上是在履行着文化创造的使命,是在以显赫的业绩汇入文化的长河。 巴金对艺术、对传统文化所做的那些批判,是在特定历史范畴内特意表现出革命的姿态,甚至还可看作他在因现实的郁闷、刺激而发泄不满时,特意选定的表述方式。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一思想带来的副作用。正由于早在十几岁时就选择了来自西方的思潮,巴金所熟悉的和研究的大多是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他感兴趣并予以描写和赞美的也以外国人物居多。相对而言,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方面的修养,是他的弱项。他很少用毛笔写字,在同时代的作家中,茅盾、冰心、沈从文等擅长书法,而巴金却远远不及。他的作品中,很少看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也较少引用古诗古文,更不习惯于使用典故,而这在不少作家那里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随着年岁增长,巴金身上的激烈情绪渐渐淡化,自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之后,我们便可以看出巴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所转变。在他的堆满着外文书籍的书橱里,也开始出现了明代万历刻的线装本《批点唐诗正声》。传统旧戏也不再被他视作攻击对象了。尤其是川戏,成为他的业余爱好。据他的朋友回忆,五十年代初他在兴致好的时候,可以随口背诵许多古诗,包括《长恨歌》、《琵琶行》那样的长篇,这很使人想起巴金在幼年时候,由他母亲亲自教诵《白香词谱》的情景。也许到了中年以后,母亲在无意中留给作家的古典文学的修养方始开出了灿烂之花,这些美学趣味上的变异,与作家的生活环境,政治情绪都有密切的关系。 对于年轻时候的行为,晚年巴金作了认真的反省:“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他对简化汉字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如果汉字走向拼音化,“这样我们连李白、杜甫也要丢掉了。”然后他说:“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遗产,谁也无权把它们抛在垃圾箱里。”他的这番话,与1932年的激烈,形成了鲜明对照。 随着偏激思想与情绪的消退,浓厚的文化兴趣与独特的艺术鉴赏力,在巴金身上凸现出来。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等人的著作的同时,他翻译了历来被认为是唯美作家王尔德的童话;他酷爱买书、藏书,在同时代作家中其藏书量名列前茅。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他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业绩。 《巴金传》的作者陈丹晨先生有一个见解,他说巴金一生的编辑出版活动,从1934年创办《文学季刊》到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再到1957年创刊的《收获》,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这是一个宽泛的文化圈。不是流派,不是团体,没有明确的、一致的文学主张,但巴金以绝不惟利是图的严肃出版理念、以杰出的文化判断力和认真的编辑态度、以真诚、热情的友谊,把一大批作者吸引在他的周围。 他说得不错。当年,曹禺、萧乾、鲁彦、刘白羽、何其芳、卞之琳、罗淑、严文井、荒煤……一批作家的处女作或代表作,都是由巴金发表和出版。八十年代初,从维熙、谌容、张洁、冯骥才、沙叶新、张一弓、张辛欣等不少在新时期走上文坛的作家,同样得到了巴金的扶持、鼓励和保护。特别每当有年轻作家受到不公正的批评时,巴金总是公开站出来发表文章,声援他们,为他们辩护。从而在八十年代文坛,对于那些受惠于巴金的作家们来说,作为编辑家、出版家的巴金,无疑也是一棵为他们挡住风沙的大树。 在我后来接触到的萧乾、严文井、荒煤、卞之琳、谌容、从维熙、沙叶新、张辛欣等作家那里,我不断听到他们发自内心的对巴金的敬重与感激。 谈到处女作《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发表,从维熙至今对巴金充满感激之情: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两个凡是”正在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面对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返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的速度和头题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能不能问世,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未知数X!(《巴金箴言伴我行——贺巴金九九重阳》) 巴金不正是在一个个类似的故事中进行着文化的创造与积累吗? 作者简介: 李辉,1956年出生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在北京《北京晚报》担任文艺记者和文学副刊编辑;1987年11月至今,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担任副刊编辑。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沧桑看云》、《李辉文集》五卷等。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相关专题:巴金逝世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巴金逝世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