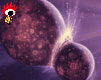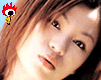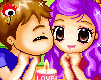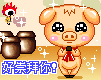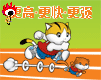| 经要读 理也要讲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7日12:00 新民周刊 | |||||||||
|
撰稿/胡晓明 “强迫孩子在3-12岁期间背15万字自己并不懂的东西”,这违反了教育即发蒙开窍的本来意义;同时也妨碍了孩子们接触多元的文化,违反了“少年儿童的人权”。这是蒋庆编所编12册“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被人斥为“蒙昧”的理由之一。批评者认为这“教育诵本”不仅得不到孩子们的喜欢,不仅竞争不过西方少年儿童教育读物,而且是文化保
无独有偶,被人称为21世纪“新读经运动”遭受抵制的另一起事件,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道德经选修课”,先是被各大媒体宣传得很风光,说是已经成为该校最受学生欢迎的选修课之一,先后有8000多人修过,这学期就有1000多人选修。忽然有学者们指责该选修课的教材,解释得“百孔千疮”、充满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是一本很不合格的教材;这样去讲《道德经》,完全是糟蹋经典,误人子弟,反而将不良学风带给了学生《“熊释”〈道德经〉引发争议》,载《中华读书报》7月7日。 养在博物馆或研究院的中华传统文化,重新回归生活实践,本来是大好事。稍知20世纪百年思想史的人,都会认识到两个事实,一是中国文化,已经边缘化得很厉害,文化的危机,与文化的断层,大有关系。二是文化的战争,其实不如文化的和平建设,更有益于世道人心。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好事,却引起负面的效果?这是因为做好事的人,与反对这事的人,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两种不同的正当性要求,这两种正当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你死我活的关系,但是却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了,这就成为新的冲突。化解这样的冲突,需要的是“区分”的智慧和“沟通”的理性。 什么是沟通的理性呢?并不是勉强的形式主义的沟通,而是实质理性的沟通。有一个理念就是,传统/现代,并非二元论。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也不是与现代打成两截、甚至相反的东西。在中外学术界,渐已成为一种思想共识。这正是沟通的基础。 譬如儿童在13岁以前,充分开发他的语言记忆能力,多诵读一些经典,这是中国的蒙学传统,其中具有相当现代的合理因素。 第一,充分尊重儿童生理阶段的特殊性。根据语言学家研究,人类学语言最快的时期是从0岁到3-4岁,称为语言的天赋期。此时的语言识记能力极强,能快速背诵,尤其是对语音韵律特别敏感。中国强调背诵的传统,与现代强调儿童识记的科学,在这一点上相互支援,共同肯定了以记诵为特点的学习是科学的方式。文言古诗的短小、韵律,既适应了儿童心理特点,通过诵读的反复刺激,有助于早期语言能力的开发,同时也刻下了文言语法与词汇的心理底子。 第二,哲学史家和教育心理学家对科学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类的学习能力,很大一部分、甚至很重要的一部分,应是默会知识tacik knowledge的学习,即潜移默化的学习。看起来学了他不懂的内容,看起来他真正记得的也并不多,其实这些将转变成一种“内隐记忆”,在心理背景中渐渐会产生作用。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反而有时候过于用一些看起来很道理化的内容,去晓之、知之,可能会伤及学生的未知能力。所以,表面上是“蒙昧”的传统做法,其实是有其科学的合理因素的。 再次,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语言并非只有单一的交流功能。有些书面语言,具有某种高强度的“储蓄”功能,即存储人类文化遗产的多元丰富信息,而“储蓄”越早,“利息”越丰厚;“储蓄”的习惯越早养成,“理财”的本领越大。无论是语言文字的敏感度和接受力,还是道德情操的幅度、文化心灵的动力,早开发早受益。梁启超早说过,文言“成诵易记”,这是它“含金量”大、“提取方便”的原因。尊重文言的这一功能,也正是科学的态度。 第四,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又表明,语言与语言的社会性格是不一样的。语言有雅俗之分。文言由于与当代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缺点是生动性不够,优点是距离产生美。相对而言,对于生活的俗化、平庸化也有了一点的隔离效果,不至于一损俱损,遭生活的妖化。因此也相对地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权威性和圣洁性。这对于用于教谕式、启示式的语言功能,有优于白话的效果。因而让孩子较早打下这种语言的底子,无疑是道德生活的童子功,精神成人的培本固元。 最后,文化学家的研究越来越表明,人性无善无恶,其实是文化建构出来的。你可以用游戏文化,去建构一个暴戾的人;也可以用经典文化,去建构一个知书达礼的人。未来的人性,在于今天的选择。并不是说现代语文教育,必然建构不出知书达礼的人,而是说,正如不少人已经意识到的那样,现代文化自身由于先天失调,在这方面缺乏自觉的反省,可能强化了其他内容,而弱化了这方面的教育旨趣。20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化意识,是想去建构符合进化的强大国家需要的进化的强大的人,但是恰恰缺乏反省的是,如何成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一个守秩序的人,却被删除了。而有良知、守秩序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具有现代理性的人。这一点,现代文化越来越多地认识到了。因而,这既是千年文化经典在今天的正当性,又是它富有新意的现代性。 由于现代社会是以人的自主性为基础的社会,所以现代教育终究还是要以启蒙式为主,尤其在中国广大农村,更重要的是现代公民的素质教育应从小抓起。这就注定了读经不可能成为儿童教育的主流模式。然而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对儿童读经的看法必然是:读经是现代教育重要的补充。与其他教育方式的关系,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沟通的理性,看到传统里的现代,以化解单面的现代立场的僵硬性。 什么叫“区分”的智慧呢?蒋庆批评蔡元培下令取消读经,但是他显然忘记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如果说传统社会是没有分化的、价值现成化、思想定于一尊的社会,那么,现代社会则是分化的、个人自主的、失去宇宙意义公设的社会。因而,蔡元培取消自上而下的教育部读经令,是具有教育理性的正当性的,是中国现代理性化进程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今天由蒋庆先生来做读经这件事,正体现了政府的归政府、信仰的归信仰,心灵的归心灵,这正是分化社会的理性。在社会与个人自主性充分提升的时代,尤其是在《行政许可法》颁行的今天,蒋庆先生再提倡由政府来主持自上而下的读经,明显不合时宜了。蒋庆先生的第二个不妥当,是他没有讲清楚,经典并不是儿童唯一的阅读材料,读经并不是儿童教育的唯一方式,这就导致了薛涌批评他侵犯了“少年儿童的人权”。其实薛的说法也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所谓儿童人权,一方面包含着大人的教育权监护权,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儿童自己的文化权,即儿童有储蓄、传承文化遗产的权利。因而薛涌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你批评读经妨碍了儿童接触多元文化资源,何以见得读经就一定是与其他文化童话、游戏、讲道理式的教育相冲突?为什么不可以一天里该读经时就读经,该讲故事就讲故事?或者,有些人多读经,有些人多讲故事?至于薛氏批评美国的华人小孩读不了中国书,那是因为美国根本没有学中文的“气场”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地方说什么话。看这样的问题更是不能缺少“区分”智慧。 至于说到“熊版道德经”,我以为,熊某本意可能是为了弘扬文化传统,然而之所以会带来负面的效应,首先是他忘记了,传统文化,其实在长期的诠释与学问历史中,已经形成了相当深厚的学术理性传统;这个传统中的“学统”,其实正是传统中的现代因素,正是与传统生命相联的存在。你不尊重这个学统,就会损害你讲的文化传统本身。这就是经典之所以被“糟蹋”的逻辑。 其次,他也忘记了两个“区分”的原则,一是真的与好的,要分开的原则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适当分开的原则,你不能把你的东西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却是假的表演魔术除外。在现代生活中,任何知识与价值都必须经受形式理性基本逻辑规则、约定俗成的确定性,以及主体的真诚性的检证,取得重要的客观性,才能具有真实的意义,不然就是一场又一场的骗局而已。《道德经》的文字和知识,尤其是在上世纪的现代学术进程中,获得了相当重要的客观性,不能对此视而不见。二是大学首先是讲授和传递知识的地方,而不是文字游戏和宣扬自我主观性的地方。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搞笑、戏说,可以在教堂里或家中教诲、布道,但是利用三尺讲台的权威性公共资源,对八千名渴望知识的学子,贩卖一己主观的偶思零想,推行一种恶劣的学风,这不是典型的以权谋私,又是什么? 这两件事,恰是转型时代的征兆:一方面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华文化主体的再认,以及价值迷失中中华文化认同的需求,因而在上个世纪总体上被压抑的文化传统,又有了一点复苏,一点新机;另一方面我们又生活在一些僵硬的思想模式和落后的思想习惯中,因而复苏文化传统的“正当性”,又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20世纪百年思想史的一大主题,即不断重复的中西/古今冲突,在比较高的层次,其实多有化解之道。然而似乎在中国一般社会生活中,遇到具体问题,仍一次次重蹈旧辙,传统与现代,俨然是两截。何时才能有更宽容的智慧,同时又是更充足的理性呢?“经要读,理也要讲”,但愿可能代替王子复仇式的提问:“读还是不读,这是一个问题。”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