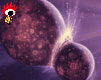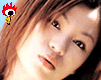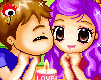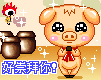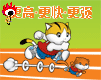| 老房子、老先生及海派风度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27日12:08 新民周刊 | |||||||||
|
访作家程乃珊 撰稿/张晓春 陈怡雯(实习记者) 如果将中国比作一个大舞池,大概只有上海这座城市才能跳出耐人寻味的探戈神韵。而用文字来捕捉、描绘并解读这 样的韵味,程乃珊可谓高手。这一方面源于她的家族百年
城市与都会 新民周刊:经常听到您用“都会”来形容上海,为什么不用“城市”呢?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程乃珊:我觉得,城市这个名字其实是空的,它一定要由建筑、人、传奇构成,所以都会和城市是不同的,我们全中 国现在可以说有两个都会,一个是上海,一个是香港。我们大城市有很多,但大城市和都会是不可以画等号的。都会永远能够 创造一种时尚,都会创造的时尚是可以让其他城市来fallow(遵从)的。大城市可以面积很大,人很多,而都会面积不 一定大,但它永远可以创造一种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真的是我们中国的骄傲。 都会里的建筑 新民周刊:自从你的小说《蓝屋》问世以后,我发现您对建筑,特别是老建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近年来“蓝屋”的 原型,铜仁路上的绿屋受到媒体的关注,这除了因为社会普遍关注财富,继而关注当年承载了财富与身份的老房子外,应该说 ,你赋予绿屋的描述,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程乃珊:在电影里有时会看到有人拿着烛灯到古堡去,大声问“有人吗?有人吗?”我完全相信,人是万物之灵,几 代人住过的房子,一定会产生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种氛围。建筑是人与时空的对话,其中一定会有一种精神留下来 。有一个地产商说他仿造上海以前法租界的花园洋房造了一幢别墅,让我们去参观。这个别墅完全是按照衡山路、华山路上的 洋房造的,但看了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劲,后来想想这个别墅太新了。一个好的花园洋房外面一定要有爬山虎,墙壁上还要长 有青苔,这样的老洋房就有味道了。新造的好看是好看,但没有味道,缺少一种历史的痕迹。所以我很喜欢去参观名人的故宅 ,我会发现那房子里留有前人住过的一些痕迹。城市建筑就是一个城市的外观。我从小就喜欢看老房子,可能我自己也是在老 房子里长大的。每一栋老房子它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造这个房子,应该都是有历史的。 新民周刊:就比如“蓝屋”吗? 程乃珊:是的,不过它不是蓝色的,而是绿色的。在上海铜仁路333号。它外面是由绿的贴面砖砌成的,通常上海 人叫它“绿房子”。 绿房子的故事 小时候我家住在南京西路,经常路过绿房子。我常看到在“绿房子”四楼,有很多穿着时髦的男男女女,将唱机放在 阳台上放音乐。听家里老人说,这幢绿屋的主人叫吴同文。“文革”开始以后,吴同文和他的小老婆一起在这里自杀了,房子 的玻璃都被打碎,大字报从四楼一直贴到下面,风吹雨打,变成一丝一丝的,周围的邻居说这栋房子晚上会闹鬼,听到有哭声 ,叫人寒毛凛凛的。后来很巧,1970年代,我结婚了,我先生来自这个房子里面,他是吴同文的外孙。 我的先生告诉我,吴同文念过很多大学,毕业文凭一张也没见到。但没有大学文凭,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本事,没有文 化。1932年,日本对华侵略扩张,吴同文有种预感,觉得中国这场仗是避免不了的。于是他就开发军绿色颜料,结果绿色 为他挣了很多钱,绿色颜料后来几乎由他垄断,只有他的公司才能生产绿色颜料,所以他觉得绿色是他的luckycolour ,他的宝马车也是绿色的。等他钱挣得差不多了,他想造一座自己喜欢的房子,他就找来邬达克。邬是一个建筑师。吴同文之 所以选这个地址,是因为当时的北京西路叫爱文尼路,而与之垂直的叫哈同路,这两条路的路名中正好嵌有他的名字,所以他 的门就开在今天的北京西路和铜仁路交界的地方。他对邬达克说:“我要的房子是上海独一无二的。”当时,上海的花园洋房 很多都是西班牙式的、英国乡村式的、德国式的……他说他的房子要很时髦很现代的。因而邬达克就给他设计了这座房子,阳 台上没有柱子,这在1930年代时是非常现代的。邬达克对他说:“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房子再过50年,也是最现代的 。”房子在1938年完工。当时的《上海日报》将它称为“远东第一豪宅”。总共四层楼的房子还配有电梯,它是上海私人 房子第一家装电梯的。电梯门是弧形的,整栋房子是圆的,圆的被认为可以化解凶险。另外,电梯门不是金属的,而是木制的 ,显得很豪华。 吴同文有两房太太。大太太就像终身制,而小老婆就像合同工,什么时候不要就不要了,所以几乎所有的小老婆公关 手段都特别高明。大太太的所有子女都说二太太比自己的妈妈还要关心他们,连佣人也说:“大太太脾气大,二太太客气。” “文革”开始,1966年8月23日抄家,吴同文大概在9月份没到就自杀了,可能因为他一辈子都没经历过这种 事,红卫兵斗他斗得太厉害。自杀其实也看得出文化,这是人对生命的一种态度。吴同文自杀时,他的二太太煮了一壶咖啡, 他们每人一瓶安眠药,咖啡中搭安眠药是没法救的。吴同文西装是不敢穿了,他穿着人民装,手里拿着“公安十六条”,即“ 要文斗不要武斗”。姨太太则穿一身中装,化了妆,两个人手拉手去世了。到发现的时候两人的手拉不开了。 上世纪90年代有一天,我走过这房子时,发现房子已经全部装修好了,像一位醒来的“睡美人”,很漂亮。我很想 知道是谁装修的。我先生进去后回来告诉我,里面住着一位台湾建筑师。 我说我一定要去见见他。我去了,这个建筑师看了我半天,他说:“你是不是程乃珊?”我说:“我是啊!你怎么会 知道我啊?”他就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我是你《蓝屋》里面的顾传辉啊!我回来了。”我非常惊讶。我为《蓝屋》主人公 取的名字就是顾传辉,而他的名字居然与我小说里虚构的名字一样,唯一不同的就是我用的是光辉的“辉”,而他是“晖”。 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他也是上海人,父亲是飞行员,他生在台湾,后来自己学建筑。1990年到上海,无意间看到这绿房子 ,他觉得这与他看到的其他房子完全不同,这座绿房子是完全超现代的。他就通过很多途径,将这个房子的租赁权拿了下来。 并将它整旧如旧。 所以我说都会永远有那么多传奇。我曾问顾传晖,怕不怕房子闹鬼,他说:“不怕,如果他们两个人出现,我就请他 们坐下来,听他们讲讲绿房子的故事。” 都会里的人 新民周刊:最近,看到您写的文章里有很多老上海人的故事,这些人是怎么进入你的视野的? 程乃珊:我有个特点,会随身带一本笔记本,就喜欢到处找一些上海的老人,让他们讲他们熟悉的上海的故事,所以 这么多的故事其实都是他们告诉我的。有时候一些朋友、读者会很热情,打电话来告诉我:“有一位某某某,他知道很多很多 上海的故事,你快去问问。”所以我女儿老是笑我,她说:“妈妈,你不如到养老院去工作算了,那儿都是老头老太,你慢慢 去问好了。”但是我就觉得这里确实包含很多历史,他们有对历史的直感。 新民周刊:前面您说,城市一定要由建筑、人、传奇构成。那么,在您寻访的老上海的故事中,有没有给您印象特别 深刻的都会人的故事呢? 程乃珊:当然有。巴黎有句话说的是:“巴黎街头掉下一块砖头,说不定砸到的就是一个艺术家。”那么我说上海街 头要是掉下一块砖头,砸到的人一定是somebody,是有点来历的人。上海马路上有来历的人很多很多,真人不露相, 大隐隐于市。我认识一对老夫妻,他们的故事真的很感人。老先生今年89岁,老太太94岁,我和他们现在成了忘年交。也 是因为我的一个学生打电话给我:“每天有一对老夫妻都到同一家饭店吃饭,你一定会感兴趣的。”我就去了,于是就认识了 。 李先生和他太太的故事 李太太是我们中国第一代的女飞行员,她在1936年就去学开飞机了,当时有个“中华飞行社”,就设在今天延安 中路和陕西北路的转角上。无论是谁,只要付了钱,报了名,就可以学。上海的1936年就已经不是学开私家车,而是学开 飞机了。我们写文章的就有个缺点,老是将一个平凡的事放大、人为拔高。我说:“李伯母,你是不是当年看到中国面临日本 侵华的威胁,所以要学开飞机?”李太太说:“什么呀!当时我们根本不关心这些事的。”我说:“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去学开 飞机?”她说:“地上行的东西我都会驾驭了,骑自行车,骑马,驾驶汽车都会了,但空中飞机不会开,就去学了。”她还告 诉我一个骑马的细节。她说:“骑马,两个脚一定要夹住马的肚皮,如果夹不住,马就不会听你的操纵。但我老是夹不住马肚 皮,教练就把我的皮夹打开,抽出几张钞票,放在我的脚和马肚中间。教练要我用脚夹住这两张钞票,如果钞票掉下来,就归 他了。这一招还真灵,我拼命夹住了马肚皮,后来就真的学会了。”这一个细节我将它写进了文字,编辑们说我怎么想得出的 ,我说这不是我想出来的。真是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李先生当年是现在所说的电台节目主持人。他就读于著名的华同公学,也就是现在的晋元中学,整个学校是“和尚学 校”(男子学校,该校毕业后可以直升圣约翰大学三年级)。这所学校在毕业前有个传统BALL(毕业盛会),参加盛会的 有校董,社会名流,各大企业的高层等。大企业往往在盛会上趁机考察学生们的行为举止,然后招募自己中意的员工。李先生 人活泼,是盛会的主持人,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结果他就被当时的加拿大驻上海的电台相中,做电台英语播音员,每天晚上8 点到12点,主持一档向西侨和洋派上海人介绍最流行的好莱坞流行歌曲的节目。 李先生主持栏目时,每天晚上12点有个女孩子会打电话进来,要点《玫瑰人生》。有一天,老板跟他说明天有几个 人来参观,那个打电话来点歌的女孩子也会来。他非常担心,心里想,要是人家女孩子长得漂亮也就算了,如果很难看,自己 不愿跟她交往,会很伤女孩子自尊心。历史无论如何变化,主题是一样的,这种心理状态我们现在也有,像网友见面。新上海 ,老上海,人的七情六欲都是一样的。最后,他看见那个女孩很漂亮,才心定了,但又咯噔一下产生新的担心,因为那个女孩 高他半个头,还大他5岁。但他们还是恋爱了。 李太太(当年还是小姐)说要学开飞机,李先生就去打前阵,到飞行社去考察。一看啊,40个学员有38个都是很 帅气的男孩子,余下两个就是自己的恋人和一个姓杨的女士。杨女士即杨瑾豫,中国最早的女飞行员,抗日战争中与日本人血 战长空,在作战中牺牲。而李太太拿到飞行执照,就回家做太太了。飞行社大多数教官都是外国人,在一个英武男性为主的群 体,李先生担心自己恋人花落人家。当时是在大场飞机场上学,李先生每天早上5点送恋人到机场,他就是要告诉其他人,她 已经名花有主了。这样李太太也很开心,觉得他很体贴。 李先生对我说:“别看她比我大5岁,在日常生活中比我小15岁都不止,她不懂事。”可见李先生心智非常成熟。 他还说:“我太太这个脑子很新的,你们谁的脑子都没她的新。”我说:“是的啊,1936年的女孩子已经想到去学开飞机 了,她的脑子不新谁新啊?”没想到他说:“不是的,她嫁给我之后,她脑子一动也没动过,脑子没用过,所以是崭新的。” 这种幽默,我真是服了他了。所谓的绅士并不是穿西装,戴领带,而是一种品行,修养,绝不是靠外貌包装的。 其实,在这对老夫妇恩爱的背后,有非常悲惨的故事。真正大都会的品行表现为很大气,不会被生活打倒。他们的婚 姻很幸福,结婚66年也“吵”了66年,老先生认为好的夫妻就是要“吵架”,“吵架”其实也是一种沟通。他们的两个儿 子都很优秀,大儿子毕业于第一医学院,小儿子是外语学院毕业的,今年也要63岁了。但是大儿子29岁时于“文革”中自 杀。他是广慈医院的医生,我说过自杀也是能体现文化和修养的,他跑到心电图室,将心电图仪器套在身上,电源一开,“啪 ”就走了,走得干净潇洒。当时社会很乱,李太太要李先生答应她一件事——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一定不能自杀。李先生答 应了她。之后不久,李先生就被抓进牢,关了6年。李太太以前不工作,被抄家后,她只有靠替人家做保姆来维持生活。她说 :“学开飞机,不是说我学会了开飞机,而是开过飞机的人,眼界、胸襟会变得很广。无论怎么苦,我心里很笃定,因为我知 道他不会自杀的。”等到李先生被放出来,打电话听见太太“喂”的一声,发现对方不是很激动,有的只是:“我知道你会没 事的。”这真的是老上海的典范。 现在他们每天早晨吃面包和牛奶,中午吃自制的三明治,只有晚上像模像样地到饭店吃一顿。他们说饭店也是一个社 会,里面的景象真好看。老先生现在还在一家外资企业担任高级顾问,一周上三个半天的班,这个公司发到国外的商务信件都 要经由老先生之手。 “文革”后落实政策,分给他们一套在浦东两室一厅的房子,但他们用这个换了重庆南路上的一间房,因为他们结婚 起就住在这里,已经有66年了,他们看惯了这里的梧桐树。 今年的年初一,我打电话给二老拜年,没人接电话,我想大概是他儿子接走了,可一直到初七,初八,他们家里也没 人。我急了,马上到他们常去的那间饭店,经理说:“有一次,老先生在我们店门口晕过去了,现在住在医院里。不过老先生 关照过了,叫我们不要去看他,他说过了这关,我们就还在饭店见,但是现在不要见面,因为他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他不要人 家看到这个形象。”在此,我要说,上海先生不是乔治·阿玛尼的西装穿好,星巴克里喝喝咖啡,这样的上海先生也太容易了 。要想锤炼成一个真正的上海先生,就要像李先生一样,经历过很多磨难,荣辱不惊,这样才是一个男人。 后来,李先生的电话来了,他说他已经到家了。我们马上见面,他说他在医院里20天高烧不退,是由于急性肺炎引 起的。我问李太太:“李先生进医院,你心里担心吗?”她说:“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知道他会没事的,因为他答应过我,将 来一定要我走在他的前面。”李先生也对我说:“是的,我答应过她的,‘我一定走在你的后面,把你的事情办完了,我再来 找你。’”李先生在医院发烧的时候,不断地问别人今天是几号,因为他心里想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无论如何也要陪老太太 去外面吃饭。这一对老夫妇我是真的喜欢他们,他虽然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什么英雄,但是他这样的素质,着 实令人打心里感动。 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它的故事是永远也讲不完的。人是建筑的灵魂,通过人和时空的对话,使建筑本身有一种灵气 。这样的建筑,这样的人,放在一起,一定是上海所独有的。李先生这样的海派,很乐观,很幽默,这全部都是上海水土所孕 育的。 新民周刊:为了这些老上海人,你就不写小说了么? 程乃珊:不是不写,而是往后挪一挪。现在我的手头有个长长的名单,都是一些老上海的见证人,他们的年纪都已经 很大了,我等不及了,我要趁他们脑子还清楚的时候,把他们叙述的故事记录下来。比如我找到了将“coca-cola” 译成“可口可乐”这个音义译都结合得很好的人。我所做的不是要怀旧,不要一提到老上海,就认为是喝喝咖啡还有旗袍。今 天的上海,处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时期,而老上海的许多东西是值得借鉴的。 新民周刊:可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卷入了“全球化”进程中,城市变化巨大,文化多样性日益受到挑战, 公众对本土文化的固有信念本已产生了动摇,你会担心自己现在所做的工作会背离自己的本意,仅仅成为人们消遣的东西吗? 程乃珊:我觉得不会。我们是需要一点声音,希望能有更多的上海人来关心老上海的历史。以前是要求全国化,话要 讲一样的,现在好不容易可以有个性了,又一下子要卷入范围更大的全球化,这其实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一直都赞成在推广普 通话的同时也要提倡讲沪语。一个城市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如果让人分辨不出,就很悲哀了。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民周刊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