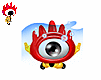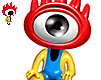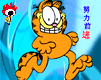| 上帝保佑赚钱的摇滚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8月25日14:41 外滩画报 | |||||||||
|
摇滚和商业的“媾和”早就不是秘密,黄燎原甚至大赞:商业是伟大的!他说,只有和商业结合,摇滚才可能“主流 ” 外滩记者海岚何玉卿(实习生)/报道 8月6日, “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摇滚音乐会在银川贺兰山下开始第一夜的疯狂;
从银川到上海,西北的荒漠沙丘与东部最繁华的都市海滩边,不管是为了纪念回顾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还是为了力 图展现多元化的国际视野,有一点是一致的,乐坛的多元趋势在这一年将中国摇滚的主流化进程突然彰显并推至台前。 伍德斯托克情结 当王磊在台上大声叫喊:“来吧,摇滚需要身体的接触。”乐迷们开始冲破武警的警戒线涌到舞台面前。的确,王磊 煽动的语言给摇滚演出带来了气氛,音乐会现场需要互动的情绪,这是现场表演的魅力,流行音乐如此,更何况摇滚。 每年一次的迷笛音乐节是摇滚青年们的节日,北京香山下的迷笛音乐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摇滚新生力量。主办方 虽然没有强大的经费支持,但是将“迷笛”变成中国摇滚音乐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是他们一直努力的 方向。2002年,在丽江盛大举行的雪山音乐节也一度成为人们心中的中国“伍德斯托克”。而这一次贺兰山下的3场5小 时的连续狂欢,不仅是主办方的宣传,甚至几乎所有媒体一致称其为中国的“伍德斯托克”。“风·夏音乐季”的主办方也打 出woodstock风格的summershake旗号。 “伍德斯托克”对于中国音乐人来说是一个内心的梦想和希望,就像奥斯卡之于中国电影人,诺贝尔文学奖之于中国 作家。中国摇滚艰难发展的20年,恶劣的生存环境,再加之本身的不成熟,在中国做一个“伍德斯托克”几乎就是个白日梦 ,那是一个集合了知识分子、摇滚文艺青年、嬉皮士们对自由、纵情的幻想,与一种现代主义的人文情结。读了《光荣与梦想 》、《伊甸园之门》成长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先锋文化精神使其内心对摇滚的认同成为一种本能。虽然他们不可能亲历那次 45万人的狂欢派对,但可能读金斯堡的诗,哼鲍伯·迪伦的曲子,看安迪·沃霍尔的画,或许还推崇维维安的服饰。面对当 年特殊的文化背景与社会格局,不难理解崔健一曲《一无所有》唱响全国,《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菊花古剑》、《姐姐》 、《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一系列的摇滚歌曲迅速聚集了大量的歌迷。今天,这些曾经共鸣过第一、二代摇滚音乐人作品的 人,可能是艺术家、商人、公务员、传媒人、策划人。他们可能已经不再听摇滚,但是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支持摇滚。 上帝保佑赚钱的摇滚 2004年的贺兰山“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也许将成为中国摇滚的新起点,摇滚演出终于可以不赔钱了。上帝保佑 赚钱的摇滚,至少100万的盈利让这次演出成为中国摇滚史上第一次获得商业成功的摇滚节。 本次摇滚节是银川摩托车旅游节的一个项目,背后的投资人是宁夏民生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陈嘉,除去摩托车比赛、 摇滚音乐节,他还在活动场地艾克斯星谷搞了个惊人的项目:贺兰山房,邀请12位当代艺术家设计修建了12栋风格怪异的 房子。三个项目总投资3000万人民币,其中摇滚节200万。鉴于摇滚演出几无大获商业成功的先例,投资方并不寄希望 在这上面赚钱,只是通过演出来达到炒作地产的目的。 最开始摇滚节的策划人黄燎原想做一个“百团大战”,集合100支新锐摇滚乐队做演出,这个方案被投资人陈嘉否 定了,理由很简单,陈嘉认为那些不出名的新生乐队并不为银川人熟知。事实证明了陈嘉的判断,很多银川人是冲着唐朝、崔 健、张楚来的,选择的18支乐队都具有不小号召力,这是成功的关键。三天总共有12万人次观众,一张联票380元,而 只需要1万人次就不赔钱了。 伍德斯托克节花费240万美元,投资人几近破产,雪山音乐节亏了近100万元人民币。黄燎原说成功的摇滚演出 很少,投资方冒了很大的风险,这一次的成功最重要是策划好,开始探索出一个良性的模式,让更多的投资人有信心投资摇滚 演出。 商业和摇滚结合早就不是秘密,黄燎原甚至大赞“商业是伟大的”,他说:“只有和商业结合,摇滚才能主流,才能 打破目前这种唱片公司不签摇滚歌手、评奖不带摇滚乐玩的现状。”罗琦说“从贺兰山开始将摇滚商业化,浮出海面”是一次 难得的10多年朋友的大派对,“我是第一次见识这么大型的,尤其是我在德国生活回来之后,我看到歌迷那样有热情,非常 有信心。”相信任何一个乐手在看到现场那些激动的歌迷、听到大数目的盈利的消息都会振奋,内心都会充满希望,更何况是 多年萧条的摇滚。 后摇滚时代的“嘉年华” 去年SARS让滚石的中国行成为遗憾。当演出批文下来发布滚石演出消息时,中国的摇滚歌迷的确快疯掉了,而“ 摇滚”这个多年来一直在中国是个禁忌的演出市场也慢慢地被松动撬开。而且我们可以看到雪山音乐节、贺兰山摇滚节、金山 风·夏音乐季都是由政府出面牵头主办的项目,官方的支持必然给摇滚的生存创造一个新的土壤。 在贺兰山摇滚节消息发布以后,业界反应不一,令人振奋又令人失望,振奋的是这是中国摇滚乐坛20年来的一次总 结,除却窦唯遗憾缺席,当年叱咤摇滚乐坛的重量级乐队几乎全部亮相,包括退出多年的何勇、张楚。中国摇滚乐需要一次这 样的演出,但是一直无人来操作,其状况用本次音乐节策划人黄燎原的话来说就是只能在艺术上具有学术价值。特别是在摇滚 沉寂多年后,集体亮相是一种暗藏深久的能量的暴发,对中国摇滚也是一种激活的方式。而失望的人们则称:“这不过是一次 腐朽势力的登场。”对此不抱好评的部分摇滚音乐人将矛盾的焦点指向“这些都是很流行化的主流摇滚,没有新意”,更击中 要害的是直指这当中大部分乐队已经没有很好的创作力量。的确三天的演出,尽管让乐迷们听到了那些熟悉的经典,但是这些 曾经辉煌的乐队新歌却少有人回应。 中国没有摇滚,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但摇滚是个舶来品却是不争的事实。不是自家的家伙当然不好使,中国摇滚在 夹缝中生存,很多摇滚人所秉承的“摇滚精神”已经变异,乐评人孙孟晋说:“一场音乐节救不了中国摇滚。”崔健则指出, 中国之所以没有像国外那样有着长久生命力的摇滚乐队是因为很多乐手被物化了。 “伍德斯托克”以反主流文化成为一种文化标志,直到1994年百事公司举办的名为“重聚伍德斯托克”的商业演 出。在数年间,“伍德斯托克”的周年纪念日无人庆祝,无数嬉皮士朋克们已经随着时代变化成长为主流精英。摇滚在国外已 经是一种主流音乐,国际流行乐坛的多元化使各种音乐元素相互融合,尤其是电子音乐的出现,不同音乐的界限已经被打破。 “后摇滚时代”的来临,让摇滚乐从地下走到地上。 和西方摇滚音乐历程相比,20年中国摇滚还是幼稚的,崔健说:中国摇滚才刚刚开始。那么,中国所需要的摇滚精 神是什么?是继续愤青,还是另有出口?相信被物化的不仅是中国摇滚,另类也许就是未来的主流,中国摇滚在向主流文化攀 爬(或者说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的过程肯定是必然趋势。就像一直立志于发现推广中国原创音乐的Channel[V], 其创立的华语榜中榜确实推动了中国原创音乐的发展,作为“风·夏音乐季”的主办方,将多种面貌的音乐呈献给歌迷是他们 的宗旨,于是我们能看到一个盛大的音乐嘉年华,有亚洲一线流行歌手,也有类似子曰、二手玫瑰、声音玩具这样的摇滚乐队 。 黄燎原说:“我们必须商业才会有更大的传播。摇滚一定会成为主流,但主流化是需要时间的。一次成功是无法改变 它的生存状态的。它需要的是有人推进。不过这一次的成功是我们迈出的坚实的一步,让我们有信心继续做下去。” 黄燎原的苦心也得到了众多乐手的响应,尽管他们也同样尊敬做纯粹摇滚的。久居德国的罗琦以为:“摇滚的主流化 是一个必然的规律。20多年来,早期的国情不够开放,就造成了很多地下的。开放后自然也就主流起来。其实音乐只要好听 ,必然就有人喜欢。没有必要非要定位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商业化是必须的,以商养艺是必需的,否则难以达到主流。但需要 慢慢来,希望已经看到。就像这次,让我想起10年前,看到新的希望,让我觉得我们不是被遗忘的一群。” 该不该为中国话剧分代 本报上期发表《玩话剧的“第五代”》文后,一些读者给本报来信,就“中国话剧分代”表达了不同的观点。现从中 选登崔文嵚先生的文章。 崔文嵚/(北京大学话剧社社长中国国家话剧院观众俱乐部理事) 戏曲是表演者的艺术,电影是导演者的艺术,而话剧可能是更偏向作者的艺术。那么为什么不把剧作家作为分代的标 志呢?而这样,又和文学史的划分有什么区别呢? 日前看到了8月19日《外滩画报》上关于为中国话剧人“分代”的报道,有一些想法,便写了此文,一家之言,请 大方之家指正。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观众开始走进剧场观赏话剧,话剧市场一直非常红火,几乎每年都会涌现出不少新人新作。基于 这种现象,有人提出应为话剧创作者分代(见8月19日《外滩画报》文化版相关报道)。“分代”在电影领域早已不是什么 新名词,每个热心的观众都能举出一连串响当当的名字,但对于话剧观众,甚至是专家,“分代”还是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概念 。 先不说这“代”怎么个分法,“分代说”本身就已经引起不少人的质疑。“大导”林兆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支 持“分代说”。当然也有不少专家赞成这种说法,认为“分代”是对中国当代话剧史的一次很好的总结。 既然“分代说”是受了电影的影响,那么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电影界的情况。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电影与话剧的区别 在于,电影对技术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要拍电影除了要懂得文学、表演以外,还必须了解镜头、光线、构图、剪辑、特技效 果等比较专业的知识,当然也需要一定的资金基础。而话剧不然,话剧艺术的核心要素只是演员、观众和观演关系。其他的一 切,如文本、音乐、服装、化妆,甚至包括舞台、剧场都是可有可无的。只要有一个空间,有演员的表演和观众的观看,话剧 就可以成立。这一点电影永远做不到,因此话剧的参与性更大。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电影导演都必须经过电影学院等专业院 校的训练,很难“自学成才”。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年级毕业的导演在风格、视角上必然有某些共同的因素,将他们划分为 一代,一方面在电影史的描述上非常方便,另一方面也容易发现归纳他们的相似点与共性。 很难用电影的“分代说”来套话剧。现在最为活跃的话剧创作者中,一批是国家话剧院、北京人艺、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等国家级演出团体的专职导演,另一批是许多年轻的业余爱好者,即所谓的“新人”。这些“新人”很大一部分都是半路出 家,如邵泽辉、顾雷、黄盈等人,他们在大学所学的专业大多与话剧无关。他们都是在经过彷徨之后坚持了自己的理想才走上 话剧道路的。还有一些年轻导演干脆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战略,根本没有进过专业院校,如石可、张广天等人(他们是否应 该被称为“编外”导演呢)。其他的“新人”们恐怕有的只是“昙花一现”。 另外,是否应以导演作为话剧界分代的标志呢?当我们提到戏曲时会说,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谭鑫培的《定军山 》,常香玉的《花木兰》;提到电影时会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陈凯歌的《荆柯刺秦王》;而提到话剧时会说,老舍 的《茶馆》,曹禺的《日出》……可见戏曲是表演者的艺术,电影是导演者的艺术,而话剧可能是更偏向作者的艺术。那么为 什么不把剧作家作为分代的标志呢?而这样,又和文学史的划分有什么区别呢? 曾经有人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话剧史划分过发展阶段,如从“五四”到“抗战”为引进、生成阶段;从“抗战”到“建 国”为探索发展阶段;从“建国”到“文革”为服务政治阶段;“文革”为停滞时期;“改革开放”后为实验创新阶段……我 认为,这种分法实际上已经暗含了为话剧创作者分代的意思,并且非常明确地以时间作为划分标准。当然这种标准在今天看来 有不小的问题,毕竟艺术的发展与历史、政治的发展并非永远同步(艺术史上经常出现艺术与历史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不能否认给话剧创作者分代在理论研究上有一定的意义,但如何划分,以什么标准划分,还有待理论界进一步商榷。 我认为可以先不急于给出清晰的结论。 相关专题:外滩画报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外滩画报专题 > 正文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