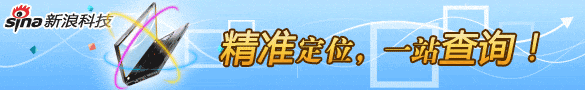马寅初被批始末
 政协筹备会常委合影, 第二排左二为马寅初
政协筹备会常委合影, 第二排左二为马寅初
 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发言
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发言
马寅初被批始末
本刊记者 徐梅 整理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解决人口问题,靠节育还是靠革命,变成了一个政治立场的选择
自1957年10月开始,费孝通、陈达、吴景超等大批研究人口问题的社会学家和人口学家陆续遭到批判,《人民日报》一篇评论文章称“这些资产阶级右派们”谈的并不是什么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战斗,必须彻底地打垮他们,揭露他们的阴谋,粉碎他们的诡计”。
1958年4月,马寅初也被公开点名批判。对他和《新人口论》的批判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以至于后人一提到马寅初,首先想到的就是“计划生育”、“人口控制”、“中国的马尔萨斯”这些关键词。
马寅初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学,“团团转”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提出的主要经济理论,在对他长达3年的批判和理论围攻中,“团团转”理论被斥责为“唯心主义的错误”,“严重歪曲了计划经济内容”,而“新人口论”的观点则被上升到“政治立场反动”、“仇视人民群众”的高度,批判文章里对马寅初及其人口观点的政治定性——“帝国主义分子”、“反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等字眼令人心惊。
一个学术问题为何会演变成政治问题?1957年春夏原本赞同人口“计划生产”的毛泽东为何突然改变立场,将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人口学者推向政治祭坛?
靠革命,还是靠节育?
“马寅初先生一再强调人口问题是个学术问题,他要捍卫学术的尊严。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的人口思想都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对人口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不违背政治原则的时候,这种思考可以存在,一旦触及敏感领域,就会带来麻烦。”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正武教授曾参与编写《人口学百年》一书,详细梳理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思想的演变。
“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人口众多,则赋税自广”,中国自古以来推崇人口增殖。
“人满之患,深可太息”的观念直到清朝末年方才出现。面对国弱民穷的社会现状,晚清历史地理学家汪士铎在《乙丙日记》中曾提出“以刀兵消息之”的极端人口控制主张,提出施行严刑峻法,斩杀人口;提倡溺杀女婴,穷人不可生女,富人只准生一女,对男孩数量也要予以限制,“不可过二子,三子即溺之”;鼓励出家,并规定“天下之贫者,以力相尚者,不才者”不准娶妻;助长灾疫,借机减民。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恰在彼时传入中国,他的主要论点为: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也即人口增长总会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这正是贫困、罪恶、饥荒时常发生,人类很难得到幸福的根源。
梁启超、严复等改良派知识分子都深以为然。梁启超在《禁早婚议》中写道,“中国民数,所以独冠于世界者,曰早婚之赐;中国民力,所以独弱于世界者,曰早婚之报。”严复也赞成改变早婚和盲目生育的陋习,提高人口素质,“民愈愚则昏(婚)嫁以无节”,“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造成贫穷和失业的原因不是人口增加,而是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人口思想也传播开来。
新中国成立后,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观点被斥为“为资产阶级作辩护”、“反动透顶”,而马克思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决人口问题的人口观则被视为革命、正统。
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靠革命,还是靠节育,不再是一个学术选择,而是一个政治立场选择。
这也为马寅初被批判时康生那句著名的质问:“你是哪家的马?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埋下了伏笔。
斯大林:人多是个好现象
“人口不断迅速增加,人民物质福利水平很高,患病率和死亡率很低,同时有劳动能力的人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的实质。”按照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阐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已经失去效力”。
1935年12月,斯大林说,苏联每年净增人口约三百万,“这是好现象,我们欢迎它。”到1950年代,有38000多名生育并抚养了10个以上子女的妈妈被授予“母亲英雄”的称号。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1953年出版了波波夫的《现代马尔萨斯学说是帝国主义仇视人类的思想》一书,书中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推演到极致,“人口无论怎样增殖,增添出来的人口无论怎样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增长着的生产中是永远可以为自己找到工作岗位的。”
“老大哥”的人口政策自然影响到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马尔萨斯”成为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社会学系被取消,人口学课程和研究自然也被封杀了。
毛泽东在建国之初的人口主张成为社会主义人口观的绝对经典,“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的社论。同年12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次年1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避孕药和避孕用具进口。
党是赞成节育的
1953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表了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普查结果是全国人口总数为六亿多,人口增长率高达千分之二十。
当天的报纸配发了一篇题为《六万万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的评论文章,除了回顾历史、继续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之外,文章中有一句话耐人寻味,“我们承认在一个经济不发展的国家,人口迅速增长是有可能造成生活上的某些困难的”。
而在此之前,邓颖超和邵力子就曾率先逆流发声,倡导避孕节育。1954年5月27日,邓颖超给邓小平写信,主张在机关中的多子女母亲或已婚干部中推行有指导的避孕,翌日邓小平便给她回了信,表示赞同她的主张,“我认为避孕是完全必要和有益的,应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当年9月的全国人代会第一次会议上,邵力子在发言中呼吁控制人口,“人多是喜事,但在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似乎也应有些限度”。次年,他在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加强避孕宣传、放宽对人工流产的限制。此后,他还自己编印《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小册子,称“避孕和流产是市民的权利”。
与此同时,马寅初通过对家乡人口增长的3年实地调研,收集了大量实证资料,为他日后的人口政策建议作了充分、扎实的准备。
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第一次人口与计划生育座谈会,他在讲话中说,“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
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组的报告,并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批示》,文件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我们的党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
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这一认识在党的八大有关决议中得到体现,“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的人口政策第一次被纳入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人口问题时说:“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少数民族地区不要去推广,人少的地方也不要去推广。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进行试点,逐步推广,逐步达到普遍计划生育。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人类在生育上头完全是无政府状态,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没有一个社会力量,不是大家同意,不是大家一起来做,那是不行的。”
马寅初1955年就在人代会浙江组就人口控制问题作了发言,但当时赞成他的人很少,有的代表说,“苏联都不讨论人口问题,我们也根本没有必要讨论这些。”马寅初感觉时机不到,主动把发言稿收回了。
人口问题和计划生育的主张写入党和国家的有关文件以及毛泽东的表态,使得包括他在内的学者放开了胆量,马寅初欣喜万状,“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见所闻远比我广,得出的结论一定更正确,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当年4月,他亲自张贴告示,在北大饭厅为上千名师生作了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演讲,“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1957年他在人代会上作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核心主张是“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普遍推行避孕,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通过人口控制,降低消费,增加积累,扩大生产”。这个发言后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当年8月,经教育部批准,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的人口学研究机构——人口研究室。这期间有大量学者公开发表了赞同控制人口的理论文章。
这是哪家的马?
正当人口学者们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们齐声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之春唱和时,作为政治风向标的《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全国人民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
1957年 8月31日,社科院哲学社科部开始批判费孝通、吴景超等“资产阶级”社会学家。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已经在党内形成决议的人口控制思想被彻底推翻,节育问题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诡计和阴谋。
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名批评了马寅初,说:“马老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
当年6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最高领袖关于人口问题的最新阐释:“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最高指示一出,人口问题之争彻底变为阶级路线之争。
7月1日康生给北大师生作报告时质问,“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此后两年的政治讨伐中,马寅初“单枪匹马出来应战”,他毫不客气地说那些针对他和《新人口论》的两百多篇批评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以经常学习”。
他坚称人口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他谢绝了周恩来等人“认个错,低一下头”的好意,“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
万马齐喑的1960年,他在《新建设》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
康生指示北京大学时任领导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之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他门上去。我们不发动,群众贴他是右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
在他的鼓动和指示下,全国报刊又一次掀起围攻马寅初的高潮。这两场大批判在理论上摧毁了人口学界对我国人口问题的探索。由于错过了解决人口问题的大好时机,最终如同马寅初先生当年预言的那样,人口过多一度成为了我们的致命伤。
自1980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这一生育政策造成的“421”家庭模式,以及生育率不断走低,低生育率的负面效应凸显,使得今天的人口学者分为“主收”、“主放”两大阵营。然而无论是哪一方,都对马寅初先生葆有崇高的敬意。
- 闂佽崵濮崇拋鏌ュ棘娓氣偓閸┾偓妞ゆ帊鑳堕惌搴b偓瑙勬礀缁绘ê顕f禒瀣濠㈣泛妫楁禍鐐節闂堟稒鎼愰柤鐢垫嚀閳藉骞樼紒妯绘闂侀€炲苯澧紒顔肩箰閻g柉绠涘☉妯哄敤闂佺ǹ绻愰ˇ顐﹀磻閹炬枼鏀介柛銉e妿閸樻劕鈹戦悙瀛樺剹濞存粣绲介悾鐤疀濞戞ê鍞ㄩ梺鑽ゅ枔婢ф宕愰幎鑺ョ厱婵°倕顑嗙€氾拷
- 缂傚倷绶¢崰妤呭磿閹惰棄纾介柛顭戝亝婵挳鏌eΟ铏逛粵闁伙綁浜堕弻鐔兼濞戝崬鍓卞┑鐘欌偓閸嬫捇姊哄Ч鍥х伄闁哥姵鍔曢—鍐晸閿燂拷 濠电偞鍨堕幐鍝ヨ姳閼测晜顫曟い鎺嶈兌閳绘梻鈧箍鍎遍幊蹇涘磹闁秵鐓熼柕濞垮劚椤忣偊鏌℃担瑙勫碍閻撱倝鏌ㄩ悤鍌涘
- 闂佺澹堥幓顏嗙不閹烘顥婇柍鍝勫暞婵ジ鏌熺憴鍕Е闁告埃鍋� 濠电偛鐡ㄧ划鐘诲磻閸曨喓浜归柛顐線閻掑﹤鈹戦悩鍙夊櫣闁诡垽鎷� 闂備礁鎲¢悷顖涚濠婂牊鍎撴俊顖濆吹椤╂煡骞栫€涙ḿ绠樼紒瀣灴閺岋綁濡搁妷銉紓婵犮垼顫夐幑鍥ь嚕閻㈠壊鏁嶆繝濠傞婵即姊洪崨濠勫暡闁瑰嚖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