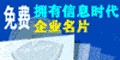| 记者探访城市救助站生活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9月30日04:05 重庆经济报 | |
|
-本报见习记者 李良军/文 今年8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取代了实行21 “新人”报道 “这个床位没有人睡,你就睡在这儿吧”。9月22日晚7点30分,江北蚂蝗梁重庆救助管理站的一位工作人员指着一张单人床告诉记者。 这个救助站的前身是重庆城市乞讨人员收容站。8月1日,“收容站”改为“城市救助管理站”后,这个地方就成了自愿接受救助者的暂时住处。记者有生以来首次走进这样的房间:筒子房,每间四个床铺。 和真正的被救助对象一样,记者进入救助站“体验”之前被明确告知,必须得按正规程序进行,即按照《救助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被救助”手续。 “填表时一定要注明是自愿被救助,否则,站里是不能救助的,这是规定。”救助管理站彭副站长特别告诉记者,进“站”程序如下:门卫室的工作人员将我带到了救助管理站男性管理办公室,拿着填写的救助手续进行入站时间登记。从入站到办理完手续,记者前后仅用了十分钟时间。但作为真正的被救助对象,不仅要向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讲清楚为什么到救助管理站的原因,还要提供家庭联系电话及被救助人员政府所在地的具体地址等等,至少得花半个小时的时间。 该救助站共有上下两层16间房,男女分开。我“下榻”的在楼下男性管理室,门前有号牌:第3室。我打量了一下室内,四床崭新的单人床横排着,除10号上的被褥堆放较为整齐外,其它三张床的床上用具散乱地堆放着,一件上衣吊在床沿边。地板铺的是地面砖,因为有水渍,地面上散落着零乱的脚印。床的对面是三张木桌,上面歪歪斜斜地放着洗涮用具。 见有“新人”进来,第3室里正躺在床上的3个人一下子坐起身来,用疑惑的眼光上下打量着我,看样子他们不怎么相信我是一个“被救助者”。由于事前我与站里达成了不能透露记者身份的默契,那位领我进来的工作人员也就不多说,留下一句“需要什么找我”的话就转身出去工作人员,我孤零零地被留在三个陌生人中间。 刚在床沿上坐下,一个带着乐山口音的中年人凑了过来:“噫,眼镜,你是啥子原因进来的呢?”我放下刚领取的生活用具及洗涮用品,“来重庆出差,身上的钱物被偷了,回不了家,所以来此救助”。 我的到来没有给这个地方的住客增加很多谈资和好奇,当室内的人确信我是“被救助对象”后,也许由于戒备心理,他们又各自去想自己的心事去了。 哭泣的小孩 隔壁5室住的是刚刚进来的3个未成年人。当记者走进去时,看见两个小孩正在下象棋,战事正酣。不一会儿,就听见一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对一个又黑又瘦的小孩说道:“将,你的老王死了,没救了。”黑瘦小孩子一脸无奈:“你又蠃了,我认输。”记者注意到,室内的3个孩子都没有成年,天真与童稚毫无保留地刻划在他们的脸上。 13岁的胡林不会下象棋,便一个人坐在床上看卡通画。常言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见记者进来,他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便要求记者陪他下军旗。于是,我俩都盘腿坐在床上,拼杀了起来。记者注意到,这个尚差几天才14岁的少年,脸上却缺乏正常少年的红润,满身的疲惫都写在了脸上,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大号灰色衬衣罩在他的身上,使他显得更加单薄。记者一边下棋,一边与胡林摆起来了龙门阵。 胡林的叙述断断续续,他想表达什么却又总是不得要领,大意是“我长这么大,妈妈是谁我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听伯伯讲,妈妈16岁时就把我生了下来,她与爸爸生活了3年之后,就被人贩子卖到外地了。就在妈妈被拐卖的那年,爸爸困为犯罪被判了刑,后来,我就跟着伯伯、伯妈、爷爷和奶奶过。去年初,伯伯、伯妈外出打工了,家里就留下爷爷、奶奶和我。他们又老又有病,没有收入,今年我们三个人的口粮还是队里给解决的”。 胡林说家里实在太困难了,自己又没有能力挣钱,9月2日,他偷偷从家里拿了30元钱,从两路镇赶车到城里来找他的一个叔叔,想从叔叔那里拿点钱回家用。但到了城里,他知道叔叔在弹子石,但具体在哪个地方他并不知道。找了几天,连叔叔的影子也没见到,身上的钱也花光了。 9月7日那天下午,胡林一个人徘徊在菜园坝广场,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实在走不动,就在菜园坝广场坐了下来一直到天黑。胡林说在那里他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伯伯给他送了好多好吃的。晚上9点多的时候,他被冷醒了,他弄不清东南西北,最后,求助在广场上巡逻的警察叔叔,“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求他帮忙,他把我送到观音桥派出所,吃了一顿饱饭。第二天,我被送到了救助站。” 胡林同很多被救助的人一样,“刚来的时候,想家想得厉害就哭,站里的叔叔常常来安慰我,叫我不要着急,他们正在与我家里联系,很快就会送我回去。” 飘零人的梦 记者与胡林下了4局军旗后,百无聊赖只好到管理室找管理人员聊天。 “这些被救助者,他们能自由出入吗?”记者问。 “当然可以,自收容遣送站改为救助管理站后,每天进出站的被救助者一般都在4至5人左右,最多的一天就有7个。只要他们提出不愿再接受救助,填张终止接受救助表就可以走了。而以前还是收容遣送站的时候,因为带有一种强制性的手段,他们的自由是有限制性的,什么时候离站,不是他们说了算,而是由收容遣送站来决定。另外,现在进入救助管理站的被救助人员携带的东西,不能随便检查,而收容遣送站时他们所带的东西一律得进行检查并暂扣起来,待他们离站时才发还给他们”。一位曾在收容遣送站工作过多年的工作人员作了这样的对比。“在人格上、人权上,被救助者与管理人员是平等的,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是救助与被救助的关系。”另一位工作人员插话道。 正聊着,住在2室的白志艺(音)走进了管理室,找到管理人员说要看电视。管理人员二话没说,带着他直接去了会议室,打开了54英寸的背投彩电。随后,又有好几个被救助者进去了,他们就在那里静静地看电视,打发时光。 回到3室,夜已经很深了,窗外的万家灯火温暖着无数家庭。中秋节过了就到国庆节了,在外漂流的人们也许正往家奔呢,同室那位乐山人,熟睡时嘴角挂着微笑,也许他在梦中梦见了自己的亲人…… (文中未成年人用化名)本版图片均由记者熊明 | |
| 首页 ● 新闻 ● 体育 ● 娱乐 ● 游戏 ● 邮箱 ● 搜索 ● 短信 ● 聊天 ● 天气 ● 答疑 ● 导航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孙志刚事件终结收容遣送历史专题 > 正文 |
|
| |||||||||||||||||||||||||||||||||||||||||||||||||||||||||||||||||||||||||||||||
| |||||||||||||||||||||||||||||||||||||||||||
|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3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