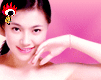新周刊封面:倾听时代最真诚的声音-我反对!(7)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15日15:52 新周刊 | ||||||||
|
刘长寿 谁能容忍城建中的低级错误 文/郭娜 图/文英 国际大都市上海为什么不应该建国际水准的大桥?66岁的刘长寿戴上助听器,摘下老花镜,面一字排开4大本“进言记录”共358页,从1990年说起。 北平、奉天长大的刘长寿很不上海。在上海这个“不反对”的城市,他捏住了“造大桥”这个大事。14年来分主题(不限于造桥)7次上书上海市市长和有关部门。母亲说他从小方脑袋,认死理。1990年,国内第一、世界第三的南浦大桥动工,刘长寿第一次上书反对;创10项世界纪录的卢浦大桥再次动工,刘长寿再次上书反对。面对着南浦、杨浦、卢浦三座振奋了上海后来居上的市民雄心、宣告了长三角把珠三角抛在身后的“宣言型”建筑,刘长寿就是不依不饶:“这是低级错误,捏住,跑不了。” 刘长寿就是有这个自信,同济数学力学系毕业,他比别人更精于计算和受力分析。不过依他看,“这个问题比较初级”。“自己也解决不了的事我不提,我能提出对策的才说。” 理由很简单:造高桥是“打肿脚穿大鞋”,“上海是人口高度密集的国际大都市,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最拥挤的空间”,根据“这个密度、黄浦江的河道状况、上海市的市龄、国外同类大桥的具体情况……”,“三座大桥”是得不偿失的浪费,影响上海发展的间接损失不可估量。 他反复发问:“为什么一定要建大桥?”为了进巨轮吗?”他再发问:“一年能有多少艘次?”他提出:“南浦大桥动迁5000户居民和180多个单位值得吗?”为什么不可以“造小桥并调整港区,腾出大块土地建一座滨江森林花园”。 “我们为什么偏爱黄浦江闹市区段的港区呢?”更主要的原因是“港区原来就造在那儿”。但是要知道,“这些码头兴建之初,浦西江岸正是城市外边缘,而现在城市外缘在长江南岸、在东海之滨……” 刘长寿反复强调:“我想再重复一下,一切均要量国力而行,但应强调规划意识。” 然而,尽管他一再奋笔疾书,每一页都用严整而隽秀的硬笔书法一字不改地誊清,每一封信的复印件上还有红笔校对的记号,每一本记录的目录上都用红笔圈出重要的页码,但是,他依然还是那个奋笔疾书的刘长寿,桥也依然造得那么高。没有什么人明白他究竟“图什么”,唯独一位圣约翰大学出身、老地下工作者的规划局老局长说过:“他这是动态的休息,活他的生命价值。” 对于得过两次癌症(1999年得淋巴癌,2002年得肝癌)的刘长寿,他开玩笑说:“飞机误点,待着也是待着。”他创作了座右铭:“说自己的话,让别人去走吧。” 走进刘长寿十几个平方的小屋,柜子上堆满了药瓶,最显眼的家当是一台3个月前刚买的飞利浦液晶显示器和外壳更新的旧主机以及惠普打印机和佳能复印机。2003年,刘长寿找到了这个最宝贝的去处,因为他知道:“许多场合不是我说话的地方,网上不同。”想法来了,刘长寿就坐下来发帖子,键盘上贴满了形状各异的胶布以便操练盲打识别,鼠标垫是塑料砧板,桌布就是枕套。老伴说他:“只要一坐下来,就不给我做饭了。”刘长寿就沉浸在这里把他的建言“广而告之,留世存照”。他说:“在这里,我能指挥刘长寿!” 找到了互联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坚持自己“不大一样”的思想方法了。他还是强调凡事“合乎逻辑”,这是他的信仰,至今还能倒背如流的古文诗词都是靠“分析文句内在的逻辑关系”记了一辈子。 一心希望上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刘长寿,在第一封写给市长的建议信中用《桃花源记》的句子为上海勾画了一番美好图景:“如果不造大桥,改建小桥并调整港区,腾出大块土地换来一座滨江森林花园。树木葱郁,江水涟漪,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那时上海市民,喜何如也。”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早就是刘长寿思考、建言的主题,有诸多领域的进言都提出在矛盾突出之前。上海,一个以国际化大都市为最大雄心的当今中国大舞台,城建发展方向亟需深入思考的诤言。 妙笔败笔?刘长寿说:“让后人评说吧!” 《新周刊》:结婚这么多年了,您在家里也爱提反对意见吗? 刘长寿:我以前不像现在这样“横秋”,只是到了50岁以后,遇事发作,继而一发不可收拾,这是说在家外面。 《新周刊》:怎样开始给市长写信的?这些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刘长寿:1990年时我是民建黄浦区区委委员。一次,区委布置要参政议政给政府提建议。当时偶然看到报纸报道南浦大桥,想到了就写了。 我自诩是中国第一流工程师,话赶话,曾向总师和全单位叫板,话很难听,没人应。专业方面,上海有几点技术突破是我破的。但因独到和耿直屡受打击,遇事党委副书记当面说“……但是你不是总师”,副总经理当面说“我们集团没有跟你刘长寿合作的打算”。我也算老专家了,临退休时我住肿瘤医院单位竟不肯照章支付住院费(是自己垫付大部分才勉强入住的)。眼见谬误横行、建设粗放,腹中才学报国无门,不肯折腰,为证曾言“我不是总师是上海设计院的错误”,写下54页技术专论批点我单位大工程设计低级错误,引起不小轰动,万马齐喑;我还接受聘请去给上海全市的建筑师和房屋结构工程师授课…… 上海市一级,缩短战线,只是再拾起、捏住黄浦江上的建桥旧题,网上帖子寄给市委书记、市长。中央一级,竟写“目前中国最大政失是什么令不行禁不止”,网上帖子和寄给温家宝同志—自认为不是打扰总理,而是探寻中央领导不致过劳于事务堆里的蹊径。希望大小人才受到起码尊重从而导致城市和国家越来越好。 人没有实力都是扯淡,名句云“语不惊人死不暝”,“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关键是我写的东西真理不真理。 《新周刊》:为什么会有这些低级错误? 刘长寿:现在的社会太浮躁,上海有些城市规划只是拿剪子哗的一下把布剪了,然后才想是要做旗袍还是做西装。可是已经晚了。不符合居住规律的情形太多。工作人员不敬业、不及格的是大多数。耐得住寂寞深入思考问题的人太少。应该对得起饭碗。 《新周刊》:同事们对您有什么评价? 刘长寿:还行。他们说:“你是我们院的刘罗锅。我们院里有三五个像刘长寿这样的人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新周刊》:不造大桥,您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刘长寿:第一,没有必要因为巨轮进港造大桥。黄浦江外的长江南岸、东海岸、杭洲湾北岸、岛屿,区别用途用较多的矮桥把黄浦江缝起来,以畅浦东、浦西交通。 第二,由于黄浦江的水深和岸边空间的局限,码头、船厂只有移出浦江才有大展宏图的天地。 第三,现在的码头、船厂、仓库迁出,建小桥省去了大桥的庞大引桥,都能腾出宝贵的黄金地段,可以进行大手笔的绿化和公共设施建设。 《新周刊》:反对造桥的这件事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吗? 刘长寿:我就像一个挑错别字的语文老师,指出专家和少数高级领导的低级错误。现在每3个月检查一次身体,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来。上海话“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是哪里”。我希望能把自己的东西网络化,留世存照吧。还是那句话:“一时的扬抑滞于权,千古的对错决于理。” 相关专题:新周刊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周刊专题 > 正文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