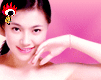新周刊封面:倾听时代最真诚的声音-我反对!(5) |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15日15:52 新周刊 | ||||||||||||
|
于坚 反全球化的那天必会到来 文/夏楠 图—何政东/新周刊 全球化是深入人心的全民运动,今天谁还会同意“闭关锁国”? 于坚马上搬出《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指着“化”这个词:“后缀。加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一说“全球化”,他马上联想到电梯。“本来嘛,步行,一万个人有一万个走法,速度、体态、目的地都不一样,一旦电梯化,还有什么细节上的不同?” 于坚上个月刚刚从巴黎回来,他感到所谓全球化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是我们每个人无法逃避的生活。它不是咖啡、麦当劳和关于先锋派文化和左岸的知识,“它是你现在正在喝的机器水”。在云南最遥远的乡村土地上,他总能看见塑料薄膜挂在蒲公英的枝叶上;他牢记拆除曹雪芹故居的时候那个并不反对的邻居,关心的只是房子的拆迁费、补偿;他更看到80岁的老人以住在四壁洁白刺目、刚刚油漆过的房间里,在大彩电前坐在新买的沙发上吊着两条腿为荣。而作为一个诗人,全球化更使他已经无法逃跑去做一个陶渊明。 “人们甚至认为土著们千年栖居的蘑菇房、竹楼都是有碍‘现代化’的,富起来的标准是看这些落后村庄和他们的落后生活方式消亡的速度。” 于坚感觉到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推动世界,“它的目标就是令我们在古代汉语里面建立起来的对人生世界的基本价值统统失效。” 他在《棕皮手记》里写道:“西方隐藏着可怕的危险,西方的器皿只要换一个角度去理解,它们都是武器。”“例如每天都要用的刀和叉,但不意味着它们总是被视为武器,把民航客机视为武器的是基地组织,汽车当然不是武器,或者不是被作为武器来制造的,但与步行和牛车相比,它确实有致命的因素;玻璃当然不是武器,或者不是被作为武器来制造的,但与雕花窗子和窗花绵纸相比,它确实也暗藏着致命的因素。你今天在大街上最害怕的是什么,难道不是汽车,你会害怕步行,对行走的人东张西望?看他在哪里拐弯?” 于坚从中国历史上揪出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认为这正是全球化的开始。“好像是在闭关锁国,但其实是在为全球化做思想准备。”他说,如果没有对中国传统的最后的激烈革命,“进步”、“天天向上”的思想怎会如此深入人心? “反全球化?今日在中国恐怕只是‘二三子’的杞人忧天。” 当人类选择“全球化”,选择“进步”、“再进步”时,于坚以个人的力量一意孤行:他拒绝无孔不入的通讯工具——手机,至今他都是一个鸡鸣时分就要起床的人(现在当然听不见鸡叫);他酷爱步行,将常去的旅行地西安强调为“长安”;出国参加诗歌节他坚持用昆明话朗诵自己的诗:他不会英语,他觉得用一生来研究汉语也是绝对不够的。“我无非是坚持我在自己故乡已经习惯了的生活传统,不动、不变而已,就已经成为一个‘另类’了。” 于坚还紧密注意身边一切的另类痕迹。丽江古城因为保持旧社会留下来的一堆“破烂”而成旅游上的另类,怒江因为是国内最后两条还没有“水电化”的原始河流之一也成为一个另类。 于坚感叹于“全球化”的厉害,它可以令传统的普遍的日常生活世界和词典全部变成“另类的”、“落后的”、“反动的”眼中钉。“我的所谓‘一意孤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愿被时代所抛弃,落后、永不成功。” 但是,当这个世界像阮籍那样途穷而返,于坚确信反全球化的那天必会到来。事实上,他早已从20世纪西方的现代主义运动中看到对‘全球化’的反对:卡夫卡的甲壳虫、艾略特的《荒原》、梭罗的《瓦尔登湖》……在巴黎,他看到的生活是推崇慢和古老,人们以没有进步或者反抗了进步而自豪。在奥尔良,他的朋友法国《诗歌》杂志的副主编穆沙先生自豪的是他隔壁的邻居是高更家的,而且现在的主人还是叫高更,那是什么样的破房子啊! 最近于坚还发现老子和庄子的作品越来越像是刚刚出版的著作。他相信:当一个中国人在8月15日的晚上走出小轿车的时候,他看不见月亮会很空虚;但一个西方人可以在空虚的时候去教堂,教堂就在世贸大厦的隔壁。 “中国人崇拜的是自然,是自然世界中的万物有灵。如果全球化的‘地球村’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为吾与子之所共适’,那么未来不正是要回到一个‘中国式的过去’吗?” 于坚对他的个人反全球化行动做结:时代的列车照样前进,但车轮会被某颗不动的沙粒磨掉一小小片,它的速度因此在可以忽略不计的记录里慢了千分之一毫米。 相关专题:新周刊 | ||||||||||||
|
|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新周刊专题 > 正文 |
|
| |||||||||||||||||||||||||||||||||||